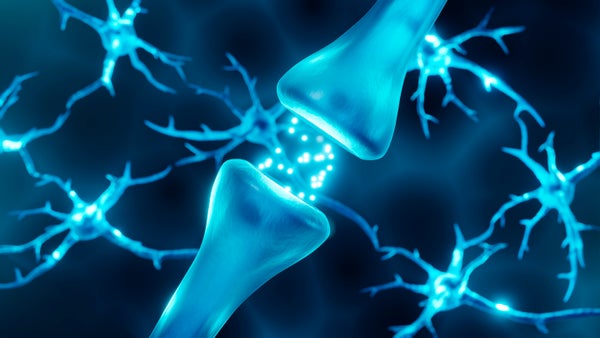梅根·霍爾: 胃如何告訴大腦它飽了?我們身體中的細胞如何生長和分裂?
詹姆斯·羅斯曼意識到這些過程背後的基本生物學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2010年,他與理查德·舍勒和托馬斯·聚德霍夫分享了卡вли神經科學獎,以表彰他們詳細描述神經細胞如何在微觀層面相互交流的工作。三年後,他獲得了諾貝爾獎。
大眾科學定製媒體與卡вли獎合作,與詹姆斯進行了對話,以瞭解他的發現和這項工作的未來。
霍爾: 詹姆斯·羅斯曼在獲得卡вли神經科學獎時感到非常驚喜。
詹姆斯·羅斯曼: 我一直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名生物化學家,其次是一名細胞生物學家。我從未真正認為自己是一名神經科學家。
霍爾: 他確實申請了神經科學研究生專案……
羅斯曼: 一切都很有道理,除了我沒有被錄取這個事實。
霍爾: 但詹姆斯不是那種會擔心標籤的人。事實上,他探索了廣泛的科學學科。作為耶魯大學的本科生,他學習了物理學,部分原因可能是他成長於 50 年代。
羅斯曼: 科學家和醫生在 1950 年代確實是最受尊敬的。尤其是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奧本海默,諸如此類的人。
霍爾: 但他的父親擔心他的職業選擇,所以他說服詹姆斯嘗試一門生物學課程。
羅斯曼: 我就愛上了它。
霍爾: 所以,他放棄了物理學,決定去哈佛醫學院學習更多關於生物學的知識。
羅斯曼: 最終我沒有完成醫學院的學業。
霍爾: 但是,當他在那裡時,他偶然發現了自己畢生的事業。
羅斯曼: 我是一名醫學院一年級學生,我正在聽我們組織學和細胞生物學課程的講座。
霍爾: 教授正在展示科學家在幾十年前拍攝的影像。它們首次展示了細胞有多麼複雜。
羅斯曼: 細胞不僅僅像是裡面裝滿了液體的愚蠢的小東西。它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地方。它更像一座城市,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
霍爾: 細胞內的這座城市擁有共享資訊的部門、建造蛋白質的工廠,甚至還有將這些蛋白質在細胞內部移動並釋放到細胞外部的機器。
羅斯曼: 如果蛋白質去錯了地方,細胞的組織就會喪失,它就無法再存活。
霍爾: 詹姆斯被迷住了。他想知道,所有這些複雜性是如何運作的?細胞中形成的蛋白質如何到達正確的位置?
羅斯曼: 並且必須有一種不同的機制,我稱之為“送貨卡車”,將貨物,即工作部件,從它們在工廠開始的地方,透過配送系統中的倉庫,運送到最終目的地。
霍爾: 當時,細胞生物學家喬治·帕拉德猜測,裝滿液體的稱為“囊泡”的小囊與此有關。
羅斯曼: 囊泡是一個小球,就像一個微小的氣球。它不大於五百或一千個氫原子,氫原子是最小的原子。細胞在任何時候都有成千上萬個這樣的小囊泡。
霍爾: 而且它們無處不在……
羅斯曼: 這些微小的囊泡遍佈自然界。它們存在於每個神經末梢,它們存在於你的消化道中,例如,它們在你的胃腸道中儲存胰島素,尤其是在胰腺中。因此,它們遍佈全身。
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喬治·帕拉德認為,這些囊泡是移動蛋白質在體內運輸的送貨卡車。但他無法證明這一點。
他無法弄清楚有多少種不同型別的送貨卡車或囊泡。他也無法真正追蹤它們在細胞中從起點到終點的過程。
霍爾: 最重要的是,他無法解釋使囊泡能夠拾取蛋白質並將它們運送到正確目的地的機制。
霍爾: 那麼,你的工作是弄清楚所有這些細節嗎?
羅斯曼: 是的,我把這當作我的工作。
霍爾: 但是如何做到的?詹姆斯首先借鑑了生物化學的一個基本前提——細胞內發生的一切基本上都只是一個化學反應。如果你能分離出那個化學反應,你就能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
羅斯曼: 而做到這一點的手段首先始終是在活細胞外部重現這個過程,無論它多麼複雜。
霍爾: 所以,他認為研究運輸囊泡如何工作的最佳方法是打破細胞,並在試管中重建囊泡。
羅斯曼: 而三維組織是如此令人歎為觀止。細胞的每個部分都位於每個細胞的相同位置。我來了,說,好吧,我要破壞那個組織。
霍爾: 生物化學家已經使用這種方法來理解各種各樣的事情,從蛋白質是如何製造的,到能量是如何儲存在細胞中的。
羅斯曼: 而唯一尚未實現的是,我們能否在細胞外部重現決定細胞自身三維組織的那些過程?
這就是我作為一名 25 歲的年輕科學家所做的假設,你知道嗎,我可能錯了。
霍爾: 事實證明,他是對的。在斯坦福大學做博士後期間,經過多年的試驗和錯誤,他成功地重現了囊泡將蛋白質運輸到細胞中特定位置的整個過程。
羅斯曼: 我們可以取出那些囊泡,並將它們放回細胞提取物中。它們會將貨物運送到完全正確的位置,就好像它們在活細胞中一樣。
霍爾: 在重現這些囊泡,然後研究它們如何運輸蛋白質之後,詹姆斯很快發現這個過程類似於包裹的運送方式。
羅斯曼: 每個包裹都有一個條形碼,就像一個追蹤號碼。卡車必須去,並且必須卸下帶有正確追蹤號碼的貨物。
霍爾: 但是囊泡不是追蹤號碼,而是蓋有所謂的 v-SNARE 蛋白。這些囊泡透過漂浮並尋找它們的匹配物(稱為 t-SNARE)來到達目的地。當兩個 SNARE 蛋白相遇時,它們會鎖定到位或融合。
羅斯曼: 這些 SNARE 蛋白存在於植物、酵母和人類中。存在細微差別,使得 SNARE 蛋白能夠在不同物種以及生物體中的不同地點和時間發揮作用。但基本的物理原理是通用的。
霍爾: 這個原理是如此通用,以至於詹姆斯在試圖理解這些 SNARE 蛋白如何工作時,意外地解決了一個來自神經科學的問題。
羅斯曼: 我的博士後知道如何測量這些 SNARE 蛋白,但不知道它們是由什麼構成的。所以,我們不知道在哪裡能找到最多的它們。
霍爾: 因此,他們開始檢查不同的組織樣本,尋找找到高濃度 SNARE 蛋白的最佳場所。
羅斯曼: 結果證明是大腦。
霍爾: 他們使用牛腦的樣本來分離和純化這些 SNARE 蛋白。
羅斯曼: 當我們鑑定出它時,結果證明它們已經是已知的蛋白質。
霍爾: 神經科學家已經一直在研究相同型別的樣本,以瞭解大腦中的神經元如何在它們之間的小間隙(稱為突觸)之間連線和交流。
羅斯曼: 我們並非有意這樣做,我們想解決一個更普遍的問題。
霍爾: 但事實證明,他們關於囊泡以及它們如何運輸蛋白質的普遍問題,也回答了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囊泡如何做同樣的事情來在腦突觸之間共享資訊。這一切都歸結為這些 SNARE 蛋白。
羅斯曼: 一旦我們看到它們與突觸中的一組相同,我們就可以精確定位它們並說,好吧,這就是突觸囊泡的工作方式。它是通用原理的一部分。
霍爾: 詹姆斯無意中解決了一個關於大腦如何運作的重要問題。如此重要,以至於他獲得了卡вли獎。
對於一個無法進入哈佛大學神經科學系的人來說,這還不錯。詹姆斯說,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
羅斯曼: 正是因為我幸運地被神經科學系拒絕,我才能夠,基本上是意外地,在試圖解決細胞生物學中一個更廣泛問題的過程中,順便解決一個神經科學問題,這難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嗎?
霍爾: 詹姆斯說,他的研究時代是關於理解細胞的機制,但科學家們開始更多地瞭解混合物中也存在的神秘物質。
羅斯曼: 在這些生物材料中,這些機器以某種方式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表現得像連續固體或液體或像橡膠彈性的材料。這實際上非常奇怪。
霍爾: 他說,理解這些奇怪的物質可能會改變我們對醫學的方法,並加深我們對身體功能的理解。
羅斯曼: 我們將看到細胞某些部分的狀態變化,而我們今天還不瞭解這些變化,我們將學習如何操縱它們,它們將在疾病中被改變。
霍爾: 他對試圖解開這些謎團的年輕科學家有什麼建議?
羅斯曼: 哦,這很容易。永遠不要聽取老科學家的建議。
霍爾: 他說,今天的研究人員面臨著與他不同的挑戰,包括較少的自由和資金來承擔重大風險,並在一個問題上長期工作。
但如果他可以給出一些一般性建議,他會說,美國應該增加對基礎研究的資助,這樣像他這樣專注的科學家更有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偶然發現重要的發現。
霍爾: 詹姆斯·羅斯曼教授是耶魯醫學院細胞生物學系主任,一位生物化學家和細胞生物學家。
2010年,他與理查德·H·舍勒和托馬斯·C·聚德霍夫分享了卡вли神經科學獎。
卡вли獎旨在表彰科學家在天體物理學、奈米科學和神經科學領域的突破——轉變我們對宏觀、微觀和複雜事物的理解。
卡вли獎是挪威科學與文學院、挪威教育與研究部以及美國卡вли基金會之間的合作伙伴關係。
這項工作由大眾科學定製媒體制作,並在卡вли獎的支援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