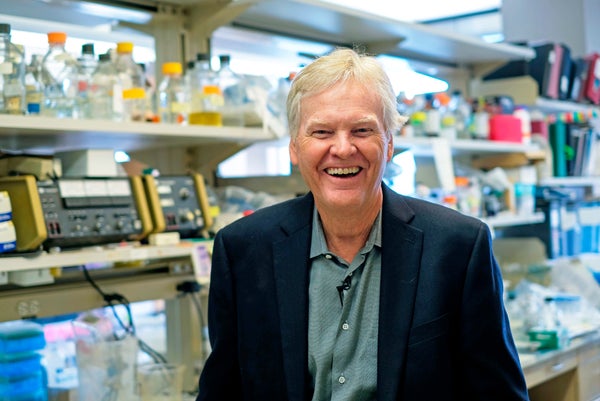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10 月 2 日,日內瓦大學的研究人員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介紹了他們在一類肌肉細胞中發現的生物鐘。同一天,三位研究人員——傑弗裡·霍爾、邁克爾·羅斯巴什和邁克爾·楊——得知他們因研究鑑定出控制生物鐘的關鍵基因而獲得了 2017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楊曾在 2000 年為《大眾科學》撰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了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他在文中加入了一個題為“時鐘無處不在:它們不僅僅存在於大腦中”的側邊欄,重點介紹了其他人在果蠅身上進行的研究,表明不僅僅是大腦有這樣的時鐘。諾貝爾獎獲得者專注於果蠅大腦,但晝夜節律機制也出現在果蠅的腎臟狀馬氏管以及昆蟲的翅膀、腿、口器和觸角中。
楊在他的側邊欄結尾寫道:“顯示晝夜節律時鐘活動的各種細胞型別的多樣性表明,對於許多組織來說,正確的時間安排非常重要,值得在本地進行跟蹤。這些發現可能會給‘生物鐘’一詞賦予新的含義。”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在過去的 15 年裡,側邊欄已成為“主欄”,因為大腦外部的分子計時裝置越來越受到關注——日內瓦的論文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2015 年,西北大學的基思·蘇瑪和弗雷德·圖雷克為《大眾科學》撰寫了一篇文章——“我們體內的時鐘”——記錄了對時鐘基因的搜尋如何擴充套件到人類,並超越了視交叉上核,視交叉上核是根據光線和黑暗的線索跟蹤時間的大腦主時鐘。
現在對人類的研究提供了證據,證明了這些區域性時鐘的重要性,作者表示,這些區域性時鐘“調節著各種組織中 3% 到 10% 的基因的活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高達 50%”。蘇瑪和圖雷克寫道。更重要的是,當這些區域性時鐘與大腦的主時鐘不同步時,通常會發生糟糕的事情。晝夜節律的異常會導致代謝、心血管、胃腸道——甚至神經退行性問題。
諾貝爾獎給晝夜節律生物學帶來的關注也應該突出獎項本身在獎勵科學領域最佳工作方面的侷限性。所有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得者無疑都做了“諾貝爾級別”的科學研究。但研究依賴於數百人甚至數千人的團隊——現在研究區域性時鐘的大量人員只是一個例子。
在諾貝爾獎研究之前和之後,年代生物學領域也有著悠久的歷史。 20 世紀 70 年代,加州理工學院的西摩·本澤和羅納德·科諾普卡定位了諾貝爾獎引用的基因之一——一個名為 period 的基因。但最終克隆和測序該基因的是三位獲獎者。後來,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的約瑟夫·高橋發現了參與啟用 period 和其他時鐘基因表達的基因——分子計時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有這些科學家也做了諾貝爾級別的研究。如果本澤和科諾普卡仍然在世,或者他們被允許頒發第四個獎項,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可能會有所不同。也許諾貝爾獎需要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