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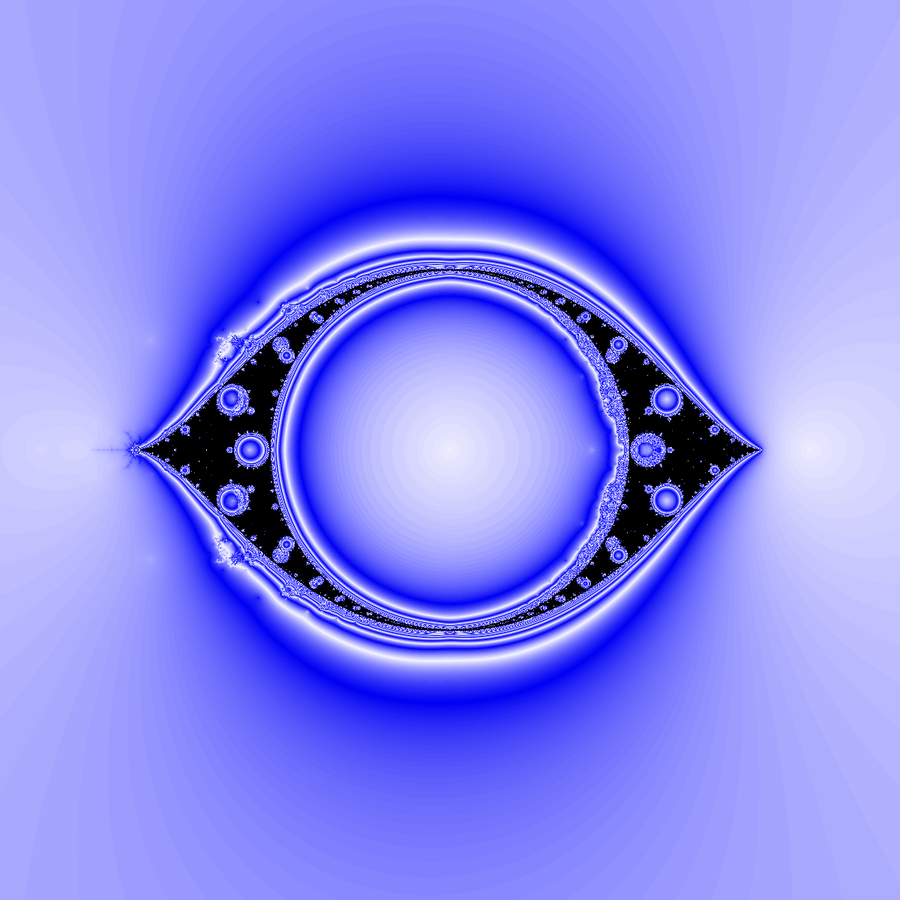
勞拉·德馬科的動力系統研究過程中建立的影像。圖片來源:勞拉·德馬科。
今年我一直在為女性數學家協會的新聞通訊共同撰寫一個名為“數學,現場訪談”的系列訪談。在我的訪談中,我“傾聽”女性數學家之間的對話。第一次訪談發表在新聞通訊的五/六月刊(需要密碼)。在訪談中,我與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勞拉·德馬科和芝加哥大學的艾米·威爾金森兩位數學家進行了交談。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她們都在動力系統領域進行研究,動力系統是研究抽象數學空間如何隨時間演化的學科。當我參加德馬科在一月份聯合數學會議上的特邀演講時,我產生了與她們交談的想法。(如果您有興趣,喬丹·艾倫伯格寫了一篇關於她的演講的精彩博文。)威爾金森在演講結束時提出了一個問題,我意識到她們將成為這個系列訪談的絕佳搭檔。
三月份,我與德馬科和威爾金森會面,我們討論了她們如何對數學產生興趣,女性榜樣對年輕女性數學家的重要性,以及她們對有抱負的數學家的建議。這是發表在AWM新聞通訊上的訪談的略微刪減版本。感謝德馬科和威爾金森慷慨地抽出時間和提供建議。
起源
伊芙琳·蘭姆:你們願意先談談你們是如何開始接觸數學的嗎?
艾米·威爾金森:我從嬰兒早期就開始接觸數學了。我一直都喜歡數學。
勞拉·德馬科:嬰兒早期?
艾米·威爾金森:我有點誇張了,但我一直都喜歡數學。
勞拉·德馬科:你在學校之外做過什麼嗎,還是隻是在課堂上?
艾米·威爾金森:我上的是蒙特梭利幼兒園。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數學。蒙特梭利的好處在於一切都是自由形式的,所以你可以整天在一個區站待著。我基本上整天都在數學區站待著。我會整天在那裡做。數五進位制數之類的。我想那時就很清楚我對數學充滿熱情。你以前是物理學家,對吧?
勞拉·德馬科:是的,但不是“真正”的。就我而言,我會說我肯定一直都喜歡數學。我一直喜歡上課,喜歡學習和做數學。但我的哥哥,他比我大,總是比我更擅長謎題之類的東西。他是參加競賽的人。他參加了MathCounts和其他各種競賽,他對那些競賽非常著迷。我對參加競賽不感興趣。我找到了自己的路,練習長笛,做自己的事情,但我可能比你晚才回到數學這條路上。
我第一次想到“我喜歡數學到想要永遠從事數學”是在高中某個時候,那時我想,“我想成為一名數學老師。”有趣的是,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天坐在校車上從高中回家,想著,“我可以成為一名數學老師。我可以永遠做數學,”想著這就是數學的意義,對吧,成為一名數學老師。我不知道當老師之外還有什麼。
在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才知道教授們做研究。我不知道做研究意味著什麼。我當時正在參加一個社會科學研討會。每週我們都會學習一種不同的理論以及各種例子。有一天,那位來自法學院的教授對我們這群二年級學生說,“你們知道你們所有的教授都在做研究嗎?” 我甚至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我的數學教授做研究意味著什麼?
第二天,我去問了我所有的數學教授,“你們都做什麼?” 我當時正在學機率論,我去找了我的機率論教授。“我聽說你做研究。你都做什麼?” 想象一下,當一個學生來問你這個問題時會是什麼樣子。我記得那是一次非常尷尬的對話。他說了一些話,當然我不記得他說的是什麼,而且我確信我當時根本不明白。但那一刻非常難忘。
與此同時,我是物理專業的學生。我高中時很喜歡物理課,我想,也許我會學物理。我知道科學家做研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瞭解到數學家也做研究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艾米·威爾金森:那真是個很棒的故事。我腦海中浮現出你走進第一位教授的辦公室,就像:“我聽說你們這些人做研究。那不是真的吧?”
伊芙琳·蘭姆:除了瞭解到數學研究的存在,還有哪些關鍵時刻讓你確信你想成為一名數學家?
艾米·威爾金森:我的關鍵時刻非常明確。我上了大學,我對自己數學能力感到非常不自信,我沒有得到很多鼓勵,我不太確定這是否是我想要做的,所以我沒有申請研究生院。我回到芝加哥的家,找到了一份精算師的工作。我喜歡我的工作,但我開始覺得我的生活中有一個空洞。缺少了些什麼。我意識到突然間我的宇宙變得有限了。為了這份工作我必須學習的任何東西,我最終都能學會。我可以輕易看到這份工作的侷限性,我意識到對於數學,我可以想象有太多我永遠不會知道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回去做數學。我喜歡這種無限視野的感覺。
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關鍵時刻,實際上只是離開數學一段時間。總的來說,不時地離開數學確實讓人精神煥發。就像我生孩子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無法做數學。然後我會想念它。然後我就明白了我為什麼要做數學。
勞拉·德馬科:你會對它格外興奮,並且真正充滿熱情。
艾米·威爾金森:是的。而且心懷感激。
勞拉·德馬科:我也有過這樣的時刻,我有點被“哇,我真的很喜歡我現在做的事情,我能有這份工作,能這樣生活真是太棒了!”的想法所淹沒。當然,我還有教學和其他職責,但僅僅是我們可以得到支援,存在這樣一個環境的想法。當一切順利時,我會這樣想。當一切不順利時,我會想,“我讓自己陷入了什麼境地?!”
我不知道你的故事,你在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年就工作了。我確實有過一些時刻,讓我確信要讀研究生。在我本科的最後一年,我的物理教授們非常鼓勵我。物理系的文化氛圍就是鼓勵。他們任何表現出色的本科生都會自動參與到研究專案中。所以我認識大部分教職員工,申請研究生院在某種程度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數學系給人的感覺不是那樣。但在我本科的最後一年,我們系終於迎來了第一位女教授。她在我的最後一年到來,那個學期我決定請她做我本科畢業論文專案的導師。僅僅是她的出現對我來說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後,在我本科最後一年的秋季學期,我的一門課的助教說,“哦,勞拉,你打算申請哪所研究生院?” 我說,“我不打算申請研究生院。我實際上明天有一個工作的面試。” 他說,“什麼?你不申請研究生院?” 他非常鼓勵我。突然之間,有一個研究生似乎很關心我,並說,“這太瘋狂了!你為什麼不申請研究生院?”
艾米·威爾金森:真是巧合。
勞拉·德馬科:這有點像是偶然,有一個人想到了實際問我的想法。
艾米·威爾金森:或者沒有想那麼多。
勞拉·德馬科:沒錯,只是問了!我的物理導師當然也談到過這個想法。但我到最後對物理並不那麼熱情。
微積分
伊芙琳·蘭姆:有沒有哪些數學主題對你們來說特別有吸引力或美麗?
艾米·威爾金森:我非常喜歡微積分,可能是因為我年輕時就學了它,而且學得很好。對我來說,用微積分做一些事情總是令人感到欣慰。微積分的發明無疑是一場革命。
勞拉·德馬科:一次概念上的突破。
艾米·威爾金森:這很有趣,因為我們就像把它隨便拋給高中生一樣,而且我認為他們中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美妙之處。
勞拉·德馬科:不知道這些想法的真正含義。
艾米·威爾金森:當然,我學到的最美麗的數學之一就是微積分。
勞拉·德馬科:你提到微積分真有趣。直到我作為研究生教微積分時,我才真正欣賞它。我當時在給一年級學生講課。我被這門學科深深吸引了。我突然意識到,天哪,這真是太美了!我記得我的祖母問我最近在想什麼。我說,“嗯,我現在正在教微積分,你知道嗎,微積分真的很美。” 她說,“好吧,勞拉,什麼是微積分?你能否在20分鐘內告訴我,什麼是微積分?” 能夠有機會坐下來,跟我的祖母,所有的人,告訴她這些真是太棒了。
勞拉·德馬科:沒錯。這很有趣,因為她說她年輕時喜歡數學,但那在那個年代並不是她可以追求的東西。她當然從未追求過任何超出一些基礎課程的東西。但她坐下來聽了我的解釋。
艾米·威爾金森:你認為她理解了嗎?
勞拉·德馬科:我不知道。我更多的是在談論哲學。我沒有做任何計算。但是微分和積分的概念,以及微積分基本定理,它們是如何聯絡起來的。我不知道她是否理解了。但這是一次很好的談話。
數學領域的女性
伊芙琳·蘭姆:作為數學領域的女性,你們是否面臨過任何挑戰?
勞拉·德馬科:現在我會說這是一種優勢。一旦我們達到現在的階段,這可能比劣勢更像是一種優勢。人們希望有女性演講者和女性參與到不同的層面,以及一定數量的頂層女性。早些時候,情況就不同了。
艾米·威爾金森:我同意。只要你能說不,這就是一種優勢。我認為你會被要求做更多的事情。很難對那些涉及年輕人或女性的事情說不。隨著年齡的增長,你會感到有真正的責任去幫助年輕人。這是唯一的劣勢。我覺得我被要求做的事情要多得多。
勞拉·德馬科:是的,絕對是。
艾米·威爾金森:我很難對很多事情說不,因為它們都是有價值的。但是當我年輕的時候,勞拉關於有一位女數學教授的故事真的引起了我的共鳴,因為當我上大學的時候,哈佛根本沒有女性。沒有研究型教員,一個都沒有。
勞拉·德馬科:甚至沒有博士後?
艾米·威爾金森:甚至沒有博士後。所以我認為我在那個時候渴望一個榜樣。我認為如果當時出現一位女性榜樣,那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我來說,生孩子也很困難。這很可怕。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真的沒有那麼多可以效仿的人,來說這是可行的。即使是在碧翠絲出生的時候,那也只是13年前,這還不是很正常,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支援。這是我認為女性更難做到的另一件事。對一些女性來說,這尤其困難。我很幸運,由於很多原因,一切都還算順利。
總的來說,刻板印象威脅對我來說確實存在。我認為在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小小的聲音一直在說,好吧,你真的認為你屬於這裡嗎?當你的自信心很低的時候。
勞拉·德馬科:是的,當你不太自信的時候。我不太自信。
艾米·威爾金森:在那個時候,沒有人真正自信。
勞拉·德馬科:沒錯,沒有人是自信的。人們的反應非常不同。但我不是那種會透過提高嗓門或讓自己被看到來做出反應的人。事實上,我傾向於做的就是試圖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淡化我的女性氣質。我像男孩一樣穿衣服,而且我真的盡力不那麼女性化。現在我感覺完全可以自在地做我自己。當然,那時我會努力不以某種方式突出自己。我不太自信,而且在我的班級裡是唯一的女孩,這並沒有幫助。
艾米·威爾金森:我確實聽到過一些人發表不恰當的、低俗的評論。這些評論有點讓人疏遠,但我認為我並沒有覺得任何這些評論特別令人沮喪。更難的是普遍的冷漠。
勞拉·德馬科:是的,這可能是一個因素。就性格而言,我可能需要鼓勵。我希望得到一些明確的鼓勵。如果我做得好,我想知道!
我記得當我最終決定申請研究生院時,我有一個非常親密的朋友說,“嗯,你當然應該申請哈佛和普林斯頓,以及所有頂尖的學校。” 我說,“哦不,我永遠進不去。” 所以我甚至懶得申請。但我確實申請了伯克利,我被伯克利錄取了,然後去了伯克利。當然,最終我轉學到了哈佛,並最終獲得了哈佛的學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最終還是發生了。而這位朋友,她不是數學家,所以我認為她根本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但最終她是對的。
艾米·威爾金森:她覺得這很明顯,這太有趣了。一個普通人會想,“嗯,當然。你是一個頂尖的學生。你應該申請頂尖的學校。” 在數學界,圍繞這些頂尖學府存在著巨大的神秘感,而一個甚至只是稍微缺乏一點自信的人,就會覺得“不,我當然不會申請這樣的地方。” 我想知道有多少女性因為這種態度而被擋在了頂尖學府之外。
勞拉·德馬科:而且沒有意識到你實際上應該去爭取一些東西。
所以你想成為一名數學家...
伊芙琳·蘭姆:你們對可能正在考慮從事數學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嗎?
勞拉·德馬科:如果你熱愛它,就去追求它。有一些人可以交談會很有幫助。有一個導師或某種研究專案來聯絡你,學習如何與人交流會有幫助。
艾米·威爾金森:我很高興我在高中時參加了數學競賽隊。
勞拉·德馬科:所以你參加了數學競賽隊?
艾米·威爾金森:我參加了數學競賽隊。在初中的時候,我的數學真的很好。我顯然有點像一個數學小子,但一群其他孩子都在參加各種天才計劃和各種考試,我太害怕做那種事情了,而且我可能也不會做得很好。當我上高中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什麼推動我去看看,但我去了。參加我高中的數學競賽隊真的很有意義。它給了我一個由其他數學愛好者組成的社群。
勞拉·德馬科:真正喜歡數學的孩子們。至少現在這些數學圈子開始在各地湧現。
艾米·威爾金森:是的,數學圈子甚至更酷,因為它不是競賽。雖然,這些數學競賽名聲不好。它不僅僅是坐在房間裡填寫這些試卷。還有口頭競賽。我記得我展示了一些關於定寬曲線的東西。你會得到一個主題,然後提前閱讀。他們會問你問題,你可以準備答案。然後你站在黑板前展示答案。女孩們,即使在當時,碰巧也做得很好。我們學校有一個名叫納迪亞的女孩,是一位非常高的俄羅斯女排運動員。她在數學競賽隊裡沒有做其他任何事情,但她是這個競賽口頭部分的佼佼者。
然後還有雙人專案,我和我的高中競爭對手組成了雙人隊。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專案。不同的才能可以參與其中,我相信現在也有類似的專案。
這是一個建議,去探索。你不必是最優秀的才能從中獲得收穫。另一個給年輕人的建議是,真的有第二次機會,事情會改變。作為一名本科生,我的學業成績非常參差不齊。我做了很多我喜歡的事情,但不一定是數學。我在一些數學課上表現出色,在另一些數學課上表現糟糕。所以我很幸運能進入伯克利。但我發現研究生院與大學完全不同。突然之間,沒有了干擾,這成了我所做的一切。
勞拉·德馬科:而且你很享受它。
艾米·威爾金森:我很享受它,我感覺自己處於最佳狀態。值得一試。那不是害怕嘗試的時候。如果行不通,那也只是一年的人生。沒什麼大不了的,隨便吧。我只是認為更多的人應該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