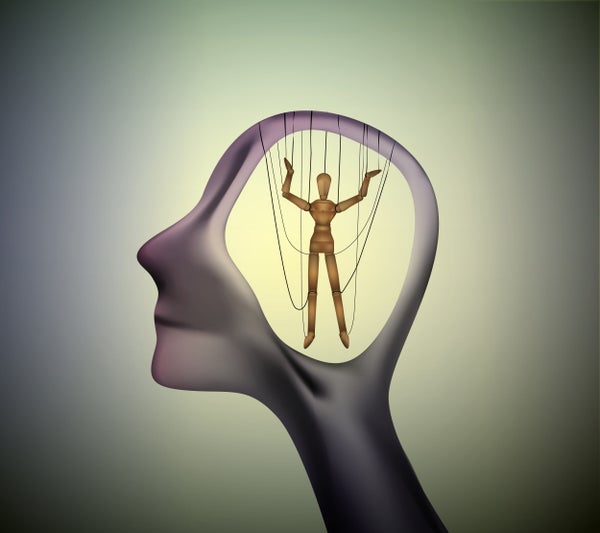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至少自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人類存在最核心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是否擁有自由意志。20世紀後期,有人認為神經科學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然而,正如最近變得清楚的那樣,事實並非如此。這個難以捉摸的答案是我們道德準則、刑事司法系統、宗教,甚至生命本身意義的基礎——因為如果生命中的每一個事件都只是機械定律的可預測結果,那麼人們可能會質疑這一切的意義。
但在我們問自己是否擁有自由意志之前,我們必須理解它到底是什麼意思。一種常見且直接的觀點是,如果我們的選擇是預先確定的,那麼我們就沒有自由意志;否則我們就擁有。然而,經過更仔細的思考,這種觀點被證明出奇地不合適。
要了解原因,請首先注意“預定選擇”中的“預”字首完全是多餘的。不僅所有預定選擇都是根據定義確定的,而且所有確定的選擇也可以被視為預定的:它們總是來自先於它們的傾向或必然性。因此,我們真正要問的只是我們的選擇是否是確定的。
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在這種情況下,自由意志的選擇將是不確定的選擇。但是,什麼是不確定的選擇?它只能是隨機的選擇,因為任何不是根本隨機的事物都反映了一些潛在的決定它的傾向或必然性。在決定論和隨機性之間沒有可以容納既不確定也不隨機的選擇的語義空間。這是一個簡單但重要的觀點,因為我們常常——不連貫地——認為自由意志的選擇既不是確定的也不是隨機的。
我們對隨機性的概念本身就已經是模糊不清的。在操作上,如果我們在一個過程中無法辨別出模式,我們就說它是隨機的。然而,一個真正的隨機過程原則上可以僅僅透過偶然產生任何模式。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可能很小,但它不是零。因此,當我們說一個過程是隨機的時候,我們只是承認我們對它潛在的潛在因果基礎的無知。因此,訴諸隨機性不足以定義自由意志。
此外,即使可以,當我們想到自由意志時,我們想到的不僅僅是隨機性。自由選擇不是古怪的選擇,不是嗎?它們也不是不確定的:如果我相信我做出自由選擇,那是因為我感覺到我的選擇是由我決定的。自由選擇是由我的偏好、喜好、厭惡、性格等決定的,而不是由其他人或其他外部力量決定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選擇無論如何都是確定的,那麼談論自由意志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如果你仔細思考,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們的選擇是由我們經驗上認同的東西決定的,那麼我們就擁有自由意志。我認同我的品味和偏好——正如我所意識到的那樣——因為我將它們視為我自己的表達。因此,我的選擇是自由的,只要它們是由這些感受到的品味和偏好決定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認為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我們的選擇是由我們自己大腦中的神經生理活動決定的觀點——與自由意志相矛盾呢?因為,儘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們並沒有從經驗上認同神經生理學;甚至不是我們自己的。就我們的意識生活而言,我們大腦中的神經生理活動只是一種抽象。我們直接和具體地熟悉的是我們的恐懼、慾望、傾向等等,就像體驗到的一樣——也就是說,我們感受到的意志狀態。因此,我們認同這些,而不是我們頭骨內發射神經元的網路。神經生理學和感受到的意志之間的所謂同一性僅僅是一種概念上的,而不是經驗上的同一性。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貫穿整個唯物主義形而上學的問題:我們真正擁有的只是意識的內容,哲學家稱之為“現象性”。我們的一生都是一種感受和感知到的現象性流。這種現象性不知何故來自於意識之外的物質——例如發射神經元的網路——這是一種理論推論,而不是一種真實的生活;它是一種我們在概念推理的基礎上創造和接受的敘事,而不是某種感覺到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無法真正認同它。
因此,自由意志的問題歸結為形而上學的問題:我們感受到的意志狀態是否可以還原為意識之外和獨立於意識的東西?如果是這樣,就不可能存在自由意志,因為我們只能認同意識的內容。但是,如果相反,神經生理學只是我們的感受到的意志狀態從外部角度觀察的呈現方式——也就是說,如果神經生理學僅僅是意識意志的影像,而不是其原因或來源——那麼我們確實擁有自由意志;因為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的選擇是由我們直觀地視為我們自己表達的意志狀態決定的。
至關重要的是,形而上學的問題可以透過一種顛倒通常的自由意志方程式的方式來合法地提出:根據19世紀的哲學家亞瑟·叔本華的觀點,是自然規律來自一種超個人的意志,而不是意志來自自然規律。感受到的意志狀態是心靈和世界不可還原的基礎。儘管叔本華的觀點經常被嚴重誤解和歪曲——最明顯的是被假定的專家所歪曲——但當被正確理解時,它們為調和自由意志和看似決定性的自然規律提供了一個連貫的方案。
正如我在我的新書《解讀叔本華的形而上學》中闡述的那樣,對於叔本華來說,一切事物的內在本質都是有意識的意志——也就是說,是意志。自然是動態的,因為其潛在的意志狀態為事件的展開提供了必要的動力。像他的前輩伊曼紐爾·康德一樣,叔本華認為我們所說的“物質世界”僅僅是一種形象,是觀察者心中對世界的感知表徵。但這種表徵並不是世界在被表徵之前本身的真實狀態。
由於我們所擁有的關於外部環境的資訊似乎僅限於感知表徵,康德認為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然而,叔本華認為我們不僅可以透過感官器官,還可以透過內省來了解一些關於它的資訊。他的論證如下:即使在沒有感官器官介導的所有自我感知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會體驗到我們自己內生的、感受到的意志。
因此,在被表徵之前,我們本質上是意志。我們的身體僅僅是我們的意志如何從外部有利位置呈現自己的方式。而且,由於我們的身體和世界的其餘部分都以物質的形式出現在表徵中,叔本華推斷,世界的其餘部分,就像我們自己一樣,本質上也是意志。
在叔本華對現實的啟發性觀點中,意志確實是自由的,因為它是最終存在的一切。然而,它的形象是自然界看似決定性的規律,它反映了意志的本能的內在一致性。今天,在他首次發表他開創性的思想200多年後,叔本華的著作可以將我們對自由意志的內在直覺與現代科學決定論調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