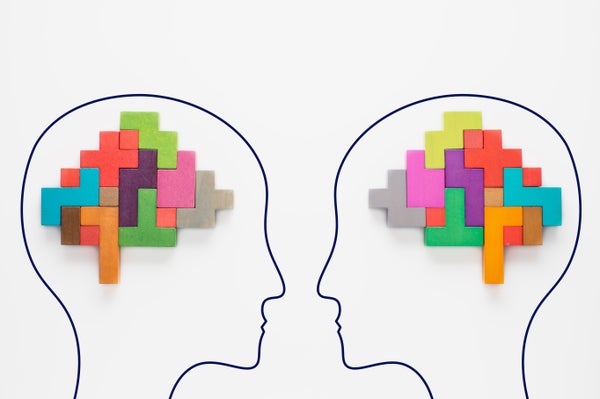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令我失望的是,西蒙·巴倫-科恩最近的文章《神經多樣性概念正在分裂自閉症群體》延續了對神經多樣性運動的常見誤解:它將自閉症視為一種差異,而非一種殘疾。巴倫-科恩將這個問題呈現為對立的兩方:醫學模型,它將自閉症視為一套需要治癒或治療的症狀和缺陷;以及神經多樣性模型,他認為該模型忽視了自閉症的任何致殘方面。不幸的是,這混淆了神經多樣性運動與殘疾的社會模型,而且這還是對社會模型的不完整理解。
在我詳細闡述之前,讓我總結一下神經多樣性運動真正相信什麼
自閉症和其他神經變異(學習障礙、多動症等)可能是殘疾,但它們不是缺陷。患有神經差異的人不是正常人的殘缺或不完整版本。
殘疾,無論多麼嚴重,都不會削弱人格。大腦非典型的人和所有人一樣,是完全的人,擁有不可剝奪的人權。
殘疾人可以過上豐富而有意義的生活。
神經變異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像體型、形狀、膚色和性格的變異一樣。我們誰也沒有權利(或智慧)透過決定保留哪些特徵和丟棄哪些特徵來試圖改進我們的物種。每個人都是有價值的。
殘疾是一件複雜的事情。通常,它更多地是由社會的期望而不是個人狀況來定義的。並非總是如此,但通常是這樣。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關於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殘疾的社會模型來自殘疾研究領域。它認為,當(社會)環境不能適應他們的需求時,一個人就是“殘疾人”。一個例子:在一個坡道和電梯隨處可見的世界裡,輪椅使用者不是“殘疾人”,因為他/她/他們可以像步行者一樣訪問所有相同的東西:學校、工作、餐館等。然而,提供平等機會並不意味著忽視輪椅使用者可能遇到的差異和困難。
在2004年的文章《不工作的權利:權力和殘疾》中,桑尼·泰勒解釋說:“精神或身體上受到挑戰的狀態是[殘疾理論家]所說的受損;受損會帶來個人挑戰,並在心理過程和身體活動方面存在缺陷……相比之下,殘疾是對受損人群的政治和社會壓迫。這是透過使他們在經濟和社會上孤立來實現的。殘疾人的住房選擇有限,在社會和文化上受到排斥,職業機會非常少。”
很少有(如果有的話)神經多樣性倡導者否認自閉症中存在障礙。或者有些障礙比其他障礙更具挑戰性,無論是否有便利設施。我們和巴倫-科恩一樣,希望解決自閉症常伴隨而來的健康問題,如癲癇和消化問題。但雖然這些在自閉症患者中比非自閉症(或“神經典型”)患者更常見,但它們實際上並不是自閉症的症狀。
文化也會影響這些事情。根據歷史上的時間和地點,癲癇可能使一個人成為受人尊敬的薩滿,或被懷疑是惡魔附身。現在比20年前食品公司開始提供無麩質食品時更容易適應麩質過敏。如果小麥和黑麥滅絕了,麩質過敏將永遠不再是殘疾!
當我們談論“不將自閉症病理化”時,我們不是指“假裝自閉症患者沒有障礙”。但我們也不認為神經和行為差異總是問題。例如,不喜歡社交活動本身並沒有什麼錯。不想社交與想參與但無法參與是不同的。這兩種情況在自閉症患者身上都可能發生。一種需要接受,另一種需要幫助。可悲的是,我還沒有遇到一位不將兩者視為等同,並同樣需要糾正的治療師。
雖然神經多樣性方法與社會模型有很多重疊之處,但它主要呼籲包容和尊重那些大腦以非典型方式運作的人,無論他們的殘疾程度如何(我在這裡將重點關注自閉症,但神經多樣性是關於“各種各樣的大腦”)。這需要挑戰我們對什麼是正常、什麼是必要以及什麼對一個人過上美好的生活是可取的假設。當然,更好的便利設施和減少汙名將極大地改善我們的生活。但對有意義的生活的更廣泛定義也會如此。正如泰勒所說:“西方文化對對社會有用性的理解非常有限。人們可以透過金錢以外的方式發揮作用。”
神經多樣性運動相信為自閉症患者提供在工作場所取得成功的工具,但不羞辱或憐憫那些永遠無法在經濟上(或身體上)獨立的人。我們認為,需要終身照顧的人也可以快樂並實現個人目標。泰勒補充說,“獨立性在這個國家可能被看得高於一切,對於殘疾人來說,這意味著我們的生活自動被視為可悲的依賴。”
但獨立性真的是指能夠自己刷牙,還是更多的是指能夠選擇自己的朋友?殘疾理論家和神經多樣性倡導者認為後者遠比前者重要。然而,大多數療法只教授具體的實用技能,而不是個人賦權。
當我們說“自閉症只是另一種人類存在方式”時,我們的意思是,嚴重的障礙不會改變一個人獲得尊嚴、隱私以及儘可能多的自主權的權利,無論這意味著選擇他們的職業還是選擇他們的衣服。我看到自閉症患者最糟糕的時刻經常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錄影,並在網際網路上向全世界播放,我感到非常難過。如果有人對你最痛苦的個人掙扎時刻這樣做,你可能會非常憤怒!這些孩子(和成人)無法發聲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此感到滿意。無法回答不等於同意。此外,自閉症兒童經常接受療法,教他們隱藏自己的不適,壓抑自己的個性,並且比神經典型的同齡人更聽話(或“順從”),這使他們面臨更高的欺凌和性虐待風險。
尊重神經多樣性意味著尊重非語言選擇,即使這些選擇“奇怪”或“不符合年齡”。這意味著尊重“不”字,無論是口頭說出、手語表達還是行為表現。這意味著給予使用AAC(增強和替代溝通)裝置的人與我們給予口頭交流的人相同的關注。這意味著關閉AAC裝置相當於用膠帶封住透過說話交流的孩子的嘴。這意味著不要用高音調的娃娃語與10歲的孩子說話,即使那個10歲的孩子仍然穿著尿布,嘴裡塞著沙子。永遠不要讓孩子聽到自己被描述為“太難管教”、“可憐”、“謎題”或“太落後”,無論她看起來多麼不理解。無法回應並不意味著無法理解,正如我們從卡莉·弗萊施曼和伊多·凱達爾等自我倡導者那裡多次聽到的那樣。
巴倫-科恩提到“社交困難”是自閉症的一種殘疾,對於許多自閉症患者來說,他們的社交掙扎確實是致殘的。但這只是不完整的畫面。一些自閉症患者確實更喜歡獨處。許多自閉症患者與其他自閉症患者的社交比與典型的同齡人更好,因此也許我們不應該僅僅根據他們與神經典型人士的互動來判斷他們的社交技能。而且,也許最重要的是,自閉症患者面臨的最大社交困難之一是神經典型人士不願與他們認為“不同”的人互動。
這是一個為自閉症患者由非自閉症患者造成的社會問題,而不是自閉症中的社會殘疾。只要求自閉症患者改變他們的社交方式,就像要求少數族裔像白人一樣說話和穿著才能被接受一樣。這是一種非常糟糕的對抗偏見的方式,無論是種族偏見還是神經偏見。
現在更多的人使用神經多樣性的語言,談論接受和支援自閉症差異。不幸的是,無論他們如何措辭,大多數自閉症療法仍然堅持將“更典型的行為”作為成功的黃金標準。即使許多自閉症成年人警告說,偽裝正常的壓力通常會導致抑鬱、倦怠甚至退化,即使在療法被宣佈成功多年之後。尊重神經多樣性意味著不要堅持目光接觸,因為自閉症患者已經(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地)宣告,目光接觸是如此困難、如此令人難以承受和如此有壓力,以至於它會破壞他們的注意力。
“安靜的手”或任何時候強迫自閉症兒童以犧牲他們智力發展或個人成長所需的精力為代價來表現得更典型,也是如此。研究最終證實了自閉症患者幾十年來所說的話:當教導照顧者而不是兒童以不同的方式表現時,我們會獲得更好的結果。可悲的是,研究人員和治療公司常常忽視自閉症患者的觀點。
以神經多樣性的角度思考意味著挑戰“假裝遊戲是必要的”這一假設,僅僅因為這是神經典型兒童所做的。雖然典型的孩子透過動手、逐步的方法學習,但許多自閉症兒童最好透過長時間觀察,然後再嘗試一項新技能來學習。正如視覺學習者或聽覺學習者應該被允許使用最適合他們的學習方法一樣,自閉症兒童也應該如此。我們應該尊重他們通常以與典型孩子不同的順序學習事物,並停止在神經典型發展時間軸上跟蹤他們的進步。

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對彩色彈珠著迷。圖片來源:Aiyana Bailin
我是一名喘息服務提供者。我的服務物件包括從4歲到20歲出頭的自閉症譜系障礙(和其他發育障礙)患者。許多人是非語言或極少語言的。我相信他們都有自己的智慧,即使他們有智力障礙。我的服務物件中有人會情緒崩潰或爆發。我同情他們的挫敗感。我的服務物件中有人會咬自己或我。我確信他們這樣做絕非沒有理由。我的服務物件使用單詞、應用程式、繪畫或只是拉著我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來交流。我不想改變他們的交流方式;我想像學習第二語言一樣學習它。我的服務物件中有人會“冒充”非自閉症患者,也有人可能永遠無法獨自生活。我不會對誰的生活更充實或更愉快做出假設。
遠離“正常”會帶來掙扎,接近“正常”也會帶來掙扎——更不用說,典型的生活也絕非沒有挑戰!掙扎是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殘疾人的生活。我們許多人認為我們知道美好的生活是什麼樣的,但我們受到自身經歷的極大限制。美好的生活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事物。只要問問敘利亞難民和紐約社交名媛,他們需要什麼才能快樂。
我的服務物件很複雜,就像所有人類一樣。我的服務物件中有人會在公共場合做粗俗和不符合社會規範的事情。如果我對他們的行為感到尷尬,那是我的問題,而不是他們的問題。我的服務物件中有人會用顫抖的手輕輕撫摸我的頭髮,有人會默默地與我分享他們最喜歡的食物,有人會在我到達他們家門口時拍打、跳躍和尖叫著表達興奮。我不會用任何東西來換取他們拍打的手和閃亮的眼睛。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很美好。
我的服務物件通常有障礙。我的服務物件通常是殘疾人。我的服務物件都很酷且有趣。我的一些服務物件會注意到別人忽略的事情。有些人不用語言也能雄辯地交流。有些人只用一兩個詞就能講笑話。有些人擁有記憶、工程和音樂方面的技能,這讓我羨慕不已。您可能會對哪些描述屬於哪些服務物件感到非常驚訝。
尊重神經多樣性意味著挑戰關於什麼是智力以及如何衡量智力的假設。這意味著提醒我們自己,僅僅因為一個人不能說話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在聽。這意味著不要要求某人先證明他們的智力,然後再以適合年齡的方式與他們交談或為他們提供智力刺激的機會。這意味著記住,身心之間可能存在巨大的脫節,並且一個人的行為可能並不反映他們的意圖,尤其是在他們感到不知所措或沮喪時。
尊重神經多樣性意味著專業界需要為幾十年來錯誤地堅稱自閉症患者缺乏情感或同理心,以及由於神經典型觀察者的這些錯誤而對自閉症患者造成的(並且仍在造成)身心傷害道歉。這意味著詢問某些“弱點”是否真的是偽裝的優勢。這意味著始終詢問“這項活動/技能/行為目標實際上是必要的,還是隻是正常的?”以及“我們成年人可以做些什麼不同的事情,讓我們的孩子不必這樣做?”
我懷疑父母們在想,“但我必須教我的孩子如何在世上生存!我可能願意為他們改變,但其他人不會。”是的,您可以努力教您的孩子您所在社會的規則,而無需讓這些課程佔據他們的生活。學校的孩子必須舉手等待發言,但我們不要求在家這樣做。練習樂器很累,所以我們不會要求幼兒一次練習幾個小時。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表現正常”。
這是一項工作,而且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不要總是要求這樣做。承認這通常很困難,有時甚至非常痛苦。問問自己,您會允許對非殘疾兒童做什麼。您會允許治療師因她咬指甲而對她進行身體約束嗎?在她配合之前藏起他最喜歡的食物?如果這對神經典型的孩子來說是不可以的,那麼對自閉症的孩子來說也是不可以的。
尊重神經多樣性意味著傾聽自閉症成年人的意見,並在他們告訴我們融入社會的心理代價通常超過收益時認真對待他們。這意味著接受有些孩子會學會寫作但永遠不會說話,或者總是比禮儀更懂音樂,或者永遠不會對運動感興趣,或者不認同二元性別;並且這個世界有空間欣賞和慶祝所有這些人的本來面目,無論他們需要多少幫助。這樣做使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都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