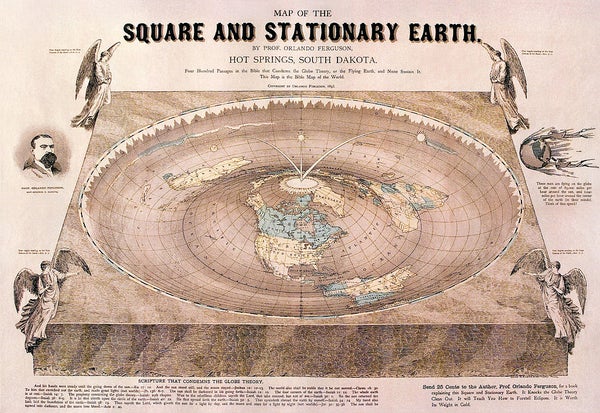本文發表在《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中,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在 2004 年獲得奧斯卡獎的劇情片《杯酒人生》中,保羅·吉亞瑪提飾演的角色是一位葡萄酒愛好者,他明確表示不喜歡梅洛。他更喜歡黑皮諾。在影片中一個令人難忘的場景中,在一家餐廳外的一場爭吵中,一位明顯心煩意亂的吉亞瑪提尖叫道:“如果有人點梅洛,我就離開。我不會喝任何[髒話]梅洛!”
電影上映後,梅洛的價格和整體銷量大幅下降,而黑皮諾的價格則飛速上漲。許多評論員——和研究人員——都將這些變化至少部分歸因於這部電影的成功。當被問及他實際上更喜歡哪種葡萄酒時,吉亞瑪提承認他更喜歡啤酒。
醫療保健領域的討論往往也顯得同樣反覆無常——關於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科學問題的公開討論,是由那些不熟悉其評論的潛在益處和後果的人所推動的。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關於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例如,考慮一下 2009 年 8 月,莎拉·佩林猛烈抨擊奧巴馬的“死亡小組”,指的是擬議的醫療改革法案中關於臨終諮詢付款的條款。一週之內,該條款從參議院法案中刪除,整個改革努力都岌岌可危。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美國主要報紙發表了超過700 篇文章討論此事,而且近 90% 的美國人聽說過“死亡小組”。
去年冬天,美國爆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麻疹疫情,此前一些政客和名人聲稱,針對這種和其他危險疾病的疫苗會導致自閉症,儘管沒有任何科學證據支援這一說法——儘管任何醫生(也許除了兩位競選總統的人)都會告訴你並非如此)。
也有一些更積極的例子。2000 年,凱蒂·柯麗克在電視直播中接受了結腸鏡檢查後,結腸鏡檢查率在隨後的幾個月裡增加了 20% 以上,並且在節目播出後近一年內保持了較高水平。最近,《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揭露了圖靈製藥公司決定將達拉匹林(一種用於治療嚴重寄生蟲感染的藥物)的價格提高 4000% 以上。在公眾強烈反對的情況下,該公司的執行長(含糊且不情願地)承諾降低藥品價格。
所有這些案例都指向一個根本問題:向公眾傳播科學是強大的,而且具有潛在的危險性——但我們對如何做到這一點知之甚少。我們不知道該說什麼或如何說。我們更不知道公眾隨後對科學問題的理解以及他們願意如何處理它。當今許多最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都深深植根於科學,但到目前為止,我們產生科學知識的能力已經超過了我們傳播知識的能力。
有些人會認為我們需要訓練科學家成為更好的傳播者。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科學家能夠有效地溝通,也許不足為奇的是,公眾和科學界在氣候變化、轉基因食品、免疫接種和進化等問題上仍然持有非常不同的觀點。最近對頂級神經科學專案的分析發現,沒有一個專案要求開設科學傳播課程。其他研究表明,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系的教師比科學技術領域的同事更傾向於與公眾互動。
科學傳播方面的指導很重要,但不完整。公眾對複雜且帶有情感色彩的科學問題的反應過於複雜,無法簡單地透過“限制術語”、“使用短句”和“從軼事開始”的建議來有意義地解決。我們需要學會如何在不聳人聽聞的情況下參與,如何在不欺騙的情況下著迷,如何在堅持基礎科學的同時吸引人。然而,同樣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框架來反駁科學討論中普遍存在的錯誤和誤導性說法——這歸因於網際網路的科學資訊(和觀點)民主化,它帶來了自身的好處和挑戰。
最終,科學家和非科學傳播者都需要更深入地瞭解有效科學傳播的過程以及公眾理解和情緒方面的傳播結果。我們幾乎沒有關於特定的印刷、電視或網際網路報道如何影響公眾對科學問題的看法的任何資料。我們不知道公眾對個人故事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臨床試驗和科學突破的媒體報道有何反應;煽動性介紹、名人地位或感知到的科學專業知識的影響是什麼;不平衡的媒體報道與虛假等價性相比如何;不同的子群體如何對不同的媒體形式和介紹風格做出反應。
這種知識的缺乏部分是因為這些趨勢很難研究——部分是因為我們沒有盡力去研究它們。我們所知道的是,美國人獲取科學資訊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2010 年,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將網際網路作為其科學資訊的主要來源;現在這個數字已經翻了一番,而且只會繼續增長。如今,印刷和電視新聞機構不太可能聘用全職科學記者,並且正在減少對科學部門的資源投入,這引發了人們對報道質量和深度的擔憂。
那麼應該怎麼做呢?一個重要的第一步是將更多的研究注意力和資金投入到科學傳播的科學研究中。政府和私人基金會應以處理經濟學、社會科學和質量改進等其他複雜問題的嚴謹態度對待科學傳播。醫學和科學領域的研究生專案應該為學生提供更多關於如何傳達他們來之不易的科學見解的指導。整個學術界應該考慮創新的方法來傳播具有公共重要性的研究,並與新聞機構建立更牢固的夥伴關係。如果目標是現實世界的影響,我們就不能再忽視利用強大的媒體聲音來促進或反駁科學證據支援的主張所蘊藏的巨大潛力。
在資訊時代,我們現在知道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資訊,而是更好地傳播資訊。更有效的溝通可能無法解決爭論,但它會推動爭論。它將我們從哲學辯論轉向戰術辯論——然後再回到更開明的哲學辯論。我們從“氣候變化是人為造成的嗎?”轉變為“解決它的最佳時間和方法是什麼?”——並最終轉變為“為了實現這些改變,我們願意做出什麼犧牲?”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曾經指出,“民主的真正保障……是教育。”今天,這意味著要對科學有更強的把握——而科學家、醫療專業人員、政策制定者和記者有責任在快速發展的媒體環境中更有效地進行溝通。我們需要認識到,通常一篇煽動性的文章會削弱一百篇學術論文的影響。
這是一個我編造的統計資料——因為我們實際上對此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