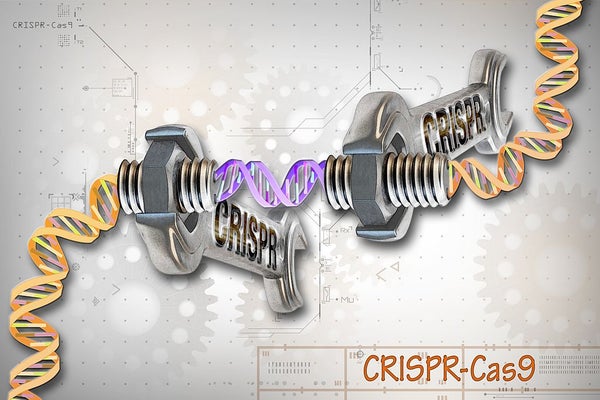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僅反映作者的觀點,不一定代表《大眾科學》的觀點
美國國家科學院和國家醫學院今天釋出了一份題為“人類基因組編輯:科學、倫理與治理”的報告,該報告探討了為人類生殖目的使用基因編輯的問題。自從基因修飾系統 Crispr-Cas9 等新的生物技術工具出現以來,這些前景已成為生動的現實。該報告建議對胚胎可遺傳的“種系”程式碼,甚至更早的上游過程(精子和卵子)的基因工程進行限制,這些程式碼會將資訊傳遞給後代。
然而,該報告似乎將公眾排除在參與之外,並得出結論:“應允許使用可遺傳的種系基因組編輯進行臨床試驗。” 他們不應該——在沒有公眾討論和更自覺地評估這如何影響社會地位、恥辱和身份,以及科學家經常傾向於形式化地引用然後迅速放棄的倫理道德的情況下,不應該允許。
該宣告是對領導層觀點的一次驚人逆轉,就在一年前的 2015 年 12 月,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家科學院舉行,我參加了這次會議,諾貝爾獎獲得者、立法者和來自全球的生物倫理學家也參加了會議,並宣佈在推進改變可遺傳程式碼之前,應達成“廣泛的社會共識”。 事實上,在峰會結束後幾周,美國立法者在一項綜合支出法案中增加了一項“附加條款”,以阻止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花費時間和金錢審查基因修飾在可遺傳程式碼上的應用。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 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與 40 多個其他國家以及歐洲委員會人權與生物醫學公約這項國際條約不同,美國並未在法律上禁止修改可遺傳程式碼,但它確實對藥物有強有力的監管框架,聯邦機構將 Crispr-Cas9 視為藥物。 但對可遺傳程式碼的限制只是暫時的,因為對 FDA 可以審查的應用的支出受到限制。
遺傳與社會中心主任馬西·達諾夫斯基指出,該報告似乎從科學家向立法者發出了“綠燈,允許繼續努力……改造傳遞給未來兒童和後代的基因和特徵”,同時指出該報告“將公眾排除在決定人類種系修飾在首位是否可接受的參與之外。”
事實上,關於我們如何確定什麼是可接受的,存在許多關鍵的論點。 首先是技術性的。 遺傳學領域絕非已經完成。 一個名為人類聚合聯盟的組織去年剛剛透露,在之前被認為是致病性的 192 個高頻基因變異中,只有 9 個可能有害——這對於任何想要重編碼其基因組的人來說都是重要的澄清。 大多數突變對生物性狀的影響非常小,而且我們對基因變異如何增強或減弱其他基因變異以及如何根據遺傳背景而不同知之甚少。
其次,正如達諾夫斯基和芝加哥洛約拉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希勒·哈克爾所指出的那樣,基因修飾與生殖技術相結合以孕育“基因關聯的兒童”並非醫學上的必要。 消極權利(即“免於”傷害的自由)與完全積極權利(即“獲得”或獲得某些好處的自由)之間存在差異。 如果基因編輯兒童是一項完全的積極權利,那麼社會將被要求為所有公民支付生育費用,對任何想要孩子的人應用基因檢測、基因修飾和體外受精技術。 重要的是,像 Crispr-Cas9 這樣的基因修飾系統的專利科學家有興趣儘可能多地出售它,這意味著不能讓科學家自己單獨負責塑造道德框架——公眾在塑造當今圍繞科學的道德規範方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 並且,隨著像 Crispr-Cas9 這樣的基因編輯系統允許我們做一些事情,比如透過編輯精子或卵子中的可遺傳程式碼來規避舊的著名事件,即改變人類胚胎,辯論變得更加細緻入微和複雜。
我們的基因組不斷發生改變,將它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是錯誤的。 基因在每一代新生命中都會被洗牌,因此基因編輯不太可能為某些家庭帶來永久性的優勢。 進化論表明,我們適應當地條件,而不是進步到更完美的形式。 但是,基因修飾會帶來“基於市場的優生學”的風險,這意味著對某些特徵賦予價值,並試圖消除其他特徵,而當有助於自閉症、神經精神疾病等多種特徵的基因變異可能與其說是疾病,不如說是存在於世界上的方式。
進化不會創造價值觀,我們才會。 而且,我們冒著將孩子塑造成我們想要擁有的商品的風險,而不是強調他們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達諾夫斯基寫道,問題在於“汙名化殘疾人,加劇現有不平等,並引入新的優生學濫用。 奇怪的是,這些可怕的風險與繼續前進的建議之間似乎沒有明顯的聯絡。” 哲學家科學家讓·羅斯坦一代人之前寫道:“科學使我們成為了神,甚至在我們配得上成為人之前。” 但那些都是專業專家。 現在是時候更多地聽取公眾對我們想法的意見了。
吉姆·科祖貝克是 《現代普羅米修斯:使用 Crispr-Cas9 編輯人類基因組》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