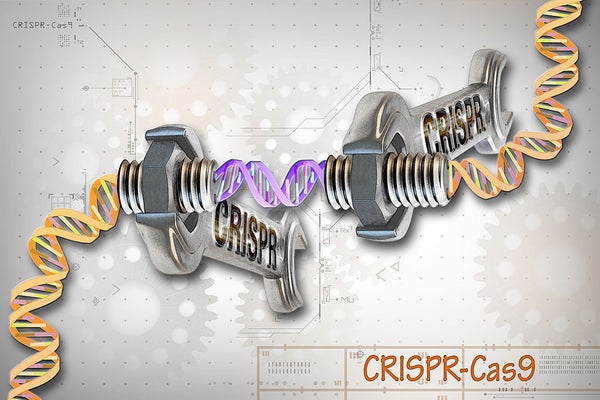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最近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封信,內容是關於 329,000 名年輕人,他們識別出 74 個基因變異——人類六十億個字母的基因組中單個核苷酸的拼寫錯誤——這些變異可用於預測完成學年的近 20% 的變異,這是一種毅力的定量特徵,與一般智力相關,您可以透過對自己的基因組進行測序來了解它。
將此作為您大學申請書的附加材料。
甚至在“分子時代”之前,我們就對錶明我們比同齡人更有價值或價值更低的蛛絲馬跡保持警惕。但學術界也告誡說,實際上我們幾乎無法利用我們的生物學來改進自身。1924 年,哈佛大學遺傳學家威廉·卡斯爾嘲諷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充其量只能讓自己顯得荒謬。我們控制優生學的能力,就像控制海洋潮汐一樣。”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輸入 Crispr-Cas9,這是第一對微小的分子剪刀,可以精確而簡單地改變 DNA 的核苷酸。如果千年之交發布的人類基因組草圖就像介紹了人類遺傳學的《Chilton 汽車維修手冊》,那麼 Crispr-Cas9 就是套筒扳手組。
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員詹姆斯·J·李是該研究的作者之一,他說:“我認為,原則上,Crispr 可以用來大幅提升胚胎的預期智力。但是“原則上”在這裡起了很大作用。一個實際障礙是,我們仍然沒有可靠的方法來確定造成這種關聯的因果位點。”換句話說,李提醒我,僅僅因為一個基因變異與一個定量特徵相關,它可能只是與該區域的另一個基因變異搭便車,而後者實際上是該效應的起因或“驅動因素”。
認知科學家史蒂文·平克告訴我:“有大量工作證實了智力的遺傳性,以及測量智力的可靠性。我們知道基因就在那裡,但由於每個基因僅佔方差的如此小一部分,因此很難精確定位。我懷疑我們會看到父母使用 Crispr 將其中任何一個植入他們的孩子體內,這有很多實際原因——基因太多,每個基因的效果都很小,我們不知道哪些基因具有負面的多效性效應(這意味著當與不同人的不同遺傳背景結合時,它們可能會導致較弱的效果),而且允許該程式的安全障礙幾乎肯定太大了。”
Crispr-Cas9 的安全性和準確性正在快速提高。人們正在發現和選擇新的蛋白質,這些蛋白質使該工具更加準確,並且不太可能引起“脫靶效應”,這意味著對細胞中不同鄰域的基因的意外編輯或破壞。由於我們每個人的基因組都是特有的,只有一點點獨特,因此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確定基因組編輯不會發生在與預期目標高度相似的位點。但是技術改進意味著該技術越來越接近被接受為一種工具,而且我們對基因靶點的瞭解也越來越精確。
科學家史蒂夫·古蘭斯曾撰寫過關於基因增強或基因興奮劑的文章,基因興奮劑在職業體育界廣為人知。他說:“對我們自己的身體做些什麼似乎是許多人願意做的事情。基因興奮劑在法律和道德結構方面是一個不確定領域。不確定誰是這個領域的思想領袖。我相信,人們對安全性的擔憂仍然太多,無法進行任何增強。一旦每個人都克服了安全問題,一切都將變得不可預測。”
生物倫理學家朱利安·薩夫列斯庫和約翰·哈里斯認為,操縱我們未來孩子的遺傳密碼不僅是權利,而且是義務,這一概念被稱為“生育仁慈”,並將父母忽視的術語擴充套件到“基因忽視”,如果我們不進行基因工程改造。相比之下,生物倫理學家希勒·哈克指出,成為人類不僅僅是基因。包括新墨西哥大學學者戴維·科雷亞在內的其他人則預想了反烏托邦式的結局,他們認為富人可能會利用基因工程將權力從社會領域轉化為基因組的持久程式碼,有效地作為“遺產基因”,建立“永久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
但是,無論我們將什麼改變編碼到我們的基因組中,最終都會在後代中與不同的遺傳背景發生衝突,這是由於染色體中的隨機重排造成的,因此它不太可能固定任何永久關係。
也許更重要的是,智力不是一個簡單的輸入-輸出系統,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發展起來的能力,可以記住並在兩個或多個對立的想法之間切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記憶能力。關於我們擁有哪些型別的智力,也存在疑問,是技術科學智力最容易轉化為現代社會的收入,還是導致小說和藝術創作的那種苦苦掙扎的創造性智力。對於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的事實,有條理地思考可能需要一種不安全感。戴維·福斯特·華萊士展示了一種探究智力本質的方式,以及它可能是多麼令人不安,當他反思最困擾他的問題時:“什麼是數字?”
事實上,沒有優越的基因,只有在權衡其他劣勢的情況下提供優勢的基因。例如,COMT 基因編碼兒茶酚-O-甲基轉移酶,該酶參與前額葉皮層和顳葉皮層中多巴胺的降解。擁有兩個突變複製的人的 COMT 活性增加四倍,而如果你的活性較低,你可能會有更好的注意力,但也更容易緊張。1995 年,阿諾德·路德維希報告稱,傑出小說作家中有 77% 患有精神疾病。喬納森·戈特沙爾指出,作家患躁鬱症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 10 倍,詩人是普通人的 40 倍。
研究創造力與瘋狂之間聯絡的心理學家報告說,情緒動盪與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關,超過這個程度,過多的慢性壓力會導致創造力下降,這個概念被廣泛稱為“倒 U 形”。但這同時也告訴我們,壓力以深刻的方式影響智力,智力不是被編碼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透過奮鬥和構建而成的。“我的智力——無論我稱我的智力為什麼——都是由那個 26 歲到 36 歲之間不停閱讀的孩子組裝起來的,”作家朱諾·迪亞茲告訴《童軍》雜誌。“那個孩子建造了我目前聲稱擁有的這座大廈。”
約翰·戈登在他 1999 年的論文《人類基因增強》中表達了他對我們是否會使用基因來改善我們的大腦的巨大懷疑。“要理解透過基因轉移來操縱智力的艱鉅任務,一個有用的方法是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單個小腦浦肯野細胞可能擁有的突觸比人類基因組中的基因總數還要多。小腦中有數千萬個浦肯野細胞,而這些細胞僅參與大腦功能的一個方面:運動協調。基因組僅為大腦的形成提供藍圖;組裝和智力發展的更精細細節超出了直接的基因控制範圍,並且必然會受到無數隨機和環境影響。”
如果歷史可以作為任何指標,那麼改變我們大腦的意願是不可避免的。1999 年,喬·錢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報告說,他們透過基因工程改造出了記憶力更好的小鼠,震驚了世界。他們透過在小鼠基因組中新增一個額外的 NR2B 基因複製來實現這一效果。該基因編碼 NMDA 受體,該受體用於記憶形成,並且可以影響神經科學家稱之為“長時程增強”的特性。媒體將超聰明的小鼠幼崽稱為“杜吉小鼠”,以當時正在聯播的熱門電視節目《天才小醫生杜吉》(Doogie Hauser MD) 命名。當時,錢說,如果它在人類身上奏效,每個人都會想使用它,因為“每個人都想變得聰明”。
丹尼爾·凱斯在幾十年前的 1966 年出版的《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一書中預見到了錢的實驗。這本書透過查理·戈登撰寫的進度報告展開,查理·戈登是一位 32 歲的麵包店工人,智商為 70,在沃倫州立家庭和培訓學校長大。查理用拼寫錯誤的單詞和不完整的句子向讀者解釋說,科學家告訴他,他們已經找到了一種快速提高他智力的方法。事實上,他們說,他們已經改造了一隻名叫阿爾吉儂的小鼠,使其變得非常聰明。
查理的智商最終飆升至 186。隨著智力發展超過情感發展,他與人際關係作鬥爭。他在麵包店工作的同事開始怨恨他。在他與愛慕物件艾麗斯交往期間,他開始接近她,但感覺到“老查理”就在附近。他變得太過於自覺而無法接近她。她聲稱他只想談論“文化變體、新布林數學和後符號邏輯”。因此,他的性格被分為對立的兩半,他努力調和自己敏銳的洞察力與滯後的情感發展。
查理決定:“智力是人類最偉大的天賦之一。但對知識的追求往往會驅逐對愛的追求。這是我最近為自己發現的另一件事。我將其作為一個假設呈現給您:沒有給予和接受愛的能力的智力會導致精神和道德崩潰、神經官能症,甚至可能是精神病。”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