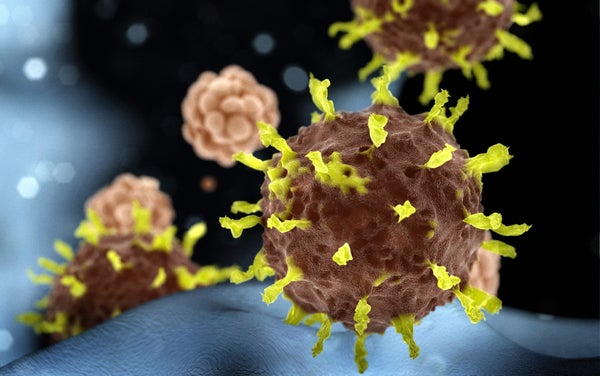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我正在從流感中康復,所以最近比平時花了更多時間獨處,發燒的頭腦中浮現出奇怪的想法。最近,關於托馬斯·庫恩、艾滋病否認論、喬治·布什、埃羅爾·莫里斯、特朗普,當然還有新型冠狀病毒的一系列不同想法以一種方式聚集在一起,這讓我想到:部落格文章!
我將從庫恩開始。他是科學哲學家,在他的 1962 年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認為,科學永遠無法實現絕對的客觀真理。現實是不可知的,永遠隱藏在我們假設、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定義或“正規化”的面紗之後。至少我以為庫恩是這樣認為的,但他的著作太晦澀難懂,我無法確定。1991 年我採訪他時,我決心弄清楚他到底有多麼懷疑。
事實證明,真的很懷疑。我們在庫恩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裡談了幾個小時,我發現自己堅持認為科學在某些方面是正確的。我曾對庫恩說,他的哲學適用於具有“形而上學”色彩的領域,例如量子力學,但不適用於更直接的領域,例如傳染病研究。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舉例來說,我提到了艾滋病。一些懷疑論者,尤其是病毒學家彼得·杜斯伯格,質疑所謂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 是否真的會導致艾滋病。我說,這些懷疑論者要麼是對的,要麼是錯的,而不僅僅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言背景下是對的或錯的。庫恩用力地搖了搖頭,說道
我會說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滑坡。涉及的病毒種類繁多。存在各種各樣的狀況,艾滋病只是其中一種或幾種等等……我認為當這一切水落石出時,你會說,天哪,我明白[杜斯伯格]為什麼會相信那樣了,而且他抓住了一些東西。我不會告訴你他是對的還是錯的。我們不再相信任何這些了。但我們也不再相信那些說這是原因的人所相信的……關於艾滋病作為一種臨床狀況是什麼以及疾病實體本身是什麼的問題不是——它是可以調整的。等等。當人們學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這些事情時,如果人們這樣做,那麼對與錯的問題將不再顯得是相關的問題。
這就是庫恩說話的典型方式。彷彿為了證明他對語言如何混淆視聽的看法,他無休止地限定自己的陳述。他似乎無法用明確的方式說些什麼。但他所說的是,即使對於像 HIV 是否會導致艾滋病這樣看似直接——而且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也無法說出“真相”是什麼。我們無法逃脫解釋、主觀性、文化背景,因此我們永遠無法說某個特定的主張是客觀上正確還是錯誤。
我稱這種觀點為極端後現代主義。我不是一個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是的,科學是一項主觀的、文化偶然性的事業,語言掩蓋的東西和揭示的東西一樣多,等等等等,但有時科學是正確的。科學發現了元素和星系、細菌和病毒,而不是發明了它們。
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後現代主義在左翼、反文化型別的人中很流行,他們將科學與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和其他不良主義聯絡起來。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極端後現代主義——尤其是所有主張都反映了主張者的利益的觀點——在右翼人士中變得更加流行。
這在喬治·W·布什政府早期變得顯而易見,當時一位高階政府官員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羅恩·蘇斯金德採訪時,公開貶低了“基於現實的社群”,他將其定義為“相信解決方案來自對可辨別現實的明智研究”的人。這位布什政府官員繼續說道,“世界真的不再那樣運轉了。我們現在是一個帝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創造了自己的現實。”
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在 2008 年奧巴馬當選後,右翼後現代主義變得更加惡毒,正如《紐約時報》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最近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回憶道。2009 年,在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機構的官員開始敦促美國人接種豬流感疫苗後,右翼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堡宣佈,“我不會接種[疫苗],正是因為你現在告訴我我必須接種。”格倫·貝克(還記得他嗎?)插話說,“如果有人現在得了豬流感,我會讓他們對我咳嗽。我會做與國土安全部所說的完全相反的事情。”唐納德·特朗普向福克斯新聞保證,流感“會消失”,並且“疫苗可能非常危險”。
根據 CDC 的資料,6000 萬美國人感染了豬流感,274,000 人住院,12,469 人死亡。哈佛大學公共政策分析師馬修·鮑姆的一項研究發現,紅色共和黨州的人們不太可能接種豬流感疫苗,因此更可能死於流感。然而,現在特朗普和林堡出於意識形態原因,正在淡化新型冠狀病毒,林堡將新型冠狀病毒比作“普通感冒”。克里斯托夫總結道,“雖然右翼吹牛大王可能會激怒民主黨人,但他們有時對自己的真正信徒構成最大的危險。”
電影製作人埃羅爾·莫里斯曾在 20 世紀 70 年代師從托馬斯·庫恩,最終憎恨他,他認為庫恩對右翼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負有部分責任。正如我之前所論證的那樣,我不相信莫里斯的假設。我反而認為,庫恩的後現代主義和右翼後現代主義代表了趨同進化的案例。特朗普對真理的蔑視並非源於挑剔的哲學辯論,而是源於極權主義強人使用的殘酷政治策略,他們宣稱真理就是他們所說的一切。我們不能因為特朗普的假新聞而責怪庫恩,就像我們不能因為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宣傳而責怪他一樣。
對於右翼後現代主義的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我真的不知道。像克里斯托夫這樣的自由派評論員的抱怨可能只會加劇這個問題,如果它們有任何影響的話。我懷疑右翼分子只有在現實——以毀滅性的流行病、乾旱、洪水或火災的形式——崛起並打在他們的臉上時,才會重新考慮他們的極端懷疑主義,彷彿在說,我以此反駁你。即使那樣也可能是不夠的,或者太晚了。
順便說一句,庫恩關於杜斯伯格最終會被認為既非正確也非錯誤的預測結果證明是,嗯,錯誤的。HIV 導致艾滋病的證據是壓倒性的,而否認 HIV/艾滋病聯絡被認為是道德上以及經驗上都是錯誤的。部分由於杜斯伯格的影響,南非政府多年來一直拒絕向其公民提供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導致超過 33 萬人不必要的死亡,根據 2008 年的一項研究。
無論我們怎麼說或怎麼想,現實都擁有最終決定權。
延伸閱讀:
哲學的意義是什麼?第 1 部分
在此處閱讀更多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資訊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