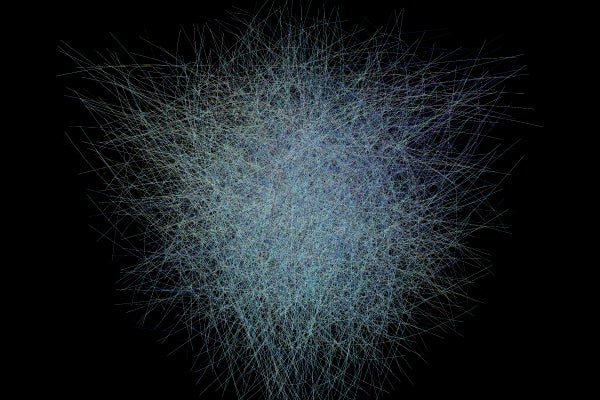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昨天,我在紐約市5月12日至15日舉行的“科學與懷疑主義東北會議”(NECSS)上發了言,這是一場“對科學和批判性思維的慶典”。我最近認識的哲學家馬西莫·皮格里ucci邀請了我,他可能對此感到後悔,因為我決定以懷疑的態度對待懷疑論者。我最初將我的演講題目定為“懷疑主義:硬目標與軟目標”。標題上方和下方文字中提到的“大腳怪”靈感來自於我在上臺前與會議主持人傑米·伊恩·斯威士的對話。他問我計劃說什麼,我告訴了他,他憤怒地為他反對相信“大腳怪”辯護。他不是在開玩笑。我沒有提到“大腳怪”,但我決定在我的演講中提到他。斯威士沒有讓我接受提問,所以我向聽眾承諾,我將在這裡釋出演講稿(略有編輯),並歡迎懷疑論者的評論或電子郵件。[另請參閱我的後續帖子此處和此處。] ——約翰·霍根
我不喜歡對皈依者佈道。如果你們是佛教徒,我會抨擊佛教。但你們是懷疑論者,所以我必須抨擊懷疑主義。
我是一名科學記者。我不讚美科學,我批評科學,因為科學需要批評家勝過啦啦隊長。我指出了科學炒作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這讓我很忙,因為,如你所知,大多數同行評議的科學主張都是錯誤的。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所以,我是一個懷疑論者,但我是小寫的“s”,而不是大寫的“S”。我不屬於懷疑論者協會。我不與那些自我認同為大寫“S”懷疑論者、無神論者或理性主義者的人混在一起。
當這樣的人聚在一起時,他們就會變得部落化。他們互相拍拍背,互相吹噓自己比部落外的人聰明。但是,加入一個部落往往會讓你變得更愚蠢。
這裡有一個例子,涉及到大寫“S”懷疑主義的兩位偶像: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和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克勞斯最近寫了一本書,名為《無中生有的宇宙》。他聲稱物理學正在回答古老的問題:為什麼存在某些東西而不是虛無?
克勞斯的書遠未實現其標題的承諾,但道金斯非常喜歡它。他在該書的後記中寫道:“如果說《物種起源》是對超自然主義最致命的打擊,那麼我們可能會將《無中生有的宇宙》視為宇宙學領域的等同之作。”
為了明確起見:道金斯將勞倫斯·克勞斯與查爾斯·達爾文相提並論。道金斯為什麼要說如此愚蠢的話?因為他非常憎恨宗教,以至於損害了他的科學判斷。他屈服於你可能會稱之為“科學妄想”的東西。
“科學妄想”在大寫“S”懷疑論者中很常見。你沒有平等地運用你的懷疑主義。你對對上帝的信仰、鬼魂、天堂、超感知覺、占星術、順勢療法和“大腳怪”持極其批判的態度。你還攻擊不相信全球變暖、疫苗和轉基因食品。
這些信仰和不相信值得批評,但它們是我所說的“軟目標”。這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你是在抨擊部落之外的人,他們會忽略你。你最終只是對皈依者佈道。
與此同時,你忽略了我所說的硬目標。這些是主要科學家和機構宣傳的可疑甚至有害的主張。在本次演講的其餘部分,我將向您展示來自物理學、醫學和生物學的硬目標示例。最後,我將對戰爭(所有目標中最硬的目標)進行一番咆哮。
多重宇宙和奇點
首先是物理學。幾十年來,像斯蒂芬·霍金、布萊恩·格林和倫納德·薩斯坎德這樣的物理學家一直吹捧弦理論和多重宇宙理論是我們對現實最深刻的描述。
問題是:弦理論和多重宇宙無法透過實驗檢測。這些理論是不可證偽的,這使得它們成為偽科學,就像占星術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樣。
一些弦理論和多重宇宙的真正信徒,如肖恩·卡羅爾,認為應該放棄可證偽性,將其作為區分科學和偽科學的方法。你輸了遊戲,所以你試圖改變規則。
物理學家甚至在宣傳這樣一種觀點,即我們的宇宙是由超級智慧外星人創造的模擬。上個月,尼爾·德格拉斯·泰森說,“我們生活在模擬中的可能性可能非常高”。再說一遍,這不是科學,而是一個假裝是科學的吸食大麻者的思想實驗。
奇點也是如此,奇點是指我們正處於數字化我們的精神並將它們上傳到計算機中的邊緣,在那裡我們可以永生。一些有權勢的人是信徒,包括谷歌的工程總監雷·庫茲韋爾。但是奇點是一種末日邪教,用科學代替了上帝。
當地位崇高的科學家宣傳像奇點和多重宇宙這樣不可靠的想法時,他們會損害科學。他們破壞了科學在諸如全球變暖等問題上的可信度。
癌症的過度檢查和過度治療
現在讓我們看看醫學,不是替代醫學的軟目標,而是主流醫學的硬目標。在關於奧巴馬醫改的辯論中,我們經常聽到美國醫學是世界上最好的。這是一個謊言。
美國人均醫療保健支出遠高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然而,我們的預期壽命卻僅排在第34位。我們與哥斯大黎加並列,哥斯大黎加的人均支出只有我們的十分之一。這怎麼會發生?也許是因為醫療保健行業將利潤置於健康之上。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醫生和醫院推出了越來越複雜、昂貴的檢查。他們向我們保證,早期發現疾病將帶來更好的健康。
但是,檢查通常弊大於利。對於每一位因乳房X光檢查發現腫瘤而延長生命的女性,有多達33位接受了不必要的治療,包括活檢、手術、放射治療和化學療法。對於男性在PSA檢查後被診斷出患有前列腺癌,這個比例是47比1。關於結腸鏡檢查和其他檢查的類似資料正在湧現。
歐洲人的癌症死亡率低於美國人,即使他們吸菸更多,癌症護理支出更少。美國人被過度檢查、過度治療和過度收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這個巨大問題的資訊,請閱讀達特茅斯大學勇敢的醫療保健分析師吉爾伯特·韋爾奇的《過度診斷》。他的副標題是“以追求健康之名使人生病”。
精神疾病的過度用藥
精神保健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精神病學已經演變成大型製藥公司的營銷分支。20多年前,我開始批評精神疾病藥物,指出像百憂解這樣的抗抑鬱藥幾乎與安慰劑一樣有效。
回想起來,我的批評太溫和了。精神科藥物在短期內對某些人有幫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總體而言,它們使人們病情加重。記者羅伯特·惠特克在他的書《流行病剖析》中得出了這個結論。
他記錄了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精神科藥物處方的大幅激增。增幅最大的是兒童。如果這些藥物真的有效,精神疾病的發病率應該下降。對吧?
相反,精神殘疾的發病率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兒童中。惠特克有力地證明了藥物正在導致這種流行病。
鑑於主流醫學的缺陷,你能責怪人們轉向替代醫學嗎?
基因奇才科學
另一個需要您關注的硬目標是行為遺傳學,它試圖尋找讓我們運轉的基因。我稱之為基因奇才科學,因為媒體和公眾都喜歡它。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遺傳學家宣佈發現了幾乎所有性狀或疾病的“基因”。我們有了上帝基因、同性戀基因、酗酒基因、戰士基因、自由派基因、智力基因、精神分裂症基因、等等。
這些將單個基因與複雜性狀或疾病聯絡起來的說法都沒有得到證實。一個都沒有!但是,基因奇才的說法層出不窮。
去年,《紐約時報》發表了兩篇由康奈爾醫學院精神病學家理查德·弗裡德曼撰寫的基因奇才文章。他聲稱科學家們發現了一種“感覺良好基因”,讓你感到快樂,以及一種“不忠基因”,讓女性對伴侶不忠。《紐約時報》應該為發表這種胡說八道而感到羞恥。
戰爭的根深蒂固理論
真正讓我惱火的生物學理論是戰爭的根深蒂固理論。根據該理論,致命的群體暴力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中。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數百萬年前,一直到我們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哈佛大學的史蒂芬·平克、理查德·蘭厄姆和愛德華·威爾遜等科學界重量級人物都在宣傳根深蒂固理論。懷疑論者邁克爾·舍默不知疲倦地宣揚這一理論,媒體也喜歡它,因為它涉及關於嗜血黑猩猩和石器時代人類的聳人聽聞的故事。
但是,壓倒性的證據表明,戰爭是一種文化創新——就像農業、宗教或奴隸制一樣——它在不到12,000年前才出現。
我討厭根深蒂固理論,不僅因為它錯了,還因為它鼓勵對戰爭的宿命論。戰爭是我們最緊迫的問題,比全球變暖、貧困、疾病或政治壓迫更緊迫。戰爭直接或間接地使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變得更糟,因為它將資源從解決這些問題上轉移開。
但是,戰爭是一個真正的硬目標。大多數人——可能包括你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世界和平是痴人說夢。也許你相信根深蒂固理論。如果戰爭是古老的和天生的,那麼它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對嗎?
你也可能認為宗教狂熱——尤其是穆斯林狂熱——是對和平的最大威脅。這是像道金斯、克勞斯、山姆·哈里斯、傑裡·科因以及已故的、偉大的戰爭販子克里斯托弗·希欽斯這樣的宗教抨擊者的說法。
我認為,美國是對和平的最大威脅。自9/11事件以來,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戰爭已造成37萬人死亡。其中包括超過21萬平民,其中許多是兒童。這些都是保守估計。
美國的行動遠未解決穆斯林武裝分子的難題,反而使情況變得更糟。“伊斯蘭國”是美國及其盟友反穆斯林暴力的反應。
美國在被我們虛偽地稱為國防上的支出幾乎與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一樣多,我們是武器的領先創新者和兜售者。承諾消除世界核武器的巴拉克·奧巴馬已經批准了一項耗資1萬億美元的計劃,用於實現我們的武庫現代化。
反戰運動非常薄弱。沒有一位真正的反戰候選人參加了這次總統競選,其中包括伯尼·桑德斯。許多美國人已經接受了他們國家的軍國主義。他們蜂擁觀看《美國狙擊手》,這部電影讚揚了一位殺害婦女和兒童的兇手。
在上個世紀,著名的科學家公開反對美國的軍國主義,並呼籲結束戰爭。像愛因斯坦、萊納斯·鮑林和偉大的懷疑論者卡爾·薩根這樣的科學家。他們的繼任者在哪裡?諾姆·喬姆斯基仍在抨擊美國的帝國主義,但他已經快90歲了。他需要幫助!
一些學者,如經濟學家泰勒·科文,非但沒有批評軍國主義,反而聲稱戰爭是有益的,因為它刺激了創新。這就像為奴隸制的經濟效益辯護一樣。
所以,總結一下。我要求你們這些懷疑論者少花時間抨擊像順勢療法和“大腳怪”這樣的軟目標,多花時間抨擊像多重宇宙、癌症檢查、精神科藥物和戰爭這樣的硬目標,戰爭是所有目標中最硬的目標。
我不期望你同意我對這些問題的框架。我只要求你以懷疑的態度審視自己的觀點。並問問自己:結束戰爭不應該像結束奴隸制或婦女受壓迫一樣成為一種道德義務嗎?我們怎麼能不結束戰爭呢?
更新(截至2016年5月23日)
有關對本文的更多<0xE2><0x80><0xAF>回應以及我的反駁,請閱讀我的後續帖子此處和此處。我在此處插入“更新”是因為我對特別重要的回應做出了回應,並且我想最大限度地提高讀者人數。
我對史蒂芬·平克的回應
“史蒂夫·平克駁斥了約翰·霍根對戰爭的看法。” 這是傑裡·科因的部落格《為什麼進化是真的》對我發起的第四次攻擊。我非常尊重平克。在《Slate》雜誌的一篇評論中,我稱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該書記錄了戰爭和其他形式暴力的歷史性下降)是一項“不朽的成就”,它“應該使悲觀主義者更難堅持他們對未來的悲觀願景”。但我也批評平克接受了一種霍布斯式的觀點,即文明,特別是以西方後啟蒙運動國家為代表的文明,正在幫助我們克服野蠻的天性。這種意識形態的承諾導致平克誇大了史前人類的暴力行為,並淡化了現代國家,特別是美國,所犯下的暴力行為。
還有一點:平克說我“認可了不合邏輯的推論”,即如果戰爭是天生的,那麼它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所知,因為我曾與他討論過這個問題,我並不“認可”這種宿命論觀點,而且我也知道平克也不認可。但是,許多其他人都是根深蒂固的宿命論者,從我的學生到巴拉克·奧巴馬,後者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說戰爭“與第一個人一起出現”,“我們將在我們的一生中無法根除暴力衝突”。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平克和其他著名科學家繼續傳播戰爭的根深蒂固理論感到如此不安,儘管它缺乏經驗支援。(有關對平克作品的更詳細批評,請參閱此處、此處和此處。此外,如果您對平克提到的拿破崙·夏農事件感到好奇,請參閱此處。)
我對大衛·戈爾斯基和史蒂文·諾維拉(最新)的回應
由於大衛·戈爾斯基繼續在網上抨擊我,我更仔細地研究了他和他的醫生懷疑論者同事史蒂文·諾維拉的文章。正如他們在他們的部落格“循證醫學”上的最新帖子清楚表明的那樣,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替代醫學,他們對替代醫學進行了積極的攻擊,這是理所當然的。
問題在於,他們在批評主流醫學方面不夠積極,他們傾向於保護主流醫學。戈爾斯基和諾維拉無疑擔心,承認主流醫學的缺陷會為江湖騙子提供幫助和安慰,但他們最終堅持雙重標準,這損害了他們的可信度。
當戈爾斯基和諾維拉駁斥精神科藥物可能弊大於利的證據,以及當戈爾斯基淡化最近一項關於醫療錯誤導致的死亡的研究時,就顯示出了這種雙重標準。同樣,當乳腺癌外科醫生戈爾斯基討論乳房X光檢查時,他總是最終肯定它們的價值,儘管價值有限。
尋求對醫學進行更客觀評估的懷疑論者應該檢視寶貴的科克倫協作組織,該組織由37,000名醫學專家組成,致力於製作(根據該網站)“可信、可訪問且不受商業贊助和其他利益衝突影響的健康資訊”。
科克倫協作組織北歐分部的負責人、醫生和醫學研究員彼得·哥特捨得出的結論是,乳房X光檢查和抗抑鬱藥可能弊大於利。哥特舍是一位真正的懷疑論者。他不一定是對的,但我更信任他的判斷,而不是戈爾斯基和諾維拉的判斷。
延伸閱讀:
人文科學應該擁抱科學主義嗎?我對平克居高臨下的懇求的後現代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