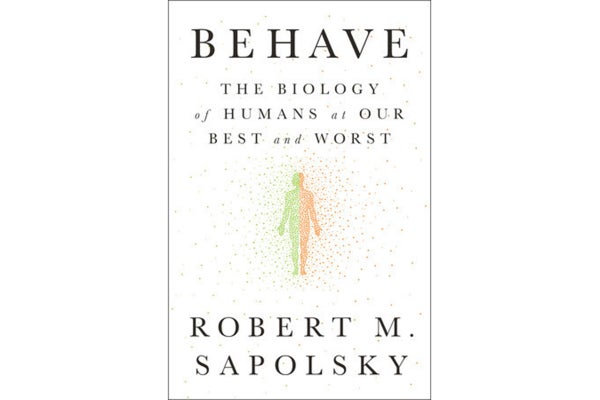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僅反映作者的觀點,不一定代表《大眾科學》的觀點
當一位科學家拒絕承認使其成名的理論中的缺陷時,事情可能會變得難堪。哈佛大學人類學家理查德·蘭厄姆是黑猩猩行為專家,他因主張戰爭(定義為一群人對另一群人實施的暴力)是古老且與生俱來的,源於自然選擇在我們身上培養的本能而聞名。我稱這種說法為戰爭的深根理論。
在他1996年出版的影響深遠的著作《惡魔般的雄性》(與一位記者合著)中,蘭厄姆斷言,我們好戰的方式可以追溯到數百萬年前,與我們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有關,黑猩猩也和我們一樣容易產生群體攻擊性。
蘭厄姆寫道:“類似黑猩猩的暴力”先於人類戰爭併為其鋪平了道路,使現代人類成為持續五百萬年致命侵略習慣中茫然的倖存者。”隨著反對這一說法的證據越來越多,蘭厄姆積極地為它辯護,指責批評者是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而非科學動機。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事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他對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羅伯特·薩波爾斯基也使用了這種策略,薩波爾斯基數十年來一直在東非研究狒狒。薩波爾斯基是我們最聰明、最雄辯的科學傳播者之一,並且是對粗糙的生物決定論的有力制衡,而這種決定論在關於人類行為的流行說法中普遍存在。
薩波爾斯基的新書《行為:人類處於最佳和最壞狀態的生物學》是一部790頁的鉅著。他深入探討了科學可以告訴我們關於暴力和侵略以及合作和同情的原因。雖然他“天生”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研究使他相信,對人類的未來,特別是對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前景,“存在樂觀的空間”。
蘭厄姆在《紐約時報》上評論行為時,以積極的口吻開篇,稱其為“心理學和神經生物學的一部古怪、固執己見且權威的綜合著作”和“你會在大學裡後悔沒有讀過的教科書”。他甚至讚揚薩波爾斯基提醒人們基因和生物學之間的聯絡很少是直截了當的。
然後蘭厄姆發起了攻擊。他稱薩波爾斯基“不平衡”和“黨派批評家”,因為他拒絕接受戰爭的深根理論。蘭厄姆寫道,薩波爾斯基對更美好世界的希望是“華而不實”。(斜體字為後加)。這種指責是令人憤慨的。如果說有人在欺騙他的聽眾,那就是蘭厄姆。
蘭厄姆忽略了提及,而一個誠實的評論家應該提及的是,薩波爾斯基特別點名批評了他。薩波爾斯基提到17世紀的學者將文明前的生活描述為“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他將《惡魔般的雄性》描述為“徹頭徹尾的霍布斯主義”。他指責蘭厄姆“斷章取義”地選取支援深根理論的資料。
蘭厄姆還具有欺騙性地暗示,薩波爾斯基對深根理論的懷疑是基於“當代狩獵採集者之間暴力發生率低”。實際上,薩波爾斯基仔細篩選了與戰爭起源相關的多種證據來源,包括對靈長類動物和史前狩獵採集者的研究。後一種資料尤其重要,因為我們的祖先在開始定居和務農之前一直以狩獵採集為生。
薩波爾斯基指出,對倭黑猩猩、大猩猩和其他靈長類動物的觀察與深根論點相矛盾。為了強調攻擊性的可塑性,他講述了他自1980年代以來追蹤的一個狒狒群體的故事,該群體的攻擊性行為急劇減少。
他指出,以暴力聞名的亞馬遜部落民族亞諾瑪米人不是狩獵採集者,而且男性亞諾瑪米人的暴力行為與生殖成功之間的相關性被高估了。他引用了人類學家道格拉斯·弗萊、布萊恩·弗格森和其他人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人類史前時期的暴力發生率很低。他指出,最古老的群體暴力明確證據是一個不超過14000年的萬人坑。
薩波爾斯基總結道:“在數十萬年中居住在地球上的狩獵採集者可能不是天使,完全有可能犯下謀殺罪。然而,‘戰爭’——無論是困擾我們現代世界的意義,還是困擾我們祖先的簡化意義——在大多數人類放棄遊牧狩獵採集生活方式之前,似乎都是罕見的。”
為什麼關於深根理論的辯論很重要?因為許多人,包括一些身居要職的人,認為如果戰爭是古老且與生俱來的,那麼它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2009年RadioLab的一集》探討了這一命題,薩波爾斯基、蘭厄姆和我對此做出了貢獻。有關此問題的更近期的討論,請參閱上週釋出在本網站上的一篇文章,“骯髒、野蠻而短暫:人類的DNA是否天生就 склонны 殺戮?”
既然那篇文章和RadioLab的廣播都讓蘭厄姆說了算,那麼我在這裡就授予薩波爾斯基這份榮譽。他以總結他的中心思想來結束《行為》——這本書像《惡魔般的雄性》一樣細緻入微,而後者則像卡通一樣粗俗,我強烈推薦這本書:“這很複雜。”
他補充說:“似乎沒有什麼東西能引起任何東西;相反,一切都只是調節其他東西……正如意外後果法則所支配的那樣,修復一件事往往會搞砸另外十件事……最終,你可能會覺得實際上可以修復某些東西,可以使事情變得更好,這似乎是毫無希望的。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嘗試。如果你正在讀這篇文章,你可能非常適合這樣做。”
延伸閱讀:
退出原始人搏擊俱樂部:關於先天黑猩猩——更不用說人類——戰爭的證據是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