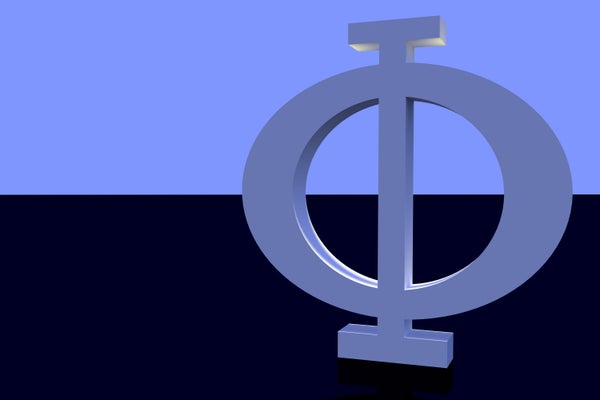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物質如何產生意識?更具體地說,物理物件如何產生像您在閱讀這句話時沉浸其中的主觀體驗?事物是如何變得有意識的? 這被稱為身心問題,或哲學家大衛·查爾默斯所說的“難題”。
我在《科學的終結》中表達了對難題無法解決的懷疑——一種被稱為神秘主義的立場。 我在新版中辯稱,我的悲觀情緒已被泛心論近期的流行所證實。這種古老的學說認為,意識不僅是大腦的屬性,也是所有物質的屬性,例如我的桌子和咖啡杯。
泛心論在我看來顯然是愚蠢的,但並非愚蠢的人——尤其是查爾默斯和神經科學家克里斯托夫·科赫——正在認真對待它。這怎麼可能?是什麼引起了他們的興趣?我是否過於草率地否定了泛心論?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這些問題吸引我參加了上個月在紐約大學舉行的為期兩天的整合資訊理論研討會。 IIT 由神經科學家朱利奧·託諾尼(師從已故的傑拉爾德·埃德爾曼)構思,是一種極其雄心勃勃的意識理論。它適用於所有形式的物質,而不僅僅是大腦,並且暗示泛心論可能是真的。科赫和其他人認真對待泛心論,是因為他們認真對待 IIT。
在研討會上,查爾默斯、託諾尼、科赫和其他十位演講者介紹了他們對 IIT 的看法,然後由大約 30 位其他科學家和哲學家進行了辯論。我仍在思考這些主張和反駁,其中一些主張和反駁非常抽象和數學化。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嘗試根據研討會和我的閱讀來評估 IIT。如果我犯了一些錯誤,這是極有可能的,我相信研討會參與者會讓我知道。
難以理解的問題
IIT 提出的一個挑戰是晦澀難懂。通俗的解釋通常讓我懷疑我遺漏了什麼。 例如,請參閱卡爾·齊默在《紐約時報》上 2010 年的報道、科赫在 2009 年《大眾科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意識的‘複雜’理論”,或他 2012 年出版的書籍《意識》。該理論的核心主張是,如果一個系統擁有一種名為 Φ 或 phi 的屬性,它就是有意識的,phi 是衡量系統“整合資訊”的指標。
Phi 對應於系統中不同部分之間的反饋和相互依賴性。在《意識》中,科赫將 phi 等同於“協同作用”,即一個系統“大於其各部分之和”的程度。 Phi 可以是任何實體(生物或非生物)的屬性。 即使質子也可以擁有 phi,因為質子是其夸克相互作用產生的湧現現象。 因此,泛心論。
另一個關鍵短語是“概念結構”,它似乎對應於資訊在特定時刻在特定系統中體現和處理的方式。 概念結構,我將其設想為電路圖或流程圖,決定——或者更確切地說,就是——有意識的體驗。
託諾尼在紐約大學研討會上開始了關於 IIT 的 90 分鐘教程,隨後科赫又講了一個小時。 他們的演講與他們 2015 年關於 IIT 的論文“意識:無處不在?”相呼應。 雖然這篇論文有一些異想天開的段落(標題呼應了一首老披頭士樂隊的歌曲),但這段摘錄傳達了 IIT 令人望而生畏的密集性
……IIT 的核心身份可以很簡單地表述為:一種體驗等同於一種在本質上最大程度不可簡化的概念結構。 更準確地說,一個概念結構完整地指定了體驗的數量和質量:系統存在的程度——意識的數量或水平——由其 Φmax 值衡量——概念結構的內在不可簡化性; 其存在的方向——意識的質量或內容——由概念結構的形狀指定。 如果一個系統的 Φmax = 0,這意味著其因果能力完全可以簡化為其各部分的能力,那麼它就不能聲稱存在。 如果 Φmax > 0,則系統無法簡化為其各部分,因此它自身存在。 更一般地說,Φmax 越大,系統就越能比 Φmax 較低的系統更充分地聲稱存在。 根據 IIT,體驗的數量和質量是處於某種狀態的機制複合體的內在基本屬性——以特定方式告知或塑造可能性空間(過去和未來狀態)的屬性,正如質量被認為是內在的,可以彎曲其周圍的時空一樣。
託諾尼和科赫在引用 IIT 的經驗證據時最為清晰。 小腦似乎比其他神經區域具有更少的內部連線——因此 phi 更低——,在小腦受損的情況下,意識不會受到顯著影響。 此外,對癱瘓、無法溝通、“閉鎖”患者的腦部掃描顯示,那些表現出其他意識跡象的患者的 phi 更高。
但是,託諾尼、科赫和其他人談論資訊、整合和概念結構越多,我就越不理解這些概念。 我還想知道科學家如何測量大腦的 phi 或整合資訊,因為他們不瞭解大腦如何編碼資訊。
當我向託諾尼坦白我的困惑時,他承認 IIT 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滲透”。 研討會上的其他人似乎也具有抗滲透性。 參與者經常要求託諾尼解決關於該理論的爭議,但他的預言式回應並不總是澄清問題。
在研討會即將結束時,有人問託諾尼,IIT 是否假設意識和物質是截然不同的現象,還是意識只是物質的副產品。 換句話說,IIT 是唯物主義還是二元論的意識理論? 託諾尼笑了笑,回答說:“它就是它本身。” (也許他的意思是,“IIT 就是 IIT 本身。”)
參與者似乎對 IIT 的一個稱為“排除”的假設特別困惑。 根據 IIT,大腦的許多組成部分——神經元、神經節、杏仁核、視覺皮層——可能具有非零 phi,因此也具有微型意識。 但是,由於整個大腦的 phi 超過了其任何組成部分的 phi,因此其意識會抑制或“排除”其組成部分的微型意識。
排除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我們不會將意識體驗為微型感覺的混亂組合,但它具有奇怪的含義。 如果一個群體(例如,IIT 研討會)的成員開始彼此痴迷地交流,以至於群體的 phi 超過了個人的 phi,則 IIT 預測該群體將變得有意識並抑制個人的意識,將他們變成無意識的“殭屍”。 從一對痴迷的夫婦到美利堅合眾國,更小或更大的群體也可能如此。
有意識的 CD 問題
當然,我可能只是太無知而無法評估 IIT。 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也讓我感到困惑,但它們表現得相當不錯。 因此,計算機科學家斯科特·阿倫森充分掌握了 IIT 的技術細節,但他對該理論表示懷疑,這一點非常重要。 阿倫森在託諾尼和科赫之後發言,稱自己是“官方的 IIT 懷疑論者”。 他補充說,“我的午餐似乎沒有被下毒,所以謝謝,”
阿倫森重申了他去年在他的部落格上提出的批評。 (另請參閱他的後續文章。)他的主要抱怨是 IIT 聲稱高 phi 會產生意識。 他說:“Phi 可能是意識的必要條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條件。”
阿倫森說,他可以設計各種簡單的資訊處理系統——例如,二維網格,執行像光碟中使用的糾錯程式碼——這些系統具有極高的 phi。 正如他在他的部落格上所說,IIT “不可避免地預測了物理系統中存在大量意識,而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會認為這些系統是特別‘有意識的’:實際上,這些系統除了應用低密度奇偶校驗碼或對其輸入資料進行其他簡單轉換之外什麼都不做。 此外,IIT 預測這些系統不僅‘稍微’有意識(這沒問題),而且它們可能比人類的意識更無限地強大。” [原文粗體。]
阿倫森還指責 IIT 的支持者為該理論辯護的方式前後矛盾。 例如,IIT 支持者引用小腦的低 phi 和缺乏意識作為該理論的證據,但他們不能確定小腦是無意識的; 他們只是根據常識做出合理的推斷。
然而,當面對阿倫森的 歸謬法 網格論證時,託諾尼接受了 荒謬; 他暗示也許網格是有意識的,並責備阿倫森訴諸常識。 阿倫森在他的部落格上反對說:“如果 IIT 預測小腦是無意識的,就將其視為 IIT 的‘成功’,同時又否認 IIT 預測 XOR 門的方形網格是有意識的,就將其視為 IIT 的‘失敗’,這是行不通的。” [原文粗體。]
在研討會上,阿倫森稱這種策略為“正面我贏,反面你輸”。 換句話說,透過在適合他們目的時訴諸常識,並在不適合時拒絕常識,IIT 支持者使他們的理論免於證偽,因此是不科學的。
儘管如此,阿倫森還是稱讚 IIT 支持者提出了一個足夠精確的理論供他測試。 正如他在他的部落格上所說,“整合資訊理論是錯誤的——出於其核心原因而可以證明是錯誤的——這一事實使其在有史以來提出的所有意識數學理論中位居前 2% 左右。 在我看來,幾乎所有競爭的意識理論都非常模糊、空洞和可塑,以至於它們只能渴望錯誤。”
迴圈性問題
託諾尼對阿倫森的批評不以為然。 他說:“我們必須做好準備,迎接極大的驚喜。” 他還暗示,阿倫森批評的是過時的 phi 版本。 託諾尼說,IIT 是“一項正在進行的工作”。
物理學家馬克斯·泰格馬克是阿倫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也是 IIT 的愛好者,他提出了六個 phi 的替代數學定義,他認為這些定義可能比阿倫森批評的版本問題更少。 阿倫森說,他的分析適用於泰格馬克和託諾尼提出的所有 phi 版本。
關於 phi 定義的爭論讓我想起了曾經流行的複雜性領域的研究人員無法就他們正在研究的內容達成一致。 正如我所指出的,複雜性至少有 40 種不同的定義——其中一些定義涉及資訊,而資訊是另一個臭名昭著的變幻莫測的概念。
這讓我想到哲學家約翰·塞爾對 IIT 的批評。 塞爾的批評不是在紐約大學研討會上(他沒有參加),而是在 2013 年《紐約書評》上對科赫的書籍《意識》的評論中提出的。 塞爾抱怨說,IIT 依賴於對資訊概念的盜用
[科赫] 並不是說資訊導致意識; 他是說某些資訊就是意識,並且因為資訊無處不在,所以意識也無處不在。 我認為,如果您仔細分析這一點,您會發現這種觀點是不連貫的。 意識獨立於觀察者。 無論任何人怎麼想,我都是有意識的。 但資訊通常是相對於觀察者的。 例如,這些句子只有相對於我們理解它們的能力才有意義。 因此,您不能透過說意識由資訊組成來解釋意識,因為資訊僅相對於意識而存在。
另請參閱隨後託諾尼、科赫和塞爾之間的交流,塞爾在交流中說 IIT“似乎不是一個嚴肅的科學提議”。 在紐約大學研討會上,託諾尼和其他 IIT 的支持者駁斥了塞爾的批評,聲稱塞爾誤解了他們對資訊的看法。 但在我看來,塞爾擊中了 IIT 的主要缺陷。
事實上,塞爾的觀點適用於其他以資訊為中心的意識理論,包括查爾默斯 20 多年前概述的一種理論(這有助於解釋他對 IIT 的親和力)。 基於資訊的意識理論是迴圈的; 也就是說,它們試圖用一個預設意識的概念——資訊——來解釋意識。
我在 2011 年的一篇文章“為什麼資訊不能成為現實的基礎”中闡述了這種擔憂。 這篇文章並非專門針對 IIT,而是針對更普遍的命題,即資訊是自然的基本屬性,與物質和能量一樣。 我將這個想法追溯到物理學家約翰·惠勒的“位元生萬物”概念,該概念的靈感來自於資訊理論和量子力學之間明顯的共鳴。 我寫道
在缺乏被告知的物件的情況下,資訊概念毫無意義——也就是說,一個能夠選擇或自由意志的有意識的觀察者(對不起,我忍不住了,自由意志是一種痴迷)。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明天都消失了,所有資訊也會消失。 缺乏令人驚訝和改變的思想,書籍、電視和計算機將像樹樁和石頭一樣愚蠢。 這個事實似乎非常明顯,但似乎被許多資訊愛好者忽視了。 認為意識與物質一樣基本——惠勒的“參與宇宙”概念暗示了這一點——也與日常經驗背道而馳。 物質顯然可以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存在,但是我們在哪裡看到意識在沒有物質的情況下存在? 朝一個人的心臟開槍,他的意識消失了,而他的物質仍然存在。
唯我論問題
此外,像所有意識理論一樣,IIT 猛烈撞擊了唯我論問題(這是阿倫森批評的核心)。 據我所知,我是宇宙中唯一有意識的實體。 我自信地推斷,像我這樣的事物——例如其他人——也是有意識的,但當我考慮不太像我的事物時,例如光碟和暗能量,我的信心就會減弱。 (在研討會上,曾就暗能量是否可能有意識進行過一次小型討論,科赫打趣道:“讓我們不要成為重子沙文主義者。”)唯我論問題對於 IIT 來說尤其尖銳,因為它的泛心論含義。
IIT 支持者已經提出了構建“意識計”的想法,該儀器可以測量任何系統(從 iPhone 到閉鎖患者)的 phi,從而測量其意識。 但這種儀器實際上不會像當前的腦部掃描那樣檢測意識。 沒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儀器可以解決唯我論問題。
總結一下:參加研討會增強了我對神秘主義的偏見。 我懷疑 IIT 能否帶領我們更接近解決身心問題,而且我預測該理論的形而上學包袱——泛心論和所有其他東西——將限制其受歡迎程度。
但我很喜歡這次研討會。 看到所有那些聰明的參與者都在努力解決存在的最深刻難題,引用笛卡爾、萊布尼茨和休謨以及不到一年前發表的論文,是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最令人興奮的智力體驗。 無論 phi 是什麼,在研討會結束時,我的大腦都充滿了它。
思考 IIT 也加深了我對身心問題的理解。 在科學主義盛行的時代,我們需要像 IIT 這樣的理論來幫助我們重新發現我們自身的神秘性。
後記:有關 IIT 研討會參與者和其他人對本文的回應,請參閱此後續文章。
延伸閱讀:
Integratedinformationtheory.org。
當我們甚至不知道“神經程式碼”時,大型腦科學新專案有意義嗎??
後後記:IIT 研討會由紐約大學的意識、大腦和意識中心(由查爾默斯和內德·布洛克共同指導)和全球高階研究所共同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