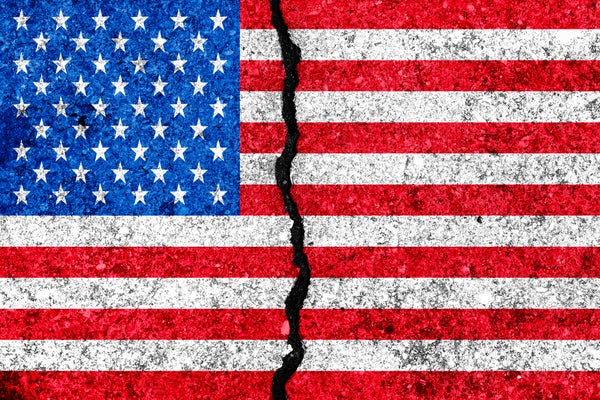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首先是‘我的一代’,然後是‘我的世代’。現在我們有經驗證據表明,我們生活在將被稱為‘混蛋時代’或‘推特時代’的時代……”——性格心理學家布倫特·羅伯茨在推特上說
“我們的運動旨在用一個由你們,美國人民,控制的新政府取代失敗和腐敗的政治建制派。... 試圖阻止我們的政治建制派,正是對我們災難性的貿易協議、大規模非法移民以及使我們國家枯竭的經濟和外交政策負責的同一批人。... 唯一能阻止這個腐敗機器的是你們。”——唐納德·特朗普為美國辯護
當今世界存在許多分歧。但有一種分歧,深深植根於人性的核心,有助於解釋許多其他分歧。我指的是人格變異的根源,它內置於我們的 DNA 中:對抗性。透過真正關注這一特質,並瞭解對抗性如何與環境條件和資訊傳遞相互作用,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瞭解當今世界最突出的分歧之一:民粹主義。
首先,讓我們深入瞭解對抗性的最新科學。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幫助確保有關塑造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對抗性的科學
人格的對抗性-宜人性維度是人格五大維度之一。與人格的其他主要維度一樣,這種特質在人群中呈正態分佈。兩個人在這個基本維度上的差異越大,另一個人的行為就越難以理解,尤其是在遵守社會規範和利他行為方面。
宜人性(對抗性的對立面)由兩個主要方面組成:禮貌和同情心。禮貌反映了遵守社會規範、避免挑釁和剝削他人的傾向,而同情心反映了在情感上關心他人的傾向。在禮貌方面得分高的人專注於公平,而在同情心方面得分高的人更專注於幫助他人,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在另一個極端,低禮貌水平的人(對抗性強的人)在攻擊性測量中往往得分很高,而低同情心水平的人在同理心測量中往往得分很差。雖然禮貌和同情心可能會分開——例如,一個人在同情心方面得分很高,但在禮貌方面得分很低——但在普通人群中,禮貌和同情心密切相關,這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宜人性的整體人格領域。
與所有其他人格變異一樣,宜人性-對抗性維度的差異也反映在大腦中。從神經學角度來看,宜人性得分高的人往往表現出預設模式腦網路的更高啟用,這與模擬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以及理解和分享他人情感體驗所必需的不同型別資訊的高階整合有關。宜人性也與情緒調節能力有關,特別是抑制攻擊性衝動和其他具有社會破壞性的情緒。從神經化學的角度來看,宜人性涉及神經遞質睪酮(與遠離禮貌和趨向對抗性的傾向有關)和催產素(與同情心和群體內社會聯絡的傾向有關)。
對抗性-宜人性維度在現實世界中具有很大的預測價值(不僅僅是在科學實驗室中)。對抗性強的人更可能做出攻擊性反應並在受到他人不公平對待時進行報復(儘管他們往往不太關心他人是否受到不公平對待)。在工作中,對抗性強的人在收到經理的憤怒講話後表現優於高度宜人的人(這會激發他們),而高度宜人的人在經理表達對他們表現的滿意後往往會提高他們的表現。
這種人格維度對政治也具有深刻的意義。更具對抗性的政治家獲得更多媒體關注,並且比更宜人的政治家更常當選。在普通人群中,對抗性強的人更可能不信任政治,相信陰謀論,並支援分裂主義運動。
對抗性並非絕對的好或壞。丹尼爾·內特爾推測所有人格特質的進化都具有權衡取捨,這就是人格變異存在的原因。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宜人性既有好處(關注他人的心理狀態;和諧的人際關係,有價值的聯盟夥伴關係),也有代價(容易受到社會欺騙和剝削;未能最大化自私的優勢)。然而,由於這種特質存在如此廣泛的變異,高度對抗性的領導人可以透過他們的言辭和資訊傳遞來喚起和影響大量在這種特質上得分很高的人。
對抗性與民粹主義的共鳴
心理學界越來越認識到,人格特質與領導人的資訊傳遞相互作用。吉安·卡普拉拉和菲利普·津巴多指出,“政治家的關鍵技能是……透過識別和傳達在特定時間對特定選區最具吸引力的個人特徵,來說‘人格語言’”。他們發現選民會選擇與其自身人格相匹配的政治家。
帕蒂·瓦爾肯堡和喬亨·彼得也提出了他們的媒體效應差異易感性模型(DSMM),該模型認為,資訊的措辭和框架對具有特定性格的人比對其他人具有更大的認知和情感影響。例如,希望的資訊可能對那些更容易體驗積極情感和熱情的人更具吸引力,而變革的資訊可能在那些願意承擔風險的人中更具吸引力。
然而,也許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互動是對抗性與民粹主義之間的互動。民粹主義的核心特徵是反建制資訊和對人民中心重要性的關注。反建制資訊將政治精英描繪成腐敗和邪惡,並且對“純潔人民”的利益漠不關心。約翰·朱迪斯和魯伊·特謝拉認為,民粹主義者的本質分歧是“人民與當權者”。
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政治傳播學教授伯特·巴克及其同事對以下問題進行了規模最大、最系統的調查:當對抗性公民收到反建制資訊時會發生什麼?他們發現,民粹主義者的反建制資訊最能引起高度對抗性人群的共鳴,這一觀點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援。這一發現在三大洲的七個國家得到證實。對抗性預示著對右翼(特朗普、英國獨立黨、丹麥人民黨、自由黨、瑞士人民黨)和左翼(波德莫斯、查韋斯)民粹主義者的支援。
他們還使用生理測量方法,確定了這種聯絡背後的更深層次的情感過程。研究人員使用皮膚電導測量(捕捉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發現人們對與其人格相符的政治資訊反應的喚醒程度有所提高。特別是,對抗性強的人發現反建制資訊令人興奮,而高度宜人的人則發現親建制資訊令人興奮。
這很重要,因為情緒在決定政治溝通如何影響我們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那些更容易被特定資訊喚醒的人更有可能記住它,並在長期內再次尋求該資訊。這些發現表明,政治家可以透過提供與選民人格產生情感共鳴的資訊來對選民施加重大影響。
他們還研究了威權主義。威權主義概括了對社會秩序、結構和服從的偏好。先前的研究表明,高度威權主義者對外群體成員表現出較少的容忍度,並支援具有右翼意識形態的民粹主義政黨。與此一致,巴克及其同事發現,雖然威權主義並不能預測反建制資訊,但它確實能預測對特朗普和英國獨立黨的支援,以及對任何持有強烈反移民立場的候選人的支援。這些發現表明,民粹主義還有第二條途徑,即透過與右翼民粹主義相關的特定意識形態。
對抗性-宜人性分歧的意義
這些天似乎有些不同尋常。根據您的觀點(和個性),事情要麼更“險惡”,要麼更“革命性”。但我認為我們都可以同意,僅僅在過去幾年裡,政治格局和話語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直存在黨派分歧,但似乎有一種不同型別的分歧更加突出,即人民與政治家之間的分歧。正如荷蘭政治學家卡斯·穆德指出,“如今,民粹主義話語已成為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的主流。”
重要的是要強調,民粹主義是一種超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研究表明,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是宜人的,但他們宜人的方式不同:宜人性的禮貌方面與保守的觀點和更傳統的道德價值觀相關,而宜人性的同情心方面與自由主義和平均主義相關。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可以互補;社會既需要那些深切關心每個人的公平和社會穩定掌權者,也需要那些更專注於幫助有需要的人。
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僅憑民粹主義本身並不一定危險。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將包括那些挑戰政府並批評當權者的人。特別有問題的是,當一位高度對抗性的領導人使用言辭來喚起其他對抗性人群的情緒,並團結他們支援特定的有害意識形態時。這可能會導致一種情況,即掌權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缺乏同理心、視角轉換能力以及控制攻擊性和破壞性衝動所需的自我控制能力。
當然,並非所有支援民粹主義的人都是對抗性強的人。人們支援民粹主義者有很多原因。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在試圖理解許多特朗普選民在投票時的想法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原因包括“停滯不前的工資、失去家園、難以捉摸的美國夢以及在他們的生活背景下有意義的政治選擇和觀點,撕裂了他們的生活。”
然而,在社交媒體、YouTube 和另類媒體上,對抗性強的人越來越多,他們認為自己比政府“精英”有更好的答案,並受到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資訊的鼓舞和喚醒,從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影響力。人們變得更容易接受民粹主義的關鍵原因,與其說是社會經濟因素是民粹主義吸引力的最突出解釋(巴克及其同事實際上在其研究中控制了社會經濟地位),不如說是人們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並且更自由地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事實上,民粹主義的吸引力部分歸因於 1960 年代日益增強的平均主義,其結果是今天的公民對政治家期望更高,並且感覺自己更有能力評判他們的行為。
總的來說,這是一件好事。然而,正如卡斯·穆德指出的那樣,越來越多的公民認為自己對政治家的所作所為有很好的瞭解,並且認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與此同時,實際上更少的人想要透過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來做得更好。政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在撰寫時很好地表達了這一點:“近半個世紀的調查提供了壓倒性的證據,表明公民並不重視實際參與政治生活。”
有趣的是,民粹主義支持者實際上並不想由“普通人”領導;相反,他們希望自己的價值觀和願望由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來實施。穆德發現,大多數民粹主義領導人實際上都是“局外人精英”;他們與精英階層聯絡緊密,但他們不是精英階層的一部分。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只是不想受“異己”精英的統治,他們的政策不能直接滿足他們自己的願望和關切。
這項研究非常重要,需要牢記在心,因為它看起來,為了推行更激進的政策而使用民粹主義言論不會在短期內消失。正如穆德觀察到的,由於多種因素,“民粹主義將成為未來民主政治中更常見的特徵,只要‘沉默的大多數’的重要部分感到‘精英’不再代表他們,它就會爆發。”
理解人格差異可能不是理解民粹主義吸引力的唯一因素,但為了國家和世界的緣故,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