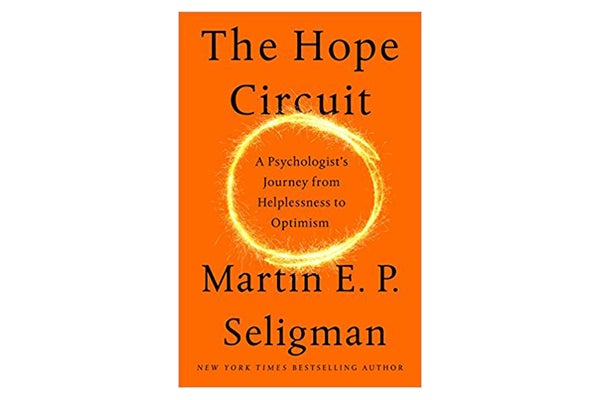本文發表在《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中,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幾年前,我清楚地記得在應用積極心理學碩士(MAPP)課程畢業典禮的會場後排就座。環顧四周,我看到學生們興奮和期待,他們的創始人,偉大的馬丁·塞利格曼戲劇性地闊步走到會場前方向班級講話。當他走上講臺時,他開始敬酒。“大家舉起酒杯,”他用洪亮的男低音和一個勝利的微笑說道。當學生們急切地舉起酒杯時,塞利格曼自信地宣佈:“讓我們為背側縫核乾杯!”學生們感到困惑,尷尬地碰了碰杯子,急於想聽更多,因為馬蒂繼續向學生詳細描述背側縫核,以及如何透過啟用內側前額葉皮層來學習控制來克服與此迴路相關的被動性。在進行了技術描述後,塞利格曼的臉上煥發出光芒,他興奮地總結說,他最近意識到這實際上是“希望迴路”!
不知何故,我在積極心理學中心與馬丁·塞利格曼共事的美好回憶似乎很適合用來介紹他對剛剛釋出的自傳《希望迴路》的評論。完整披露:我從2015年到2017年在想象力科學方面與馬丁·塞利格曼合作,他問我是否願意寫一篇關於他書的評論。我很榮幸他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之所以答應不僅是因為這份榮譽,還因為我讀過(並評論過)該書的早期草稿,並且認為這是一本非常值得評論的有趣的書。
儘管如此,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將盡力給出儘可能客觀、公正和真實的評論。《希望迴路》之所以會引起你的興趣,主要有三個原因: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你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你對一位傑出心理學家的視角下的心理學領域歷史感興趣,
你對一位傑出心理學家的個性感興趣,
你對馬丁·塞利格曼對他批評者和對積極心理學的批評的回應感興趣。
按照這個組織,讓我們深入探討一下。
心理學史(從一位傑出心理學家的視角)
這本書令人著迷的一個層面是,它描述了關於心理學史的獨特視角,尤其是在它與作者對該領域的貢獻相交的時候。不可否認的是,馬蒂對該領域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我發現這本書從習得性無助到習得性希望的總體弧線特別引人入勝。馬蒂和他在習得性無助實驗中的最初合作者,史蒂夫·邁爾(研究生畢業後將注意力轉向了神經科學)意識到他們最初的習得性無助理論實際上是倒退的(參見“習得性無助五十週年:來自神經科學的見解”)。在他們的習得性無助實驗中體驗到的被動性和缺乏控制感實際上是預設反應,一種自動的、未習得的對長期逆境的反應,而實際上必須學習的是希望——即一個人可以控制和利用環境中不可預測性的感知。我發現馬蒂對這些見解能夠為抑鬱症的治療提供資訊感到非常鼓舞。
你可以在這本書中閱讀馬蒂的許多其他貢獻,包括他在習得性樂觀、積極心理學、軍事韌性訓練、性格優勢的編目和測量,以及積極心理學的各種分支:積極教育、積極健康和積極心理治療。
毫無疑問,馬蒂一直很忙!當然,他並不是獨自完成這項工作的,他對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幫助過他的人進行了充分而華麗的描述,包括(但不限於):Lyn Abrahmson、Alejandro Adler、Lauren Alloy、Roy Baumeister、Aaron Beck、Rhonda Cornum 將軍、Mihalyi Csikszentmihalyi、Ed Diener、Angela Duckworth、Johannes Eichstaedt、Barbara Fredrickson、吉朗文法學校、Jim Hovey、Suzanne Johnson、Darwin LaBarthe、Sonja Lyubomirsky、Acacia Parks、James Pawelski、Chris Peterson、Richard Pine、Jack Rachman、Peter Railton、Tayyab Rashid、Karen Reivich、Judith Rodin、Paul Rozin、Carl Sagan、Stephen Schueller、Peter Schulman、Andrew Schwartz、Arthur Schwartz、Barry Schwartz、Carly Seligman、Daryl Seligman、Jenny Seligman、Mandy Seligman、Nikki Seligman、Chandra Sripada、John Templeton 爵士、Jack Templeton、Lyle Ungar、George Vaillant、Joe Wolpe 和 David Yaden。
我發現他對亞倫·貝克、曼迪·塞利格曼、克里斯托弗·彼得森和彼得·舒爾曼的描述特別令人感動,他對他們的喜愛似乎非常真誠。此外,很明顯他確實很感激生活中幫助過他的許多人。正如他回憶的那樣,在他60歲生日派對上,他對最親密的朋友和同事們說了以下一段話
“我今天從 Bob Olcott、Kathleen Hall Jamie- son 和 George Vaillant、Ed Diener、Ray Fowler、Barry Schwartz、Mike Csikszentmihalyi、Lester Luborsky 和 Chris Peterson 那裡學到——但主要是從 Mandy 那裡學到——我的生活不是自傳,而是傳記。這是一個關於我如何透過友誼、同事情誼、慷慨和愛來獲得世界幫助的故事。”
他職業生涯中的一個特殊轉折點發生在30歲左右,當時他剛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終身教授職位,並且仍在從事動物實驗心理學研究。作為馬蒂導師並幫助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教授職位的亞倫·貝克(認知行為療法之父)警告馬蒂,如果他繼續走這條研究道路,並且沒有做更多應用工作,他將“浪費[他]的生命”。然後,幾天後的一個夢幫助鞏固了他改變職業軌跡的決定
我感到激動,但還沒有被動搖。蒂姆告訴我採用新方法,並透過將我的工作轉向直接處理真實的人和實際問題,在外部效度方面做得更好。但幾天後,一個神秘的夢動搖了我的根基:我不知何故發現自己身處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我正慢慢地沿著它著名的彎曲斜坡蹣跚而行。每隔幾步,右邊都有房間,房間裡的人在玩紙牌。它們似乎是塔羅牌。
我問:“為什麼每個人都在玩紙牌?”
這時,博物館的屋頂打開了,上帝出現了——只有他的頭,而不是他的身體。如果你想知道,上帝非常年邁,他是男性,他有白色、修剪整齊的捲曲鬍鬚,並且有洪亮的男低音。他令人難忘地說:“塞利格曼,至少你開始問正確的問題了。”
很明顯,馬蒂在他的旅程中得到了很多支援。在這方面,以及在許多其他層面上,馬蒂都是一種現象。我在職業生涯中與多位巨人共事過,但我從未見過像我與馬蒂共事時所見的那樣。他身邊總是有源源不斷的人想進入他的軌道,人們想為他的研究提供資金。這真是令人著迷的景象,這種現象在他的自傳中非常明顯。
不幸的是,我擔心他往往對他圈子外的人不太欣賞。這在書中很明顯——不僅透過他所討論的內容,更透過他省略的內容。閱讀馬蒂對心理學史的敘述,有時感覺好像心理學領域由兩個主要階段組成:馬蒂之前的一切和馬蒂之後的一切。當然,他不能因為沒有在自傳中包含所有內容而受到責備,但肯定有一些地方他本可以給出更全面的評論。
特別是,我感到失望的是沒有看到對人格和人本主義心理學(它們在50年代和60年代彼此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絡)、積極心理治療、積極教育和前瞻性心理學的更準確的描述。馬蒂在整本書中唯一提到的人格心理學家是戈登·奧爾波特。然而,他並沒有以最好的眼光看待奧爾波特。馬蒂提到奧爾波特用“人格”代替了“性格”,因為他認為該領域應該沒有價值觀。根據馬蒂的說法,這是一個“大錯誤”,積極心理學領域應該研究“積極特質”。
奇怪的是,奧爾波特和他那一代的許多其他人格心理學家肯定會同意這種說法。奧爾波特時代的人格心理學家對研究“整個人”(包括積極和消極方面)深感興趣,他們對當時新興的人本主義心理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事實上,奧爾波特本人在20世紀30年代就將“人本主義心理學”這一短語引入了人格研究。正如人本主義發展心理學家夏洛特·比勒指出,
“人本主義心理學最普遍的共識之一是,我們努力尋找途徑來研究和理解作為整體的人……正如[戈登]·奧爾波特所說……我們自身擁有許多‘自我’,而整合它們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當時的其他人格心理學家,包括喬治·凱利、加德納·墨菲和亨利·默裡,也在為我們理解人性的積極方面做出巨大貢獻,他們研究了人類需求的分類、自我的構建、意義、意圖、責任、價值觀、開放性、擁抱未知以及與宇宙的認同。當人本主義心理學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成為一門正式學科時,這些人格心理學家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它的盟友,為“健康人格”的理念做出了重大貢獻。正如加拿大人本主義心理學家西德尼·朱拉德所說,“健康人格是[人們]在智慧和對生命的尊重的指導下行動的方式,以便[他們的]需求得到滿足,並且[他們]的意識、能力和愛的能力都會得到增長。”
公平地說,馬蒂承認他最初將人本主義心理學家與“水晶療法”和“芳香療法”混為一談是歪曲了他們的形象,併為“這種毫無根據的輕視”道歉。他還承認亞伯拉罕·馬斯洛創造了“積極心理學”這個術語。但他隨後又對馬斯洛進行了一些挖苦,說“亞伯拉罕·馬斯洛出現得太早了”,並講述了馬斯洛的一位研究助理的故事,他寫道:“如果弗雷德·斯金納回個電話,亞伯(Abe)會更開心。”馬蒂用以下內容結束了這一部分:
“事實上,我這個不求甚解的學者並沒有讀過太多馬斯洛的書,所以他的著作在我的思考中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即使我恰當地引用了馬斯洛,那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積極心理學直接源於我對主流臨床和實驗科學的缺陷的看法。”
不管你對這段話有什麼其他看法,至少我認為可以肯定地說,在整個心理學發展史上,有相當多的主流臨床醫生非常強調人格的積極方面,包括卡爾·榮格、卡倫·霍妮、維克多·弗蘭克爾和卡爾·羅傑斯。不幸的是,這本書中沒有提及這些開創性的心理學家。
那麼,積極教育呢?馬蒂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積極教育領域早在他參與之前就已存在。根據馬蒂的說法,在聽取了安東尼·塞爾登關於幸福感、快樂、意義、成就感和教育參與度等重要性的演講後,他認為安東尼“定義了一種新的教育方式,我認為它的名字一定是‘積極教育’。”然後他繼續描述該領域的發展歷史,而他重述的歷史完全源於他在 90 年代對悲觀主義的研究。那麼,約翰·杜威呢?積極青年發展運動呢?E. 保羅·託蘭斯呢?蒙特梭利運動呢?我可以繼續說下去。
最後,還有“前瞻性心理學”。在書中,馬蒂描述了他如何“將前瞻性提升到心理科學的最前沿和中心”。根據馬蒂的說法,按照傳統的觀點,如果你想知道你將來會做什麼,原則上你需要知道四件事:
你的歷史
你的基因構成
你當前的刺激
你當前的驅動力和動機
“精神分析、行為主義和大多數認知心理學都接受這一點。但我不同意,”他寫道。“這裡有一個巨大的盲點,它困擾了我五十年:它忽略了人類的能動性,以及它的支點,即一種代謝過去和現在以創造未來的思維,然後從可能的未來中做出選擇”(原文為斜體)。
然後,馬蒂討論了他所理解的前瞻性心理學的歷史,基於他了解到預設大腦網路與思考未來有關,以及他與羅伊·鮑邁斯特、彼得·雷爾頓和錢德拉·斯里帕達的對話和合作。“如果記憶不是電影和照片的檔案櫃,而是一個與未來最相關的不斷變化的可能性集合呢?”他寫道。“也許記憶的不可靠性不是一個錯誤,而是一個基本特徵。記憶的錯誤,對我們舊記憶片段的轉移和洗牌,可能使我們能夠從過去吸取不同的教訓,而這些教訓對於更美好的未來是必要的。”
這確實是一個很酷的想法!不幸的是,馬蒂忽略了許多為這種思維方式鋪平道路的開創性心理學家,包括丹尼爾·沙克特和蘭迪·巴克納。在他們 2007 年的論文“回憶過去以想象未來:前瞻性大腦”的摘要中,沙克特和巴克納寫道:
“最近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想象未來依賴於與回憶過去所需的大部分相同的神經機制。這些發現導致了前瞻性大腦的概念;即大腦的一個重要功能是使用儲存的資訊來想象、模擬和預測可能的未來事件。我們認為,諸如記憶之類的過程可以根據這個想法進行富有成效的重新概念化。”
這還不包括 E. 保羅·託蘭斯關於愛上自己未來形象的重要性的研究,查爾斯·斯奈德和沙恩·洛佩茲關於希望心理學的研究(2016 年,洛佩茲在研究如何向年輕人灌輸更多希望的職業生涯後,在年僅 46 歲時不幸去世),埃德溫·洛克和加里·萊瑟姆在 35 年間關於未來目標設定重要性的開創性研究,以及喬治·安斯利關於我們如何透過現在和未來的自我之間的討價還價來調節當前行為的研究(參見“意志的崩潰”)。人們從根本上以未來為導向的想法也是控制論的基本前提,喬治·米勒、尤金·加蘭特和卡爾·普里布拉姆在他們 1960 年的極具影響力的著作“計劃與行為的結構”中將其引入心理學(計劃實際上是未來的影像)。
即使這些人中的許多人沒有親自影響馬蒂的想法,我仍然認為他們值得被認可,並且在沒有提及他們的情況下,對心理學歷史的完整敘述是失職的。再次強調,這都不應該減損馬蒂對這些主題的重要貢獻。
一位傑出心理學家的人格
當馬蒂在 90 年代決定競選美國心理學會主席時,內部人士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候選人已經提前安排好,並且接班順序已經指定。這隻會激起馬蒂更大的獲勝慾望,而他確實贏了,“在選舉中獲得了將近 10,000 張選票,是離他最近的對手的三倍。”在承認失敗時,心理學家迪克·蘇因將馬蒂稱為“自然之力”。
正如在整本書中看到的那樣,這是對馬蒂的準確描述。《希望迴路》除了讓我們更多地瞭解心理學的歷史之外,也是對心理學中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之一的性格結構的引人入勝的研究。
令人著迷的是,他從三歲之前愛笑快樂的孩子,到悲觀不開心的青少年,再到抑鬱的初級教員,再到樂觀和幸福最著名的研究者的轉變過程。

作者:馬丁·塞利格曼

作者:馬丁·塞利格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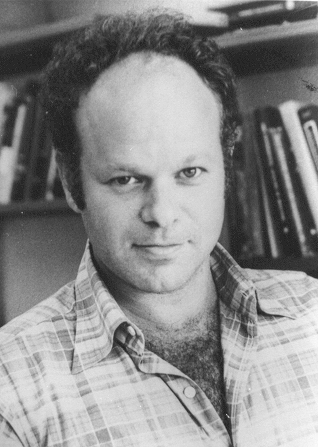
作者:馬丁·塞利格曼
馬蒂自己也承認,他有“脾氣暴躁”和“自我陶醉”的過去,並且書中有一條線索顯示了他的智力與他的社交智商之間的對比。例如,在他關於童年、青年時期和“誤導教育”的部分,我們多次得知他非常聰明:
“十二歲時,我就很聰明瞭。”
“十八歲時,我仍然很聰明。”
“彼得告訴我,我的智商是 185。”
“我的學業成績一直很好。在我學校,A 是一個罕見的等級,而我卻得到了很多……”
“我與智力競賽的孩子比賽,經常獲勝……”
然而,我們也瞭解到他在學校“社交方面表現不佳”。然後,當他描述他的早期職業生涯時,這個主題再次出現。雖然他寫道他“努力成為一名知識分子”,
“我試圖匆忙地完成這一切。我想完成事情,而且我非常魯莽。我走了捷徑。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我沒有好好聽別人說話,幾乎立即向內漂移,思考我聽到的內容如何符合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人們認為我是在踐踏他們,但我認為這是這種自我陶醉的副作用。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太喜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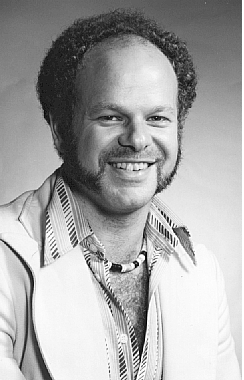
作者:馬丁·塞利格曼
貫穿全書的另一個主題是他的雄心壯志:
“我雄心勃勃,並且渴望成功。我希望艾伯特太太知道我的名字。”
“我雄心勃勃,而且我知道我的雄心壯志是什麼……我的雄心壯志是像維特根斯坦一樣,被忠誠的學生和追隨者包圍。”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一個具體的未來目標如何幫助將其變為現實。正如馬蒂在書的結尾寫道,這個被忠誠的學生和追隨者包圍的終身夢想“實際上實現了,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對獎項的渴望。”
馬蒂還寫到了他強烈的知識野心,以及他在高中畢業那年得知自己不是告別演說者時感到的巨大失望,儘管他已經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
“畢業對我來說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丹是我們班的告別演說者——儘管五十年後,我的朋友道格·諾斯,1958 年的告別演說者和新校長,寄給我一份官方成績單,表明我實際上是班級第一名畢業的。我沒有獲得我認為自己應該獲得的各種學術獎項。相反,它們被分發給了那些在未來幾年最有可能在經濟上支援學院的男孩們。我感覺自己更像一個失敗者,而不是一個即將征服新世界的勝利畢業生。我要去普林斯頓大學了,這本應是值得慶祝的事情,但我的四個同學也是如此,而且我畢竟是被哈佛拒絕的人。”
他野心的另一個方面與他渴望成為上層“社會階層”的一部分有關。在他的童年時期,我們看到了諸如:“我仍然屬於下層階級,儘管我不太清楚是哪種下層階級”這樣的陳述,以下是他對他的高中畢業舞會的描述:
“貝絲和艾琳在我家後院為我舉辦了一場毫無生氣的派對,桌子擺在我們那棵酸櫻桃樹周圍。我的表兄弟姐妹、姑姑和叔叔都在那裡,但我像個殭屍一樣機械地走過場。我已經不再屬於他們那個下層階級的世界了。”
他整個職業生涯的另一個明確動力是他的追求“不無聊”。正如馬蒂回憶的那樣,他1964年在本科哲學導師彼得·麥迪遜給他的臨別建議是:“人們進入心理學領域有兩個原因。一是避免犯錯。二是避免無聊。我希望你選擇第二個。”馬蒂對這個建議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併發誓永遠不要無聊。我認為,說馬蒂一點也不無聊是很公平的。
另一個主題是他對自己性格的描述——我認為這非常準確——具有“創業”心態和廣泛的“企業家”傾向。縱觀該領域歷史,很少有心理學家像他一樣與如此多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合作(甚至有如此強烈的合作動機),發起如此多的大型專案,併為這些專案獲得如此多的資金。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馬蒂的功利主義道德觀在整本書中也很明顯,不僅體現在他對研究生研究中電擊狗的倫理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還體現在他反思自己離婚並拋下孩子這一決定。
“我永遠會為我離開孩子的決定感到內疚,但如果沒有那個魯莽的舉動,曼迪、我的接下來的五個出色的孩子以及積極心理學就不會出現。”
無論你對此有何看法,都不可否認他對與曼迪的關係以及他在積極心理學方面的工作感到多麼自豪。他的更溫柔的一面在名為“曼迪”的章節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該章節以以下內容開頭
“曼迪·麥卡錫·塞利格曼是我生命中的摯愛。她是我們的四個孩子的母親。三十年後,當我醒來在她身邊時,我仍然很高興看到她。她改變了我的個人生活,然後是激勵我轉向積極心理學的繆斯。”
我必須承認,我發現整個章節是整本書中最感人的章節。很明顯,曼迪本身就很出色,她深深地影響了馬蒂,讓他改變了心意。曼迪在研究生院遇到了馬蒂,他是她的導師,直到他向她表達了自己的感情。
另一個對馬蒂的性格(以及他決定推動積極心理學領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人是他的女兒妮基。根據馬蒂經常重複的起源故事,有一天在花園裡,他年幼的女兒說道:“爸爸,你還記得我五歲生日之前我是一個愛抱怨的人嗎……好吧,在我生日那天,我決定停止抱怨,那是我做過的最難的事情。如果我能停止抱怨,你就能停止做個壞脾氣的人。”馬蒂決定“如果妮基可以改變,我也一樣可以。我決定改變。”
無論他是否改變了自己的性格,他肯定將研究重點轉向了更樂觀的方向。為了提出一個“變革性”的議程,作為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馬蒂決定呼籲一個新的領域,專注於美好生活的科學,以及對使生活值得過的各種事物進行嚴格的研究。不應低估這一決定所產生的真正影響,以及它為幸福科學帶來的關注和資金。
馬丁·塞利格曼對批評者的回應
最後,本書可能對那些有興趣瞭解馬丁·塞利格曼如何回應他本人和他的工作的一些批評的人有吸引力。在題為“積極性及其批評者”的章節中,馬蒂回顧了積極心理學方面的許多成就
“在谷歌上搜索‘積極心理學’會顯示超過100萬個結果”
“我的免費正向幸福網站(www.authentichappiness.org)已註冊了近500萬人”
“許多大學課程都在教授積極心理學”
“幾乎所有主要的英文報紙和雜誌都報道了積極心理學”
“成千上萬的研究人員和從業者自稱為‘積極心理學家’”
“有數千篇關於積極心理學的同行評審期刊文章,以及200多本書籍,其中幾本是暢銷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僅我的書就被翻譯成近五十種語言”
“該主題已獲得至少2億美元的撥款和合同”
“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積極心理學組織,以及一個由數千名成員組成的國際積極心理學協會”
“《時代》雜誌做了一篇封面報道”
在本章中,馬蒂還試圖回應他的批評者。他將自己的回應分為“強烈的批評”(那些可檢驗並最終會證明對錯的批評)和“微弱的批評”(那些人身攻擊或稻草人論證)。我不會詳細介紹他所有的回應,但我會討論其中的一些。
在“強烈的批評”類別中,馬蒂回應了積極心理學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新穎或令人驚訝的內容的批評。他透過列舉該領域一些更令人驚訝的發現來反駁這種批評。我同意他的觀點,他提到的一些發現,例如“特定的練習可以增加幸福感並減少六個月後的抑鬱症,而其他看似合理的練習只是安慰劑”,完全可以證明積極心理學領域的合理性。此外,當有些人駁斥整個積極心理學領域時,我也感到不悅,該領域由數百名研究人員組成,研究與幸福相關的眾多主題,稱其為“沒什麼令人驚訝的”。
另一個強烈的批評是“人本主義心理學運動在四十年前就說過一切了。”我不會重複我對這件事的想法,但我會補充說,我覺得他對這個稻草人論證的批評本身就是一個稻草人論證。我不認為很多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實際上是在說人本主義心理學說了一切,但相反,我認為他們只是在正確地指出,50年代和60年代人本主義運動中的傑出心理學家在很多情況下都主張與馬蒂在他的總統演講以及隨後的關於積極心理學的著作中主張的許多相同的東西。
這種裂痕是不幸和不必要的,並且存在一個人本主義心理學和積極心理學之間愉快結合的真正機會。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創始人,包括亞伯拉罕·馬斯洛和卡爾·羅傑斯,提出了許多豐富的、可檢驗的理論,這些理論可以使用現代嚴格的分析方法進行檢驗,而這些方法在他們那個時代是無法使用的。我個人正在嘗試從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那裡獲取很多想法並進行實證檢驗,並且我知道該領域的其他人,如肯農·謝爾頓、理查德·瑞安和愛德華·德西也在嘗試做同樣的事情。
在“微弱的批評”部分,馬蒂正確地反駁了積極心理學僅適用於“WEIRD”人群(西方、受過教育、工業化、富裕和來自民主社會的人)的觀點。實際上,人們對跨文化幸福決定因素的興趣日益濃厚,並且有一些關於該主題的非常好的研究。
馬蒂還就金錢的重要性提出了很好的觀點,並敏銳地反駁了“賺更多的錢是實現更多幸福的解決方案”的觀點。正如他正確指出的那樣,當收入超過一定水平後,如果你將額外的錢花在成長型消費上,例如花時間與朋友和家人在一起或培養自己的愛好和熱情,你的生活滿意度就會更高。
話雖如此,我認為馬蒂沒有充分解決的一個批評是,積極心理學忽略了苦難和不幸。雖然他認為這是一個“稻草人論證”,並指出他的大部分工作都直接來自他對苦難和不幸的研究,並且他認為積極心理學“補充而不是取代努力擺脫束縛生活的困境”,但我認為,一個完整的幸福科學永遠不能脫離對那些處於極端貧困(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或那些飽受精神疾病折磨或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真實、無法控制的歧視和虐待的人的關注。在《希望迴路》中,非常明確地關注能動性的重要性,並且在最後一部分中,馬蒂強調,總的來說,世界正在比過去做得好得多。他是對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無法否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對於這個星球上的許多人來說,存在著真實的無助,不僅僅是習得性無助,他們迫切需要真實的希望,不僅僅是心理上的希望。
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馬斯洛將身體安全和保障納入作為允許一個人蓬勃發展基本需求的原因,以及為什麼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創始人的重點明確地不是幸福或福祉,而是存在和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原因。需要一種真正的、健康的
消極和積極的整合。我們已經看到了當我們把幸福與消極因素脫離地看待時會發生什麼,例如那些快樂、適應良好的人,他們因為實現了個人幸福目標而感到滿足,卻忽視了周圍那些不幸的人的困境。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真正的批評,馬蒂在他的書中過於草率地駁斥了它。請參閱露絲·惠普曼的優秀文章《當金字塔倒塌時我們在哪裡?在瑜伽課上》,這篇文章的批判我認為如果我們想要擁有一個幫助所有人都蓬勃發展的幸福科學,我們需要公開和誠實地討論。
馬丁·塞利格曼的遺產

現在,讓我們進入真正的核心內容。在《希望迴路》(Hope Circuit)中,有一點很明顯,那就是馬蒂非常在意自己的遺產(好吧,其實誰不在意呢?)。在本書的最後一節,他真誠地、令人耳目一新地謙遜地反思了自己在該領域中的角色以及他的工作將對後代產生的影響。他在這裡給人的感覺確實是,他深深地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產生足夠的影響,從而激勵後代接過他的衣缽。
我認為馬蒂不必為此擔心。儘管我上面對他的一些遺漏之處提出了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留下了重要的遺產,並激勵了許多研究人員、教練、治療師、教育工作者和軍事人員在未來繼續傳遞這一火炬。
馬蒂是如何理解他成功的起源的?在最後一章中,馬蒂提到積極心理學對他來說是一種“召喚”。事實上,“被未來召喚”的想法貫穿了整本書,正如他指出的那樣,“有些人實際上是被未來召喚的,被未來本身或被上帝召喚。夢想和願景是召喚的媒介。” 馬蒂反思道: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不是艾爾·班杜拉(Al Bandura)、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Lazarus)、朱利安·羅特(Julian Rotter)、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ke Csikszentmihalyi)或埃德·迪納(Ed Diener)?所有這些科學家都在更早的時候,就已在富有成效地研究生活的積極一面……”
在試圖理解他今天是如何走到這一步時,他反思了自己一路走來的夢想和其他經歷,這些經歷讓他覺得自己是被召喚的。他指出,在他狀態好的日子裡,他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自己是“天生的”。
“我喜歡認為自己是‘天生的’。在橋牌中……在高階專家中,有少數人是天生的;牌會從他們的手中飛出,他們並不總是能解釋他們做了什麼。但他們的打法始終是正確的。彼得·麥迪遜(Peter Madison)很早就發現了我的這一點,我也意識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天生就是指在心理學方面有好的想法。從我擔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開始,我成了一個天生的鼓舞者,並且獲得了魅力……我無意在我的生活中求助於更高的力量。但我也不打算否認它。然而,這些話語還是被說出了我的口。”
馬蒂確實是一位天生的牌手。但從他的自傳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總是拿到一手非常幸運的牌。也許馬蒂最大的天賦是他非凡的能力,能夠利用他遇到的無數機會。無論各種因素的具體組合是什麼,毫無疑問,這種協同作用最終造就了有史以來最複雜、最有抱負、最有成效、最有影響力,而且絕對不乏味的心理學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