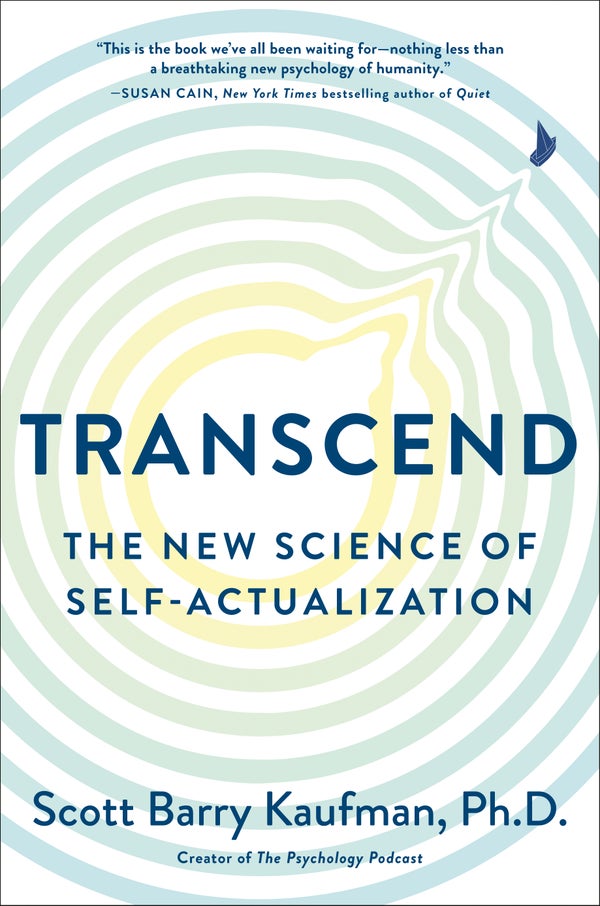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在某種程度上,當苦難找到意義時,它就不再是苦難了。” ——維克多·弗蘭克爾,《活出生命的意義》
金繕是一種古老的日本藝術,用於修復破碎的陶器。這種技術不是隱藏裂縫,而是用漆與金、銀或鉑金粉末混合物重新連線破碎的碎片。當重新組合在一起時,整個陶器看起來和以前一樣美麗,甚至擁有其破碎的歷史。
許多人都在思考,在歷史上的這個時刻,我們是否會迎來第二次生命。當重新組合在一起時,我們將以尊嚴和優雅恢復嗎?科學表明,我們不僅會恢復,而且還將展示人類巨大的韌性和成長能力。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從韌性到成長
臨床心理學家喬治·博南諾在他的開創性2004 年論文中,主張對壓力反應進行更廣泛的概念化。博南諾將韌性定義為經歷過高度危及生命或創傷性事件的人保持相對穩定、健康的心理和生理功能水平的能力,他回顧了大量研究,表明韌性實際上很常見,它與簡單地沒有精神病理學不同,並且可以透過多種,有時是意想不到的途徑獲得。考慮到美國約有 61% 的男性和 51% 的女性報告一生中至少經歷過一次創傷性事件,人類的韌效能力非常驚人。
事實上,許多經歷過創傷的人——例如被診斷出患有慢性病或絕症、失去親人或遭受性侵犯——不僅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而且實際上在創傷性事件之後茁壯成長。研究表明,大多數創傷倖存者不會患上 PTSD,甚至有很多人報告說從他們的經歷中獲得了成長。理查德·泰德斯基和勞倫斯·卡爾霍恩創造了“創傷後成長”一詞來捕捉這種現象,將其定義為由於與極具挑戰性的生活環境作鬥爭而體驗到的積極心理變化。
據報道,以下七個成長領域源於逆境
更加珍惜生命
更加珍惜和加強親密關係
增強同情心和利他主義
識別新的可能性或人生目標
更好地認識和利用個人優勢
加強精神發展
創造性成長
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經歷過創傷後成長的人當然更希望沒有經歷過創傷,並且與遇到積極的生活經歷相比,這些領域中很少有領域在創傷後表現出更多的成長。然而,大多數經歷過創傷後成長的人常常對發生的成長感到驚訝,這種成長通常是出乎意料地發生的,是試圖理解難以理解的事件的結果。
哈羅德·庫什納拉比在反思他兒子的去世時很好地表達了這一點
因為亞倫的生與死,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敏感,更有效率的牧師,更富有同情心的輔導員。如果能讓我的兒子回來,我願意放棄所有這些收穫。如果我可以選擇,我寧願放棄所有因我們的經歷而來的精神成長和深度。 。 。 。 但我無法選擇。
毫無疑問:創傷會動搖我們的世界,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珍視的目標和夢想。泰德斯基和卡爾霍恩使用了地震的比喻:我們傾向於依賴一套關於世界的仁慈和可控性的特定信念和假設,而創傷性事件通常會打破這種世界觀,因為我們從平常的認知中被震醒,不得不重建自己和我們的世界。
但是我們有什麼選擇呢?正如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所說,“當我們再也無法改變一種情況時,我們就被挑戰去改變自己。” 近年來,心理學家已經開始瞭解將逆境轉化為優勢的心理過程,並且越來越清楚的是,這種“心理地震”式的重組實際上是成長髮生的必要條件。正是在自我的基礎結構被動搖時,我們才最有可能在生活中尋求新的機會。
同樣,波蘭精神病學家卡齊米日·達布羅夫斯基認為,“積極解體”可能是一種促進成長的經歷。在研究了許多心理發展水平較高的人之後,達布羅夫斯基得出結論,健康的個性發展通常需要人格結構的解體,這可能會暫時導致心理緊張、自我懷疑、焦慮和抑鬱。然而,達布羅夫斯基認為,這個過程可以引導人們更深入地審視自己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並最終達到更高水平的個性發展。
使我們能夠將逆境轉化為優勢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充分探索我們圍繞事件的想法和感受。認知探索——可以定義為對資訊的一般好奇心以及資訊處理中複雜性和靈活性的傾向——使我們能夠對令人困惑的情況感到好奇,從而增加我們在看似不可理解的事物中找到新意義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的是,創傷後成長的許多步驟與我們避免極端不適情緒和想法的自然傾向背道而馳。然而,只有透過擺脫我們自然的防禦機制,正面應對不適,並將一切視為成長的素材,我們才能開始擁抱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悖論,並對現實產生更細緻入微的看法。
在創傷性事件之後,無論是重病還是失去親人,都很自然地會沉浸在事件中,不斷思考發生了什麼,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想法和感受。反芻通常表明您正在努力理解所發生的事情,並且正在積極地拆除舊的信仰體系並建立新的意義和身份結構。
雖然反芻通常開始時是自動的、侵入性的和重複性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思考變得更有組織性、更受控制和更深思熟慮。這種轉變過程當然可能是痛苦的,但反芻,加上強大的社會支援系統和其他表達渠道,可能非常有益於成長,並使我們能夠挖掘我們從未意識到存在於我們內心的深層力量和同情心。
同樣,悲傷、悲痛、憤怒和焦慮等情緒是創傷的常見反應。與其盡一切努力抑制或“自我調節”這些情緒,體驗性迴避——避免害怕的想法、感覺和感覺——反而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強化我們對世界不安全的信念,並使追求有價值的長期目標變得更加困難。透過體驗性迴避,我們關閉了我們的探索能力,從而錯失了許多產生積極體驗和意義的機會。這是接受與承諾療法(ACT)的核心主題,該療法幫助人們提高他們的“心理靈活性”。透過擁抱心理靈活性,我們以探索和開放的態度面對世界,並且能夠更好地應對服務於我們選擇的價值觀的事件。
考慮一下託德·卡什丹和詹妮弗·凱恩進行的一項研究,他們在大學生樣本中評估了體驗性迴避在創傷後成長中的作用。在這個樣本中,最常報告的創傷包括親人突然去世、機動車事故、目睹家庭暴力和自然災害。卡什丹和凱恩發現,痛苦越大,創傷後成長就越大——但這僅在體驗性迴避程度較低的人中。那些報告痛苦程度較高且很少依賴體驗性迴避的人報告了最高的成長水平和人生意義。
對於那些求助於體驗性迴避的人來說,這一發現被顛倒了,更大的痛苦與較低水平的創傷後成長和人生意義相關。該研究增加了一篇越來越多的文獻,表明焦慮水平低且體驗性迴避水平低(即心理靈活性水平高)的人報告生活質量得到提高。但這項研究也表明,人生的意義也增加了。
增加的意義可以成為創造性表達的絕佳素材。
從創傷中創造
劣勢與創造力之間的聯絡由來已久且備受推崇,但現在科學家們開始解開這種聯絡背後的奧秘。臨床心理學家瑪麗·福爾加德要求人們報告他們一生中最有壓力的經歷,並指出哪些經歷的影響最大。不利事件清單包括自然災害、疾病、事故和襲擊。
福爾加德發現,認知加工的形式對於解釋創傷後的成長至關重要。侵入性的反芻形式導致多個成長領域下降,而有意識的反芻導致創傷後成長的五個領域增加。其中兩個領域——人際關係的積極變化和對生活中新可能性的認知的增加——與對創造性成長的認知增加有關。
在她《當牆壁變成門:創造力與轉變疾病》一書中,託比·扎斯納分析了患有身體疾病的著名畫家的傳記。扎斯納得出結論,這些疾病透過打破舊習慣、引發不平衡並迫使藝術家產生替代策略以實現其創作目標,從而為他們的藝術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總而言之,研究和軼事支援參與藝術療法或表達性寫作以幫助促進創傷後重建過程的潛在巨大益處。每天只需花十五到二十分鐘寫下引發強烈情緒的主題(“表達性寫作”),已被證明可以幫助人們從他們的壓力經歷中創造意義,並更好地表達他們的積極和消極情緒。
我知道現在時局艱難,在我們能夠再次變得完整之前,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而,關於創傷後成長的最新研究可以為您提供一些希望,即我們很可能會變得更強大、更具創造力,並且擁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的意義感。
--
摘自斯科特·巴里·考夫曼博士的《超越》,由企鵝出版集團旗下的 TarcherPerigee 出版,企鵝蘭登書屋的一個部門。有限責任公司版權所有 (c) 2020 斯科特·巴里·考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