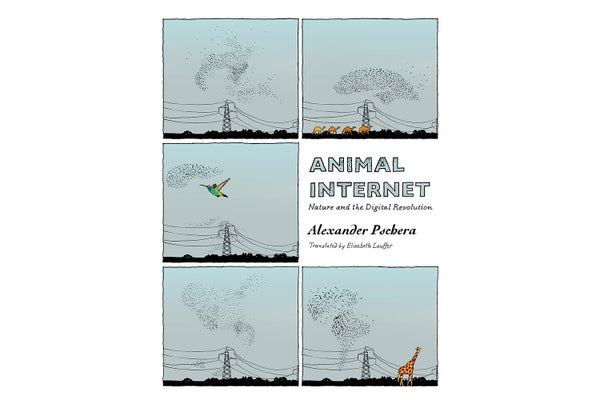摘自《動物網際網路:自然與數字革命》,
亞歷山大·普舍拉著(伊麗莎白·勞弗爾從德語翻譯)。 版權所有 © 2016年4月12日,新航海出版社。
目前,我們對野生動物的生活方式的瞭解還不到百分之一。也就是說,幾乎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小海龜剛從海灘上的蛋殼中爬出來時是如何表現的。我們不知道小杜鵑在秋天來臨時是如何找到去往何處的。這就是為什麼保護動物如此困難。動物的生活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基本聯絡仍然未知。我們對許多瀕危動物的生活知之甚少,以至於無法有效地幫助它們。我們甚至不知道某些物種是否仍然存在。每年都有新的物種出現或重新出現。例如,斑尾袋鼬(Dasyurus maculatus),一種食肉有袋動物,最近在澳大利亞格蘭屏國家公園的遠端數碼相機中被捕捉到,此前人們認為它已經滅絕了141年。據說最後一隻這種動物是在1872年被殺死的。當時它們被認為是真正的害蟲。然而,這種物種的存在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它是生態系統穩定的標誌,因為作為一種夜間食肉動物,斑尾袋鼬佔據了食物鏈的頂端,因此可以與塔斯馬尼亞惡魔相提並論。如果這種動物已經存活了這麼長時間,那麼它捕食的物種也一定是如此。總的來說,然而,人類先前對大多數動物的瞭解是如此之少,以至於不可能從中推斷出任何進一步的理解。它沒有提供任何可靠的經驗基礎,可以據此制定可行的策略。每年,數十億隻鳥類和蝙蝠飛行數千英里,從它們的繁殖地飛往它們的越冬地。然而,在這些遷徙過程中實際發生了什麼,仍然是一個謎。我們知道的是,遷徙期間的死亡率非常高。但我們不知道的是,高度移動的動物何時何地死亡。在許多瀕危物種的案例中,我們無法回答我們需要保護什麼才能拯救它們這個問題:是食物選擇?水質?植物多樣性?是什麼阻止我們描繪出自然的真實圖景並制定出人類行為的有效規則呢?是缺乏可靠的經驗資料和具體資訊:目前存在哪些動物?它們如何在地球上移動?它們在地下或夜間做什麼?它們吃什麼,誰吃它們?
從動物網際網路收集的資料回答了這些問題。它們產生了自然的新形象。當在資訊時代開始並繼續徹底改變我們對社會的看法的並行發展背景下考慮時,這個形象才真正成形。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對社會結構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階層和環境,甚至國籍的形象,過去是由意識形態的預設和分配所支配的。“法國人”或“德國人”或多或少地代表了民族陳詞濫調。我們主要看到我們所知道的。然後我們會承認這些階級和國家的代表,並據此對他們進行評判。意識形態固定的目光首先隨著新的直接溝通和觀察模式的引入而開始軟化,這些模式在感知中建立了一種新的現實主義。電話和電視首先與網際網路相結合,然後與社交媒體相結合,為交流提供了視覺支援的機會,並假設為任何使用者提供了直接訪問其他使用者獨特生活的機會。階級和國籍的同質化、一成不變的先入之見因此而日益消失。社交媒體為我們提供了社會真實面貌的圖片:充滿了矛盾、交叉和不和諧。今天,那些想要堅持他們的意識形態觀點的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當面對獲得對世界的具體印象的誘惑時,他們的努力往往會崩潰。這些新的見解產生了一種也在改變社會的動態。因為看到產生知識,而知識導致行動。社交網路準備從內部解構社會理論,透過啟動一個擺脫意識形態理論的社會和系統變革引擎,正如最近埃及、突尼西亞、土耳其和烏克蘭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動員群眾和協調社會程序——這些是意識形態的核心功能。社交媒體現在已經承擔了這些職責。網際網路帶來了正規化轉變——拋棄理論和意識形態,迎接實踐和現實。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人類網際網路改變了社會,而動物網際網路將改變自然。我們不斷地談論現代技術如何影響人類溝通和人際關係。自從物聯網(IoT)誕生以來——也就是說,自從為無生命的物體配備智慧感測器,使這些東西可追蹤和“有感知能力”以來——對話已經擴充套件到解決這場技術革命對人類與無生命環境的關係以及對我們整個社會的影響。不再只是人類可以使用網際網路、傳送和呼叫資料,裝置、開關和感測器也可以連線到網路並進行互動,而無需人類的參與。可以透過整合電子裝置跟蹤的包裹以及墨盒快用完時自動訂購更換墨盒的印表機都是物聯網的無害示例。健身手環、電子計步器以及聯網家居的便捷新功能也是如此。但是,帶有感測器的房間可以記錄人類的存在,然後識別這些人類並將他們與從網路上提取的資料進行匹配,則具有更大的潛在風險——即使所謂的“智慧空間”技術肯定有許多有用的可能用途。
當智慧技術不僅允許事物開始思考和說話,而且還允許動物也開始思考和說話時,會發生什麼?當野生動物開始向我們傳送訊號,並且我們能夠將它們識別為具有自己背景的獨特個體時,會發生什麼?關於數字技術如何重塑我們與其他生物和自然的關係的討論仍然是新的;事實上,它甚至還沒有真正開始。然而,我們已經可以預見到網際網路對我們對自然的認識和知識的革命性影響。技術已經存在,可以允許動物自主交流,從而為我們提供對自然的現實印象,這種印象與兩百年的自然歷史寫作和生態理論所描繪的必然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圖景有所不同。這種新的概念不是源於理論——源於達爾文主義、行為理論、生態位的概念等等——聲稱透過單一的具體觀察得到證實;相反,它源於大量的資料和資訊。現在的重點是個體動物,而不是確認個體階級。在動物王國中,我們的注意力不再關注科、屬或種,而是轉移到具有特定歷史的個體。
動物網際網路的動物不是使用者生成的內容;它們不是模因,那些以光速傳播並催生了一種新的視覺“文化”的數字資訊包。相反,它們自己生成和傳輸資料。動物甚至植物——例如雨林中基本上無法接近的樹木,其生長可以透過所謂的樹木生長儀來測量——都配備了感測器,這些感測器傳輸關於它們的資訊,而不僅僅是關於它們的運動,還有各種環境資料(溫度、氣壓等)和動物身體的生理讀數。許多動物已經被標記了強大的GPS裝置,安裝在它們的身體上甚至體內:雪豹、座頭鯨、信天翁、紅眼樹蛙、果蝠、虎貓、賽加羚羊、錘頭鯊、蘭花蜂、山地大猩猩、鸛和棕熊。這些發射器使得追蹤動物成為可能,無論它們在哪裡:在雨林中心、在沙漠中徘徊,甚至在深海之下,並且由於網際網路技術,我們可以從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訪問這些資訊。每天都有更多的野生動物配備感測器。因此,一個龐大的資料儲存庫正在逐漸形成,以形成對自然的細緻入微和差異化的形象,最終將成為動物生活的複雜寫照。
動物網際網路無疑是一場技術革命。動物網際網路的核心是微型發射器,其功能甚至足以將資訊傳送到太空。在2016年上半年,國際空間站(ISS)將安裝一個特殊的接收這些訊號的天線。生物學家預計資訊將呈指數級增長。來自遙遠距離的微弱訊號將在空間站被處理併發送到資料庫,在那裡資訊將被轉換為視覺化影像。國際空間站天線旨在容納大約一萬五千個可接收的發射器。未來的計劃包括將天線安裝到低空飛行的衛星上,以實現更廣泛的覆蓋範圍和即時跟蹤動物的能力。這將使我們將來有一天能夠標記較小的生物類別,如昆蟲(它們是動物王國中物種數量最多的),並從太空單獨跟蹤它們。畢竟,即使是蝴蝶的遷徙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探索。這自然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一個關鍵的挑戰是為發射器供電,發射器必須在沒有電氣連線的情況下執行。它們最終都會耗盡電量,因為電池無法自行充電。透過智慧、節能技術的發展,動物網際網路正在形成一個更加緊密的結構,將宏觀和微觀視角結合起來。
四個組成部分定義了動物網際網路背後的系統:第一步包括跟蹤動物。緊隨其後的是資料傳輸到行動電話網路和網際網路熱點或太空。然後是第三個組成部分,位於Movebank.org的資料庫,接收和處理資料。最後,視覺化的資料可以以移動應用程式(如Animal Tracker)的形式呈現給科學家、普通人和愛好者。對運動和行為資料的分析提供了對理論和應用生物學領域中眾多問題的深入瞭解,由於缺乏或有限的知識基礎,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長期以來遙不可及。
GPS單元特別適合標記野生動物,因為它們可以從遠處精確定位,而傳統的遙測技術需要研究人員駕駛著收發器追逐動物,這是不允許的。發射器已經變得非常精細和小型化,現在可以跟蹤許多動物數月甚至數年。發射器的重量不應超過動物體重的百分之五,這對研究人員和他們的技術人員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這意味著一個0.70盎司的北美小 Chickadee 的發射器重量不能超過 0.035 盎司。然而,已經制造出重量僅為 0.0007 盎司的發射器。這使得即使是昆蟲也可以被標記。一隻大黃蜂飛多遠才能到達它的食物?它的活動半徑是多少?這在以前是未知的,直到德國南部康斯坦茨湖畔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一個團隊使用發射器來探究這些問題的根源,並發現蜜蜂會飛行數英里才能到達它們的食物來源。
植入野生動物體內的發射器自然會對動物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干擾,並可能阻礙其移動能力。無論該裝置多麼輕巧,仍然存在限制動物移動能力以及其生存機會的危險。將其連線到動物身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幾乎無法想象在不傷害生物的情況下,將發射器縫在三英寸長的紅眼樹蛙身上,紅眼樹蛙的皮膚具有兩棲動物典型的光滑性。在野外實施之前,必須在受控的實驗室條件下反覆測試此程式。每一代新發射器的原型都經過設計,使其在干擾繁殖等關鍵生命活動時,動物可以輕鬆地擺脫這些裝置。
資料傳輸的形式(永久性還是分段性)取決於當地的通訊基礎設施。在缺乏基礎設施的地區或在長途遷徙過程中跟蹤動物時,資料傳輸透過衛星進行;資料被分段,這意味著它們被間歇性地收集並作為捆綁包傳送。為了做到這一點,資訊必須暫時儲存在晶片上。此時的一個重大技術障礙是如何為晶片供電。不同型別的電池發揮作用,從高效能電池到太陽能電池再到動能系統。關鍵的考慮因素是效率,因為電池很難更換。這實際上取決於晶片設計的智慧性。晶片可以被程式設計為僅在特定時間處於活動狀態。或者它們可以被遠端控制以開啟或關閉、捆綁資料或在預定時間上傳資料。也可以在晶片本身上處理收集到的資料,並且僅傳送結果。甚至可以將簡訊回覆程式設計並存儲在晶片上,然後在收到某些訊號時自動傳送。
這項技術經常在西澳大利亞州使用,以警告游泳者和衝浪者靠近海岸的可能對人類構成威脅的鯊魚。這主要適用於大白鯊和虎鯊,其中三百多條已被標記。為了跟蹤它們,首先捕獲這些生物,進行麻醉,然後拉到船上。留在海上的海洋研究人員隨後進行快速手術,將小型發射器植入鯊魚的腹腔。由於無線電波在水中傳播不良,這些裝置會發出水下麥克風拾取的聲音波。每當鯊魚游到麥克風的範圍內時,它都會以個人身份徽章登入。然後,訊號被轉發到監控站網路。這些資料提供了關於動物遷徙模式的重要資訊。當鯊魚越過其中一個所謂的數字“地理圍欄”時,它的到來會透過簡訊或Twitter宣佈。訊號也透過衛星傳輸到安裝在海灘上的監視器。
另一個有點令人毛骨悚然的標記鯊魚的例子證明了GPS技術最終將向我們揭示的鴻溝。在澳大利亞海岸附近,一條十英尺長的,被標記的雌性大白鯊,名為“鯊魚阿爾法”,從雷達上消失了。根據跟蹤裝置,在凌晨四點,鯊魚突然被驚人的力量和速度撕裂到五百碼深處。幾秒鐘之內,晶片還記錄到環境溫度從 8 攝氏度飆升至 25 攝氏度。那是動物體內的溫度;鯊魚一定是被水生食肉動物吃掉了。晶片可以被跟蹤接下來的八天,在那之後它從控制監視器上消失了。它很可能已經排空了。四個月後,它在岸邊被發現,被胃酸漂白了。研究人員懷疑鯊魚阿爾法淪為一種更大的生物的獵物。它必須至少有五米長,重兩噸或更多。但那是什麼呢?虎鯨?虎鯨通常在靠近水面的地方捕獵。有記錄的最深的虎鯨潛水深度為 260 碼。另一條大白鯊?這個物種的體溫為 18 攝氏度——而不是 25 攝氏度。難道真的是一個巨大的章魚或巨齒鯊,一種有人說可能倖存下來的巨型史前食肉動物,隱藏在海洋最黑暗的深處?
正如這個例子所說明的那樣,收集的資料不必僅限於傳送關於動物位置的更新。晶片還可以中繼關於周圍環境條件的資訊,從氣候資料到氣壓和水壓。在某些情況下,專用感測器可以提供關於動物一般生理狀況的讀數。主要關注點可能包括心率、體溫和血糖水平,但更復雜的身體功能也可以透過心電圖、肌電圖或腦電圖測試來捕獲。因此,研究人員可以從遠處確定動物是否生病。這項技術不僅改善了野生動物接受的護理,而且還使科學家能夠更好地確定疾病傳播甚至流行病的預後。最後,這些資料可以與視聽資訊相結合,以傳達每個動物當前情況的最精確的描述;這些描述然後充當現實概況的構建塊。考慮到這一點,馬克斯·普朗克鳥類學研究所所長,動物網際網路的首席動物學家之一馬丁·維凱爾斯基正計劃為鳥類的喙配備微型攝像頭,這些攝像頭由進食期間的特徵性頭部運動觸發。這將允許以高畫質記錄動物的每日選單。
有了如此精確和隨時可用的資料,自然研究人員不再依賴於臆測、推論或他們自己的想象力;這種資訊豐富、客觀的自然形象將對保護運動產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畢竟,這些資料提供了對遷徙路線和種群規模,以及棲息地問題和與人類可能發生的衝突領域的關鍵見解。它們有助於回答長期以來無法回答的問題。
關於動物未知的生活,仍然存在著許多明顯的問題,但在數字技術的幫助下,研究人員正在深入探究這些問題,並利用他們的發現來幫助改善動物的棲息地和生活條件。追蹤水下生活的動物仍然面臨著一些最大的挑戰。然而,對於那些曾經依賴於對海象透過黑暗的北太平洋的曲折路線進行假設的人來說,已經有可能搭乘“佩內洛普女士”的後鰭,並分享她的經歷。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最大的海豹物種的代表在她的 Facebook 頁面上迎接訪客——使用者從Tagging of Pelagic Predators (TOPP) 網站關注該頁面——熱情地說道:“嗨,我叫佩內洛普,我的家鄉海灘是 Año Nuevo,自從我被標記以來,我已經遊了 8,910.04 英里。”
海象特別適合標記,因為它們總是返回同一個海灘。然後可以更換或讀取晶片。由於海象在海洋中長途跋涉,因此它們是有趣的研究物件。研究人員可以從它們的長途旅行中收集大量資料。由於持續的數字監控,佩內洛普的生活故事可以從頭到尾地敘述。除了繪製她的運動軌跡外,她的晶片還記錄了她的潛水深度和長度,以及光線變化。她令人敬佩的歷史如下:1998 年 1 月上半月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海岸的 Año Nuevo 州立公園,當時她的體重只有 46 磅。今天,這位高貴的生物在體重秤上登記了 1500 磅。在她的一生中,就像真正的貴族一樣,佩內洛普鄙視小資產階級的敏感性,拒絕一夫一妻制的習俗,並毫不保留地尋求多個伴侶的陪伴。她生活在一個所謂的 polygynous 社會中,在其中她與其他雌性分享她的伴侶。然而,忠誠從來都不是她的強項,眾所周知,她不時地與來自其他 beta 男性的社交。她有六個孩子,第一個孩子是在五歲時生的。這種無憂無慮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回報——26 歲的佩內洛普可以被認為是她所在物種的偉大幸存者之一。碰巧的是,這些動物中有百分之五十在成熟之前就死亡了。與此同時,佩內洛普已經佔據了更大的舞臺:她最近被整合到 Google 地圖的海洋街景中。她穿越海洋的旅行產生了區域圖片,然後這些圖片被新增到虛擬水下地圖集中。
自 2000 年以來,TOPP 專案已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海洋研究人員聯絡起來。在這段時間裡,動物學家們設法標記了 22 種不同的物種——海象、大白鯊、海龜、魷魚、金槍魚、信天翁——以及 2000 多隻帶有衛星發射器的個體動物。從一開始,該計劃就旨在向公眾提供這些科學資料。其既定目標之一是將這些動物從默默無聞中解救出來,並分享它們的生活故事。這種“讓自然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推動是自然保護新時代的核心特徵。它利用了故事的力量。一方面,科學家們正在使用技術工具,如帶有整合個體動物部落格的網站,或 Shark Net 等智慧手機應用程式,允許使用者選擇他們想要關注的特定鯊魚。另一方面,研究人員也不迴避像年度海象返鄉日這樣的吸引人群的活動,在這一天,返回家鄉海灘的被標記的動物受到啤酒和燒烤的歡迎;或者 Great Turtle Race,其中各種海龜參加虛擬比賽,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島,並在網上直播給粉絲觀看。這些格式的主要目標是以一種有趣的方式讓使用者和觀眾採用動物的視角,從而創造一種聯絡感。自然可以再次變得有趣。
然而,情況的嚴重性不斷回到最前沿。例如,以沿著阿根廷海岸移動的麥哲倫企鵝為例。這些動物在航行於航運線時經常遇到油汙。當石油接觸到它們的羽毛時,企鵝就無法維持體溫,它們會死於體溫過低。那些倖存下來的企鵝飽受健康問題的困擾,並且無法再繁殖。阿根廷海岸的石油汙染每年殺死多達四萬只企鵝。P. Dee Boersma,世界領先的企鵝研究員之一,早在 90 年代中期就開始用 GPS 裝置標記企鵝。這使她能夠確定企鵝通常的遷徙路線。然後,她在與阿根廷航運管理局的談判中使用了這些資料,阿根廷航運管理局同意將其航線移至更遠的海上。如果不是真正保護了麥哲倫企鵝免於滅絕,這一系列事件也極大地提高了這種企鵝物種的存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