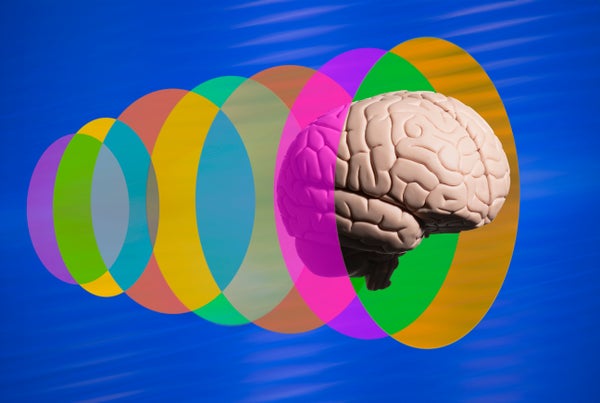當一位攻讀生物統計學博士學位的年輕女性因精神病症狀來找精神科醫生邁克爾·甘達爾時,她成為了直系親屬中第五位被診斷出患有神經發育或精神疾病的人——在她身上是精神分裂症。她的一個兄弟患有自閉症,另一個兄弟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 (ADHD) 和圖雷特綜合徵。他們的母親患有焦慮症和抑鬱症,他們的父親患有抑鬱症。
甘達爾以前見過這種模式。“如果一個人,比如說,他的家庭中有人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症,那麼不僅這個大家庭中的其他人更有可能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他們也更有可能被診斷出患有雙相情感障礙、自閉症或重度抑鬱症,”甘達爾說。這種傾向在家族中遺傳。
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DSM)》(精神衛生領域的診斷標準)描述了近 300 種不同的精神障礙,每種障礙都有其自身的特徵性症狀。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它們之間的界限充其量是模糊的。患有精神障礙的人通常同時或在人生的不同時期出現多種不同疾病的症狀。更重要的是,正如家族模式所暗示的那樣,與這些疾病相關的基因存在重疊。“一切都與基因相關,”倫敦國王學院的行為遺傳學家羅伯特·普洛明說。“相同的基因影響著許多不同的疾病。”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杜克大學心理學家阿夫沙洛姆·卡斯皮說,事實上,很難找到任何型別的特定原因,包括遺傳或環境原因,來解釋個體的精神疾病。大多數神經系統疾病,如癲癇和多發性硬化症,情況並非如此。這些疾病似乎具有獨特的遺傳和生物學起源,這與 2018 年發表的研究結果所表明的“精神疾病的深度互聯性質”形成對比。
換句話說,科學家們說,每個人都有患上各種精神問題的傾向。他們稱這種傾向為一般精神病理學因素,或 p 因子。這種共同的傾向並非是導致某人出現精神疾病症狀程度的次要因素。事實上,它解釋了大約 40% 的風險。
這個概念類似於一般認知能力,或 g 因子,它可以預測空間能力和語言流暢性等技能測試的分數。它表明,將精神健康狀況聯絡起來的因素至少與區分它們的因素一樣重要。卡斯皮說,p 因子的概念“幾乎是為關注共同點而不是專注於不同點而發出的響亮號召”。
一些研究人員呼籲消除精神疾病之間的硬性界限,這可能會對這些疾病的診斷和治療產生巨大影響。“我認為這將是診斷分類方案的終結,”普洛明說。
很難找到任何型別的特定原因,包括遺傳或環境原因,來解釋個體的精神疾病。
儘管鑑於醫生和保險公司依賴於 DSM 的診斷程式碼,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很快發生,但研究人員已經提出了更符合 p 因子概念的替代方案。至少,一些專家表示,包括治療臨床試驗在內的精神健康研究應該擺脫 DSM 的束縛,並將多種診斷納入其中。“我們應該在沒有 DSM 眼罩的情況下看待精神病理學,”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精神科醫生和青年精神健康教授帕特里克·麥戈裡說。
一些科學家已經擺脫了 DSM 的束縛。他們努力揭示可能潛藏在 p 因子下的基因或大腦特徵,這可能會使我們更深入地瞭解精神疾病。“如果你能找到 p 因子正在發揮作用的生物學機制,那麼理論上,如果你能找到針對該生物學機制的方法,”由此產生的治療方法可能對許多精神疾病有效,甘達爾說。
其他人則認為,p 因子不一定反映了精神疾病的共同原因。石溪大學臨床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教授羅曼·科托夫說,它可能反而代表了不同型別精神疾病中存在的品質,類似於發燒等症狀,發燒是對各種病毒性疾病的反應。
最近在《自然評論心理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 p 因子的追求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該論文的作者質疑用於證明 p 因子有效性的統計模型。他們認為,無論 p 因子是否存在,該模型都傾向於確認其存在。“目前非常清楚的是,人們用來聲稱他們發現了 p 因子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存在,”範德比爾特大學心理學家、主要作者阿什利·沃茨說。
然而,專家表示,支援 DSM 現實版本的資料至少同樣站不住腳。手冊中編纂的疾病是從醫生在其患者身上注意到的症狀模式中發展而來的。例如,在 1943 年的一篇論文中,精神科醫生利奧·坎納根據他在 11 名兒童身上觀察到的特徵,概述了自閉症的標準。但是,很難證明由社互動動困難以及重複性和限制性行為定義的疾病真的存在。“我們以什麼為依據說存在綜合徵?這些事情是否會同時發生?”普洛明說。“它們不會同時發生。自閉症的組成部分彼此之間的基因相關性低於主要疾病彼此之間的相關性。”
DSM 的界限是軟性的,即使不是虛構的,更多的證據與以下觀察有關: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精神疾病患者——最近的資料表明,多達 82%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現出跨越這些界限的症狀,有時會導致多種診斷。例如,抑鬱症患者通常患有焦慮症,而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 患者很可能患有物質使用障礙。
麥戈裡說,跨越經典診斷的精神疾病特徵在疾病的早期階段可能最為常見。“這有點像一系列焦慮、抑鬱,可能在很大一部分人中出現一些輕微的精神病預警訊號,在其他人中出現一些情緒不穩定,在一部分人中出現藥物和酒精[濫用],”他說。“如果你從未讀過 DSM,你自然不會想到”該手冊的疾病分類方法會很有用。
DSM 命名的任意性質的另一個跡象與診斷隨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的方式有關。在一項縱向研究中,科學家追蹤了 1972 年和 1973 年在紐西蘭達尼丁出生的約 1000 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在卡斯皮及其同事 2020 年關於 45 歲參與者的報告中,他們發現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健康障礙的人通常會在幾年後看到診斷髮生變化。卡斯皮說,例如,物質使用障礙可能會緩解並讓位於抑鬱症,但隨後又會再次出現,因為抑鬱症被嚴重的焦慮症所取代。
對精神疾病的一般易感性——許多人認為這是 p 因子的本質——可以解釋診斷的流動性。來自遺傳學的證據支援這一觀點。研究表明,基於 DSM 做出的診斷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基因重疊。

Darya Komarova/Getty Images
在精神疾病的全基因組關聯研究 (GWAS) 中,研究人員將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患有特定精神健康狀況的人的基因組與相同數量的沒有這種疾病的人的基因組進行比較。透過這樣做,他們將 DNA 中的微小變化與正在研究的疾病聯絡起來。大約 15 年前發表的首次精神疾病研究表明,與雙相情感障礙相關的許多特定基因版本與精神分裂症相關的基因版本相同。“我們認為截然不同的這些東西,最顯著的是雙相情感障礙和精神分裂症,根本不是截然不同的,”普洛明說。“這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從那時起,研究人員對幾乎所有其他主要精神疾病——包括 ADHD、PTSD、抑鬱症和強迫症 (OCD)——進行了跟進,並發現了許多所有這些疾病共有的基因。這些基因的完整集合已被稱為“遺傳 p 因子”,這是一種控制精神病風險的生物學槓桿。“這是一個統計抽象,”普洛明說,“但這非常重要,因為它表明許多基因對其心理健康的影響是普遍的。”
研究人員現在正試圖瞭解這些基因的生物學作用可能是什麼。2019 年,一個團隊在丹麥全國近 150 萬人的出生佇列中,對抑鬱症、厭食症、自閉症、雙相情感障礙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和神經發育障礙進行了 GWAS 研究。研究發現,這些疾病共有的基因變異在胎兒神經發育中起作用。“隨著大腦的發育,這確實是一個關鍵時期,許多生物學過程正在顯現”——這些過程可能會影響精神病風險,該研究的作者之一甘達爾說。
甘達爾和他的同事最近發現了與 p 因子特異性相關的基因變異,這部分解釋了青少年大腦認知發展 (ABCD) 研究中 10,000 名青少年的精神病症狀,科學家們在 2023 年美國人類遺傳學會會議上報告了這一發現。此後,研究人員一直在研究該研究和其他研究確定的特定基因版本的生物學功能。“我們現在可以解析[分子作用],大約 60% 的遺傳命中,”他說。
“當我在研究僅僅患有抑鬱症而沒有其他疾病的人時,我到底在研究什麼?”
——阿夫沙洛姆·卡斯皮 杜克大學
其他尋找 p 因子意義的人正在檢查大腦結構。在 2020 年的一項研究中,對 12,000 多名患有六種主要精神疾病之一的人進行的大腦掃描顯示,四種疾病(重度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精神分裂症和強迫症)的結構差異相似,而 ADHD 和自閉症的結構差異不同。2023 年一項類似的針對 5,549 名患有自閉症或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或重度抑鬱症的人的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或抑鬱症患者的大腦皮層變薄的模式是相同的。
p 因子也可能源於共同的精神特徵。“在我從生物學角度向你解釋之前,我想先在[心理層面]理解,‘是什麼真正將許多不同的疾病聯絡在一起?’”卡斯皮說。情緒調節困難是一種可能性,但卡斯皮懷疑共同點是思維紊亂:認知扭曲,這可能以精神病中的妄想、焦慮中的非理性恐懼、抑鬱症中的本能消極情緒或強迫症中的侵入性思維的形式出現。他說,這目前只是推測,但一旦人們確定了心理上的中心是什麼,“你就有了一個可操作的目標,也許你可以開始從生物學的角度來思考它。”
p 因子可能存在對精神健康研究的開展方式具有影響。首先,它讓人懷疑將治療臨床試驗限制在僅患有一種疾病(如抑鬱症)的參與者身上的做法。畢竟,許多精神疾病患者患有不止一種診斷。“當我在研究僅僅患有抑鬱症而沒有其他疾病的人時,我到底在研究什麼?”卡斯皮問道。“這不一定代表這種情況。”相反,他說,科學家應該將研究和療法瞄準精神疾病的更一般特性。
大約十年前,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 (NIMH) 啟動了一個名為研究領域標準 (RDoC) 的專案,旨在做到這一點,或者,按照該機構為此目標制定的術語,鼓勵“對跨越疾病的維度結構進行研究”。該計劃旨在資助旨在研究人類行為(包括典型行為和非典型行為)的生物學根源的研究,以此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但批評者指責該機構沒有貫徹這一使命。當麥戈裡想要將 NIMH 資助的精神病風險研究擴大到更廣泛的診斷範圍時,他被告知堅持最初的想法,即專注於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因此,我認為他們甚至沒有資助 DSM 類別之外的專案,儘管他們說 RDoC 是他們的範例,”麥戈裡說。
NIMH 反駁說,它繼續鼓勵和支援使用 RDoC 原則研究精神病理學的專案,並估計已經資助了數百個此類專案。該機構表示,其中一些專案側重於瞭解被診斷出患有 DSM 定義的相同疾病的人之間的差異,而另一些專案則試圖識別在 DSM 診斷中觀察到的生物學和行為機制。然而,NIMH 並非專門資助採用 RDoC 方法的研究,它表示 RDoC 方法“對於某些專案比其他專案更合適”。
p 因子對臨床決策應該意味著什麼尚不確定。沒有人說所有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都是一樣的。幻覺、酗酒、飲食失調和社交焦慮等症狀顯然不會在精神疾病患者中統一齣現。事實上,普洛明最近測量了 11 種疾病中的任何一種疾病的基因變異與 p 因子無關的程度。例如,他將 ADHD 的這種測量稱為“非 p 因子 ADHD”。“沒有人說這全是 p 因子。只是說存在 p 因子,”普洛明說。
沃茨對 p 因子持懷疑態度,她認為精神疾病更可能分為幾個廣泛的類別,而不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徵。她說,所謂的內化障礙——抑鬱症、焦慮症、PTSD 和其他以負面情緒為特徵的疾病——往往會重疊,並且對相同的治療方法有反應。“外化”行為(如多動症、攻擊性和違反規則)也是如此,這些行為反映了缺乏衝動控制。“我認為證據非常清楚地支援這些更廣泛的高階維度的存在,但不一定支援 p 因子的總體維度,”沃茨說。
然而,即使是廣泛類別的想法也與 DSM 的劃分不一致。“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這些診斷周圍劃定任意界限,”沃茨說。這些界限反映了另一個謬論:精神疾病與健康是截然不同的。實際上,抑鬱症、物質依賴和社交焦慮等疾病的嚴重程度在人群中變化,遵循經典鐘形曲線的模式。大多數人經歷中度症狀,這反映在曲線中間的大凸起中,左側是輕度病例,右側是重度病例的較小“尾部”。沒有明顯的臨界點。
科托夫和其他人提出了框架,試圖捕捉特定疾病的嚴重程度。在科托夫及其同事開發的精神病理學分層分類法 (HiTop) 中,根據患者 100 多種精神病症狀中每種症狀的嚴重程度對其進行評分。結果是特定於個人的評分組合。“每個人都由一個概況來表示,因此診斷成為一個概況,而不是一個標籤或標籤列表,”科托夫說。
一些研究人員旨在透過長期觀察患者來提高診斷的特異性。在對 5,432 名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進行的縱向研究中,甘達爾及其同事發現了五類人在其一生中具有相似的診斷模式。甘達爾在談到 2021 年的結果時說,這是朝著識別精神分裂症亞型邁出的一步,這些亞型可能會在基因上得到進一步定義。
麥戈裡贊成一種分期系統,該系統類似於用於癌症的分期系統,側重於疾病的嚴重程度而不是其性質特徵。“分期想法允許以跨診斷型別的方式捕獲和驗證症狀的流動性,”麥戈裡說。麥戈裡認為,這也有助於緩和疾病與健康之間存在硬性界限的看法,從而減少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反過來,這可能會鼓勵更多痛苦中的人尋求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