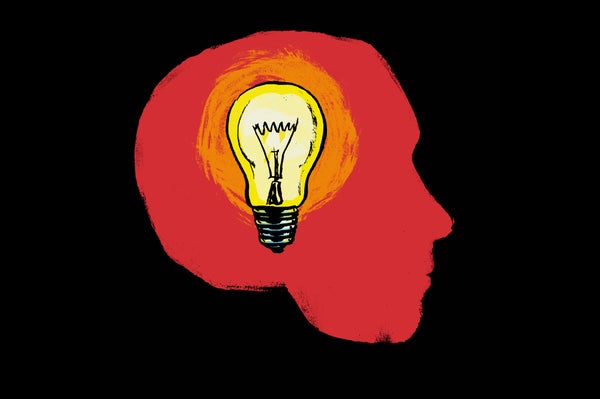創造力使人類能夠征服地球的每一個角落。的確,我們對創新的渴望是我們人類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然而,我們這個物種並不是唯一具有創造力的物種。研究人員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其他生物身上記錄了這種能力。他們的一些發現與關於創造力的起源以及如何在人類思維中培養創造力的傳統觀念背道而馳。
關於創造力的老話當然是它源於必要性。蘇黎世大學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卡雷爾·範·沙伊克根據他對猩猩的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當食物稀缺時,猩猩會進入節能模式。它們會盡量減少活動,專注於不太吸引人的後備食物,”他觀察到。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策略與創新截然相反,但這很有道理。“嘗試新事物可能是有風險的——你可能會受傷或中毒——而且這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和注意力的投入,而結果總是 uncertain,”範·沙伊克解釋說。
對面臨匱乏的人類研究與範·沙伊克對猩猩的發現相呼應。2013年,《科學》雜誌發表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森德希爾·穆萊納坦和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埃爾達·沙菲爾的一項研究,描述了提醒低收入人群他們的經濟困境如何降低他們在新情況下進行邏輯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隨後的一項研究發現,印度甘蔗農民在收到一年一次的農產品付款後,在同一認知能力測試中表現得更好,暫時解決了他們的經濟擔憂。(以前沒有參加測試的農民在獲得報酬後也表現得相當好,因此改進不太可能是之前測試經驗的結果。)當然,人們會盡一切努力生存,這偶爾可能會帶來創新。但正如這些和其他研究表明的那樣,如果一個人總是專注於諸如尋找食物、住所或支付賬單等緊迫問題,那麼就沒有多少能力來提出改善生計的長期解決方案。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事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那麼創造力從何而來呢?洞察力來自於一個令人驚訝的觀察,即猩猩在圈養狀態下可以非常有創造力。“如果食物充足且沒有捕食者,它們突然有很多空閒時間,可以擺脫這些干擾,”範·沙伊克解釋說。此外,在它們高度受控的環境中,探索很少會產生不愉快的後果,而且有很多不尋常的物體可以玩耍。在這種情況下,猩猩似乎失去了它們通常對未知的恐懼。在2015年發表在《美國靈長類動物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中,範·沙伊克和他的同事比較了野生和圈養猩猩對新引入物體的反應,這是一個形狀像猩猩巢的小平臺。雖然圈養的猩猩幾乎立即接近新物體,但大多數野生猩猩,儘管已經習慣了人類的存在,但在幾個月的測試中甚至沒有靠近它——只有一隻最終敢於觸控它。這種對新奇事物的恐懼可能對創造力構成重大障礙:如果動物避免接近任何新物體,創新就會變得相當不可能。“所以如果你問我,機會是發明之母,”範·沙伊克評論道。
同樣,對多種鳥類以及斑鬣狗的研究表明,更渴望探索新事物的個體往往是最具創新精神的個體。這種好奇心也可能是人類創造力出現的驅動力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專家們通常試圖研究兒童的創新問題解決能力。但事實證明,這種調查非常具有挑戰性,尤其因為孩子們似乎不是很具有創新精神。在2011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伯明翰大學的研究人員要求不同年齡段的英國兒童使用他們得到的直而柔韌的管道清潔器,從洞底夠不著的貼紙桶中取出貼紙。九年前,在2002年,一隻名叫貝蒂的圈養新喀里多尼亞烏鴉解決了同樣的問題,將直鐵絲彎成鉤子來取桶,桶裡裝滿了誘人的食物,因此上了頭條。(科學家們後來觀察到她的物種在野外製作鉤子和彎曲樹枝。)但這項挑戰難住了大多數5歲兒童和大約一半的8歲兒童。昆士蘭大學心理學家馬克·尼爾森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西方兒童並不是唯一被這項任務難住的人:南非布須曼人的孩子也覺得同樣困難。
年輕人在鉤子和水桶挑戰中表現不佳,部分原因可能在於實驗進行的條件。今年早些時候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B哲學彙刊》上的一項初步研究是在匹茲堡兒童博物館進行的,那裡鼓勵積極探索和操作工具。這項實驗中4至5歲的兒童比早期研究中接受測試的兒童表現得更好,早期研究中的兒童偶爾會對研究人員向他們展示技巧時允許彎曲金屬絲表示驚訝。“但我們確實需要更大的樣本才能對我們的發現更有信心,”喬治梅森大學教育心理學家金伯利·謝里丹說,她與同一機構的阿比蓋爾·科諾帕斯基一起領導了這項實驗。
創新故事的新轉折出現在9月14日,當時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克里斯蒂安·魯茨和他的同事在《自然》雜誌上報道說,另一種鳥類——夏威夷烏鴉,或稱 ʻalalā——也會製造和使用工具。雖然這種鳥在野外已經滅絕,但科學家測試的幾乎所有圈養成年鳥和近一半的圈養幼鳥都使用樹枝和其他物體從隱藏的地方取回食物,並且經常改變工具材料來實現這一點。該物種的如此多的鳥類自發地使用工具,再加上幼鳥在沒有觀察到長輩的情況下就掌握了這項技能,這向魯茨表明,這種行為可能是該物種的一個特徵,而不是最近的創新。儘管如此,這些鳥類使用工具可能起源於進化史上的創造性創新。喜歡使用工具的鳥類覓食成功率的提高可能導致自然選擇發揮作用,從而促進這種有利趨勢的遺傳因素。在這種情況下,鳥類的生態可能在工具使用和改進的第一個創造性步驟中發揮了作用:由於在島嶼家園上捕食者或競爭者很少,夏威夷烏鴉有自由——機會——嘗試新事物。
伯明翰大學的傑基·查佩爾說,到目前為止,試圖找出哪些個人特徵可以解釋兒童解決任務能力差異的嘗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定論,她曾與鳥類(包括貝蒂)以及兒童一起工作。“只有年齡和詞彙量具有預測性。一種可能性是,當智力達到一定水平以上時,創新的差異主要歸因於外部因素,尋找兒童創新者是沒有用的。我們會拭目以待。”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喬·亨裡奇最近寫了一本書,探討文化在我們物種成功中所起的作用。他預計情況確實如此。“我認為創新依賴於個人天才的想法是 misguided 的。歷史表明,發明總是建立在早期發現的基礎上,這些發現被重新組合和改進。我們每天使用的大多數東西都是任何單個人在其一生中都無法設計的發明,”他觀察到。“這些發明與其說是個人創新者的產物,不如說是我們社會的產物。創新依賴於個人向他人學習——透過這種方式,人類社會就像一個集體大腦一樣運作。”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心理學家邁克爾·穆圖克裡希納是亨裡奇的合作者,他補充說,在很大程度上,智商等個人智力指標可能是與社會其他成員進行知識交流的產物。“透過這種方式,社交性可能是發明和智慧之母:社會的規模和相互聯絡,使我們能夠聯絡和分享更多的想法,”他反思道。與範·沙伊克一樣,亨裡奇和穆圖克裡希納認為,創新應該受益於失敗成本的降低,而不是增加。穆圖克裡希納說:“透過降低風險,社會安全網可以刺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