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與歷史一樣古老,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更古老。例如,公元前 68 年,羅馬城市奧斯蒂亞是世界上最早的超級大國之一的重要港口,被一群暴徒縱火焚燒。他們摧毀了領事戰爭艦隊,並且相當尷尬地綁架了兩名高階參議員。恐慌隨之而來——同樣的恐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重演,這要歸功於諸如愛爾蘭共和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基地組織以及最近的 ISIS 等恐怖組織。在撰寫本文時,世界在 20 天內目睹了三起重大恐怖襲擊——貝魯特、巴黎、聖貝納迪諾——緊隨其後的是伊斯坦布林、喀布林、迪誇、奈及利亞和其他地方發生的額外暴行,每次都是由伊斯蘭極端分子實施的。正如 19 世紀德國曆史學家西奧多·蒙森描述奧斯蒂亞的罪犯是“來自各國的破落戶”組成“一個具有特殊集體精神的海盜國家”一樣,今天的政治領導人通常將恐怖分子描述為精神錯亂、精神失常或純粹的邪惡。
那麼心理學家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相當多。但是,他們冷靜的觀察似乎被參議員、名人和其他人對伊斯蘭教發動他們自己的修辭聖戰的過於熟悉的合唱聲淹沒了。當我們繼續努力應對暴力極端主義的挑戰時,也許我們都應該進行一次大腦檢查。也許我們應該傾聽來自我們一些實驗室的更安靜、更敏銳的聲音,而不是鸚鵡學舌地重複那些好辯的評論員和好戰的吹牛大王刺耳的叫囂。
或者更確切地說,也許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應該這樣做。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有助於確保有關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誠然,科學和政治常常成為不舒服的床伴。歷史證明,兩者之間令人遺憾地發生了一系列即興的幽會,孕育了不人道的意識形態。想想種族滅絕的雅利安至上主義者殘酷地綁架了主流進化論,並透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媒介將其令人作嘔地重塑為納粹主義教條。然而,面對暴力極端主義的日益高漲,如果我們科學家只是袖手旁觀,無所作為,似乎就太失職了。
因此,在本文中,我們挺身迎接將社會心理學置於反恐戰爭中心舞臺的挑戰。我們不會假裝這很容易:多年來,該領域產生了大量經過經驗洗滌的智慧。但在與一個國際專家小組進行熱烈的討論之後,我們集中研究了來自社會認知到衝突解決等廣泛研究領域的七項典範研究。我們相信,每一項研究不僅對政策決策具有直接意義,而且對我們所有身處快速變化世界中的個人也具有直接意義。
1. 你和我在一起嗎?

哈里·馬爾特
研究: “虛假共識”效應:社會認知和歸因過程中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偏差。 李·羅斯、大衛·格林和帕梅拉·豪斯(1977 年)
研究領域: 社會認知
概述: “永遠記住,你是絕對獨特的,”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俏皮地說。“就像其他人一樣。” 她說得很對。難道我們不都認為自己是“正常的”嗎?這項經典研究考察了我們有多容易受到一種錯覺的影響,即我們的選擇、判斷、感受和信仰也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
方法論: 調查人員向大學生展示了真實和假設的任務(例如,他們是否願意在校園裡戴著三明治板,作為態度改變研究的一部分?),並要求他們表明自己的反應。他們還要求他們估計他們認為會以相同方式回應的其他學生的百分比。
發現: 參與者始終認為他們自己的個人判斷廣泛代表了他們同學的觀點。這種現在已得到充分證實的效應已被稱為虛假共識偏差。
啟示: 這個實驗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在“做自己”這件事上,我們人類既想擁有蛋糕,又想吃掉它。我們陶醉於成為我們自己的人的想法,但我們的大腦是為群體生活而生的。因此,自然選擇想出了一個漂亮的小應用程式,它為我們提供了與其他人一樣的錯覺。它告訴我們,我們的行為選擇是理性的和適當的,同時為我們提供了我們渴望的社會認知自主權。在大多數情況下,它都執行良好: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政治家在選舉前經常表現出如此奇怪、毫無根據的樂觀情緒?但偶爾,當一點點好戰的信念轉移成惡性意識形態腫瘤時,共識的錯覺可能會變得致命。這在群體中尤其危險;在沒有任何其他觀點挑戰的情況下,腫瘤會迅速變得具有攻擊性。
政治家和公眾必須願意質疑他們的假設——關於恐怖主義、關於移民、關於宗教——以免他們陷入虛假共識的陷阱。
2. 看到什麼,說什麼

哈里·馬爾特
研究:群體對旁觀者在緊急情況下干預的抑制。 比布·拉塔內和約翰·M·達利(1968 年)
研究領域: 群體決策
概述: 為什麼人們有時在面對危險時無所作為?這項來自社會心理學史冊的殿堂級研究調查了其他人的存在對緊急情況下決策產生的強大而令人驚訝的影響。要採取行動,個人必須首先注意到事件,將其解釋為緊急情況,並承擔個人責任進行干預。該研究表明群體動力學如何打破該鏈條中的環節。
方法論: 被分配完成問卷調查的男大學生髮現自己身處一個開始充滿煙霧的房間。他們是獨自一人,三人一組,或者由兩名參與實驗且沒有反應的人陪同。有人會離開房間報告煙霧嗎?
發現: 大約 75% 的單獨參與者報告了煙霧,而三人一組的參與者只有 38% 報告了煙霧。那些由冷漠的研究同夥陪同的受試者呢?只有 10% 的揉眼睛、揮舞煙霧的斯多葛派人士拉響了警報。
啟示: 這項研究表明,對於任何可能取決於不熟悉的行為或決定的行為,我們都會參考其他人。不幸的是,緊急情況通常始於模稜兩可、可能無害的情況。而且,由於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避免尷尬的熱情支持者,因此我們會參考他人的行為來告知我們自己的行為。如果他們不行動,我們就不行動。
因此,政策制定者的一個關鍵挑戰是促進心理學家所說的“人際賦權”的文化傳播:我們都對影響他人福祉以及我們自己福祉的結果負責的意識。簡單的干預措施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張貼海報,例如,海報上可能顯示一個可疑的包,並警告說:“不要指望別人。這取決於你!”
我們都會從定期提醒中受益,這樣我們的旅鼠式傾向就不會妨礙挫敗恐怖襲擊。同樣,在極端主義團體內部,同樣的抑制可能也在起作用,阻止成員質疑令人髮指的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行為就變成了常態。
3. 群聚和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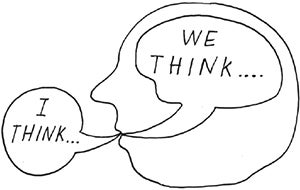
哈里·馬爾特
研究:通過了解你是誰來了解該思考什麼:自我分類與規範形成、從眾和群體極化的性質。 多米尼克·艾布拉姆斯等人。(1990 年)
研究領域: 信仰形成
概述: 有時我們想要第二個意見,但事實證明,我們對信任誰來提供意見是有選擇性的。這種偏見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它甚至影響了我們對物理現實的感知。本文中的實驗表明,我們如何錯誤地認為與我們認同的人比我們歸類為“不同”的人更清楚地瞭解現實。
方法論: 調查人員向一組六名參與者展示了經典的視錯覺,即自動運動效應,在一個漆黑的房間裡。在這種錯覺中,一個靜止的光點似乎在不同的方向移動約 15 秒。在一系列試驗中,參與者必須大聲估計他們認為聚光燈從起點到達的最遠距離。但有一個陷阱。該小組的一半是秘密特工,研究人員向他們介紹了將真實參與者的判斷延長五釐米。此外,實驗人員巧妙地操縱了其中一些秘密特工的社會身份,使他們或多或少地類似於真正的參與者。群體“歸屬感”會導致參與者增加他們的估計以匹配滲透者的估計嗎?
發現: 絕對是!參與者和秘密特工之間的明顯差異越大——他們看起來有多麼不屬於不同的社會群體——他們的估計差異就越大。
啟示: 這裡有兩個主要資訊。第一個是我們效仿我們認同的人的榜樣,而無視其他人。因此,圍繞社會差異的政策框架至關重要。溫和、中年的伊瑪目譴責狂熱、年輕的原教旨主義者固然很好,但年輕人什麼時候認同過當權派呢?第二——社群和宗教領袖請注意——當我們不確定如何處理給定的情況時,我們依靠我們自己社會群體中的人來決定什麼是適當的反應。在健康的文化熔爐中,這很好。但是,當群體開始與傳統社會隔離時,這種天生的“群聚和規範”傾向可能會形成小團體、邪教和其他型別極端分子的跳板。
以下兩點:首先,我們的領導人必須積極尋求來自他們自己群體以外的專家的證據和建議。其次,他們應該嘗試找到阻止群體漂向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孤立狀態的方法。
4. 部落聯絡

哈里·馬爾特
研究:社會分類和群體間行為。 亨利·塔吉費爾等人。(1971 年)
研究領域: 群體動力學
概述: 如前所述,我們人類天生就是群體的一部分。但是,自然選擇設法多麼一絲不苟地安裝了我們的部落電路,以及它的開關多麼容易被撥動,直到這篇經典論文巧妙地將克利置於康定斯基之間才完全顯現出來。
方法論: 志願者評估了不熟悉的、未署名的藝術品,然後在一個完全捏造的、任意的基礎上被分成兩組:一半人被告知他們喜歡的畫作是藝術家保羅·克利的;另一半人聽說他們更喜歡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作品。事實上,分配是完全隨機的。一旦被放入這些毫無意義、零熱量的群體中,並且不知道還有誰在其中,每個參與者都被賦予了一項完全不相關的任務:向兩位同伴研究物件分配積分——這些積分可以轉化為金錢。這些同胞是匿名的,但以下身份標籤除外:克利小組或康定斯基小組的成員。參與者是某個群體而非另一個群體的簡單事實會影響他們對積分的分配嗎?
發現: 參與者慷慨地向自己群體的成員發放積分——以及獲得經濟獎勵的前景——並堅定地拒絕向另一群體的成員發放積分。公平蕩然無存。那是“我們這群人對抗另一群人”。句號。
啟示: 不難理解群體內偏見的威力。您所要做的就是出現在足球比賽中或登入 Facebook。但常識不太容易接受,而本文如此優雅地證明的是,這種忠誠可以在沒有終生效忠於野馬隊、巨人隊或老鷹隊——或伊斯蘭教、基督教或猶太教的情況下獲得。將人們歸類為所謂的最小群體——除了名稱之外,沒有任何區分特徵的群體——足以喚醒一種立即的、可能是祖先的對積極的群體內獨特性的渴望。我們與他們的心態——所有歧視和偏見的心理零點。
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是利用這種內建的成為“夢之隊”一部分的動力來造福社會。我們需要減少我們-他們區分的心理契合度的策略。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彈藥:關注每個人作為獨特的個體;關注超級我們,一個將每個人捆綁成一個群體的類別(例如,人類);或者放大我們類別中與他們類別相交的各種類別(例如,性別、年齡和國籍,甚至是對籃球的熱情)。所有這些方法都可以幫助消除人們將他們所有的心理積蓄都押在那唯一一把存在主義撲克牌上的傾向。
5. 極端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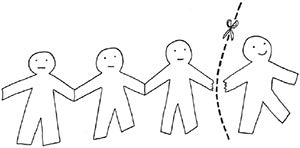
哈里·馬爾特
研究:為自己的群體而死和殺戮:身份融合緩和了對群體間版本的有軌電車難題的反應。 威廉·B·斯旺等人。(2010 年)
研究領域: 社會身份
概述: 許多人對“重要”的事業高度投入,但很少有人會為此獻出生命。是什麼區分了這些意識形態極端分子?根據本文,他們個人身份和群體身份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
方法論: 研究人員比較了兩種型別的西班牙人:個人身份與國家身份“融合”或未“融合”的人。志願者面臨著經典有軌電車難題的一種自我犧牲形式的三個版本:五名西班牙人、五名歐洲同胞或五名美國人即將被失控的有軌電車撞死。但是,如果您從橋上跳下,跳到有軌電車的軌道上並死去,那麼這五個人將倖免於難。在第四項研究中,他們被問到:您是否允許一名西班牙同胞跳下去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殺死五名恐怖分子,或者您會推開那個人自己跳下去?
發現: 與那些身份未融合的參與者相比,身份融合的參與者更有可能犧牲自己來拯救他們的同胞。這種“道德義務”告知了身份融合的參與者決定保護歐洲人的生命——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擴大的群體內成員——並犧牲自己代替同胞來消滅五名恐怖分子。然而,當涉及到避免美國人或群體外人員死亡時,他們的道德信念就消失了。
啟示: 令人震驚的自殺式襲擊變得越來越普遍。但是,那些聲稱實施此類行為的人要麼是千載難逢的精神病患者,要麼是被洗腦的異議人士,都忽略了導致他們進行大規模謀殺的根本心理因素。這項研究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啟示。對於某些人來說,認同一個群體的通常過程演變成一種超越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們個人的認知、情感和道德能動性完全沉浸在集體的普遍要求中。他們變得人格解體,以至於將自殺視為對其融合群體自我的自我拯救行為。
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專業人士的中心資訊是,識別出此類人格並制定干預計劃——透過學校和輔導員,以及在我們組織和制度結構內——旨在解除自我身份的融合或首先防止融合,可以顯著降低政治或宗教殉難的風險。
6. 認識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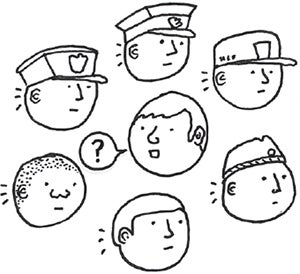
哈里·馬爾特
研究:接觸批評自己群體的群體外成員有助於群體間開放。 塔瑪·薩古伊和埃蘭·哈爾佩林(2014 年)
研究領域: 衝突解決
概述: 也許不足為奇的是,當自己群體內的成員批評我們團隊的態度、信仰或行為時,我們不喜歡這樣。但是,如果我們是群體外成員,我們會有什麼反應呢?這項研究表明,當我們的一位競爭對手批評自己人時,它可以顯著提高我們對該群體事業的同情心。
方法論: 研究人員向以色列參與者展示了各種關於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虛構聯合國報告。摘要在三個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它們是否包含對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行為的任何批評;這種批評是由巴勒斯坦官員還是來自歐洲或中國的“外部”來源提出的;以及批評是否與衝突有關。來自巴勒斯坦人自身的對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評會削弱以色列人對他們的頑固態度嗎?
發現: 答案是謹慎的肯定。閱讀了巴勒斯坦人自我批評的參與者——無論批評是否與衝突相關——都認為巴勒斯坦人比那些閱讀了來自中國或歐洲來源的不贊成宣告或那些根本沒有看到批評的人更思想開放。他們變得更理解巴勒斯坦人對局勢的看法,更希望找到和平解決方案,並且更願意探索妥協的可能性。
啟示: 在當前文化兩極分化的氛圍中,這項研究的結果與它們令人驚訝的程度一樣重要。群體內譴責很可能要付出叛徒變節者的代價。但是,作為開啟大門的一種手段——向警惕的群體外提供心理橄欖枝,並打破好戰的、根深蒂固的信仰的防禦工事——它不應被低估。伊斯蘭領導人,請注意!你們公開批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犯下的恐怖暴行可以積極影響西方公眾對主流伊斯蘭教的看法,挑戰有偏見的刻板印象。同樣,美國和歐洲當局在公開辯論其外交政策的明智性時越透明,他們就越能引起對西方帝國主義動機抱有揮之不去的懷疑的穆斯林的同情。
7. 悖論式啟動

哈里·馬爾特
研究:悖論式思維作為促進和平的新幹預途徑。 博阿茲·哈梅里等人。(2014 年)
研究領域: 說服和態度改變
概述: 我們如何才能克服群體之間的歷史恩怨?這項獨特的縱向實地研究揭示了一種非正統的干預措施如何幫助打破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固有的僵化社會心理障礙。
方法論: 一組親以色列支持者對照組觀看了中立的以色列旅遊影片。另一組人被啟動以“悖論式”思考巴勒斯坦衝突:具體而言,他們觀看了認可與他們自己一致但被推向極端的觀點的影片。例如,這些影片表達了諸如“我們需要衝突來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類的想法。這種非理性的誇張會促使他們重新考慮他們最初的立場嗎?
發現: 這項所謂的悖論式干預是在 2013 年以色列大選前進行的,它軟化了參與者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態度。它甚至影響了他們打算如何投票,增加了他們支援對實現和平感興趣的政黨的可能性。
啟示: 在某些情況下,對抗極端主義哲學的有效解藥可能是“看到”支持者的態度立場,然後“提高”它們。例如,為了對抗極端原教旨主義,更溫和的宗教領袖可能會與個別極端分子辯論“永遠不應允許婦女離開家園”的論點。這些在意識形態上一致但在實踐中荒謬的錯誤原則的延伸可能有助於迫使人們重新評估他們的想法。
最終分析
我們描述的每項研究產生的見解都得到了充分檢驗的理論和額外證據的支援或反過來促成了這些理論和額外證據。因此,它們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的有力視角。當然,科學理論有時會脫軌。但社會心理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人類行為的一些最佳工具。當尋求找到最佳前進道路時,許多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仍然將他們的信念寄託在占卜師和專欄文章或預言家的含糊不清的溢位物上,而不是科學分析,這對常識的訓誡來說是一個了不起的譴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