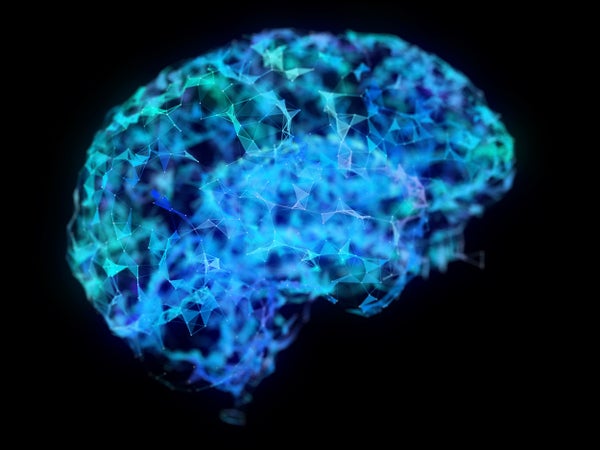當赫伯特·溫斯坦因 1992年因謀殺妻子罪受審時,他的律師們對他敘述妻子死亡以及之前事件時表現出的冷靜沉著感到震驚。他沒有試圖否認自己有罪,然而,面對他極不尋常的行為,他的冷靜使得辯護律師懷疑他可能並非如此。溫斯坦因接受了神經影像學檢查,證實了律師們的懷疑:一個囊腫壓迫了溫斯坦因額葉的大部分割槽域,額葉是大腦中控制衝動的部分。基於這些理由,他們認為他應該以精神錯亂為由被判無罪,儘管溫斯坦因自由承認有罪。
內疚感難以定義,但它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我們是責備自己跳過鍛鍊,還是在刑事審判中擔任陪審員。人類似乎天生就渴望正義,但我們也揹負著一種奇怪的衝動,想要描繪我們自己的情感線路圖。這種為我們的瘋狂行為賦予神經化學方法驅動力,導致了大量神經影像學研究目錄的生成,這些研究詳細描述了從焦慮到懷舊等一切事物的神經基礎。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聲稱我們離了解有罪的大腦是什麼樣子又近了一步。
由於內疚感因情境或文化而異,該研究的作者選擇將其操作性地定義為意識到自己傷害了他人。一系列針對兩個獨立群體(一個瑞士群體和一箇中國群體)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實驗揭示了他們所說的“與內疚相關的腦部特徵”,這種特徵在不同群體中持續存在。由於普遍存在的內疚感是嚴重抑鬱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常見特徵,作者認為,內疚感的神經生物標誌物可以為這些疾病以及潛在的治療提供更精確的見解。但是,複雜人類行為的基於大腦的生物標誌物也適用於更具倫理爭議的學科——神經預測,這是一個新興的行為科學分支,它結合了神經影像學資料和機器學習,以預測個人根據其大腦掃描與其他群體的比較結果,可能採取的行動。
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預測演算法已在醫療保健、廣告以及最臭名昭著的刑事司法系統中使用了多年。面部識別和風險評估演算法因其種族偏見以及在將罪犯分配到“高風險”與“低風險”類別時,準確性明顯較低而受到批評。最近新聞中此類偏見曝光程度最高的事件之一是2018年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關於亞馬遜Rekognition面部識別和分析演算法的報告,該演算法在針對犯罪檔案資料庫執行時,錯誤地將28名國會議員識別為罪犯。有色人種佔被錯誤識別個人的近40%,約為他們在國會中所佔比例的兩倍。亞馬遜當時公開對該研究採用的方法提出異議。然而,就在今年夏天,在一場旨在拆除警察和刑事司法中種族偏見結構的全國性運動中,亞馬遜暫停了執法部門對Rekognition的使用為期一年,這場運動旨在拆除導致有色人種死亡和監禁比例過高的種族偏見結構。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神經影像學資料在理論上應該消除當預測演算法基於社會經濟指標和犯罪記錄進行訓練時出現的偏差,其依據是生物學指標本質上比其他型別的資料更客觀。在一項研究中,來自尋求藥物濫用治療的被監禁人員的fMRI資料被輸入機器學習演算法,試圖將大腦中稱為前扣帶皮層(ACC)區域的活動與完成治療計劃的可能性聯絡起來。該演算法能夠在大約 80% 的情況下正確預測治療結果。研究人員在類似的 功能影像學研究中,已將ACC活動的變化與暴力、反社會行為和再次被捕的可能性增加聯絡起來。事實上,在腦海中尋找內疚感的神經中樞也指向了ACC。
然而,fMRI 的問題之一是,它並不直接測量神經放電模式。相反,它使用大腦中的血流作為神經活動的視覺代理。複雜的行為和情緒狀態會調動大腦中多個廣泛分佈的部分,這些網路內的活動模式比檢視各個區域的活動快照提供更多的見解。因此,雖然執法部門可能很想得出結論,即低ACC活動可以作為累犯風險的生物標誌物,但ACC啟用模式的改變也是精神分裂症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的標誌。在刑事司法背景下使用行為生物標誌物,非但沒有透過使用假定的客觀神經活動解剖學標記來減少偏見,反而有鼓勵將精神疾病和神經多樣性定為犯罪的風險。
fMRI 作為一種方法,可能還存在其他侷限性。最近一項大規模的 fMRI 研究綜述得出結論,即使在個人層面,結果的可變性也太高,無法有意義地將其推廣到更大的群體,更不用說將其用作預測演算法的框架。風險評估演算法本身的概念是基於人們不會改變的決定論預設。事實上,這種決定論是這些演算法所服務的報應性司法模型的特徵,這些模型側重於懲罰和監禁罪犯,而不是解決導致逮捕的條件。
事實上,這種將腦部成像作為人類行為預測工具的使用,忽略了神經科學的一個基本事實:大腦和人一樣,能夠改變;它們會根據經驗不斷地在電學和結構上重塑自身。神經預測不僅僅是代表一種技術上更復雜的實施懲罰的手段,它還具有識別這些相同特徵並提供干預途徑的能力。任何演算法,無論多麼複雜,都將始終像使用它的人一樣有偏見。在我們重新審視我們處理犯罪和正義的基本方法之前,我們無法開始解決這些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