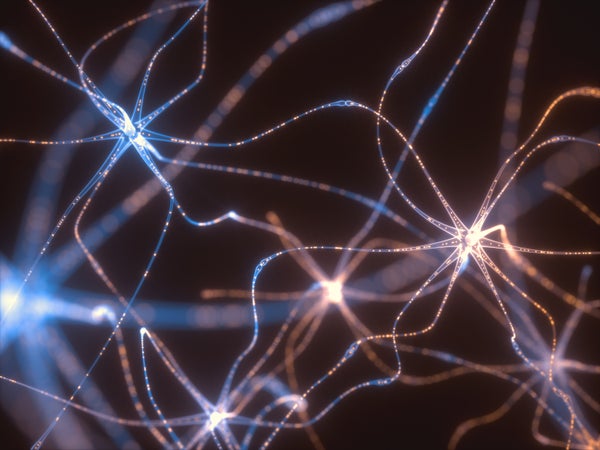我們稱之為腦電波的電振盪已經吸引了科學家和公眾一個多世紀。但它們的功能——甚至它們是否具有功能,而不僅僅是像引擎的嗡嗡聲一樣反映大腦活動——仍然存在爭議。許多神經科學家假設,如果腦電波有任何作用,那就是在不同位置同步振盪。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許多腦電波實際上是“行進波”,它們像海浪一樣在腦中物理移動。
現在,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團隊在神經科學家約書亞·雅各布斯 (Joshua Jacobs)的領導下進行的一項新研究表明,行進波在人類大腦皮層(高階認知功能的所在地)中廣泛存在,並且它們的組織性會隨著大腦執行任務的良好程度而提高。這表明這些波與行為相關,並支援了之前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它們是一種重要但被忽視的大腦機制,有助於記憶、感知、注意力和甚至意識。
腦電波最初是使用腦電圖 (EEG) 技術發現的,該技術涉及將電極放置在頭皮上。研究人員已經注意到不同頻率範圍內的活動,從δ波(0.5 到 4 赫茲)到γ波(25 到 140 赫茲)。最慢的波發生在深度睡眠期間,頻率增加與意識和注意力的提高有關。解釋腦電圖資料很困難,因為它們精確定位活動位置的能力較差,而且穿過頭部會使訊號模糊。這項新的研究於 6 月發表在Neuron期刊上,使用了更新的技術,稱為皮層腦電圖 (ECoG)。這涉及將電極陣列直接放置在大腦表面,最大限度地減少失真並大大提高空間解析度。
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科學家們已經提出了腦電波的許多可能作用。一個主要的假設認為,同步振盪用於將不同位置的資訊“繫結”在一起,使其與同一個“事物”相關,例如視覺物件的不同特徵(形狀、顏色、運動等)。一個相關的想法是它們促進了區域之間的資訊傳遞。但是,這些假設要求腦電波是同步的,產生“駐波”(類似於兩個人上下襬動跳繩),而不是行進波(如人群在體育賽事中做“人浪”)。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行進波具有不同的特性,例如,可以表示有關其他大腦位置過去狀態的資訊。它們像聲音在空氣中一樣在腦中物理傳播的事實使它們成為將資訊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的潛在機制。
這些想法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但大多數神經科學家對此關注甚少。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直到最近,大多數先前關於行進波的報告(儘管也有例外)僅僅描述了這些波,而沒有確定它們的意義。“如果你問普通的系統神經科學家,他們會說這是一種副現象[就像引擎的嗡嗡聲],”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的計算神經科學家特里·塞諾夫斯基 (Terry Sejnowski)說,他沒有參與這項新研究。“而且由於它從未直接與任何行為或功能聯絡起來,因此它並不重要。”
研究人員使用的工具也可能發揮了作用。當今主流神經科學的根基在於使用針狀微電極一次研究一個神經元的行為。該領域的先驅研究人員注意到,神經元放電的時間從一個實驗試驗到另一個實驗試驗有所不同。他們得出結論,這種時間安排一定不重要,並開始結合來自多個試驗的反應,以產生平均“放電率”。這成為量化神經活動的標準方法,但變異性可能來自神經元在振盪週期中的位置,因此這種做法忽略了揭示行進波所需的時間資訊。“概念框架是從單個神經元自身在做什麼中發展出來的,”塞諾夫斯基說,但“大腦是透過相互作用的神經元群體來工作的。”由於行進波包含分佈在大腦中的許多神經元的活動,因此單神經元技術看不到它們。但在過去十年中,出現了允許同時監測多個神經元的新技術。“這給了我們非常不同的景象,”塞諾夫斯基說。“我們第一次擁有了工具和技術來了解真正發生的事情——但這將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才能被已建立的神經科學界接受。”
光學方法,如電壓敏感染料,允許研究人員同時視覺化數千個神經元的電變化,但由於它們帶來的風險,無法在人類身上使用。然而,ECoG 通常用於癲癇患者以研究癲癇發作。因此,這項新研究背後的研究人員招募了 77 名植入了 ECoG 陣列的癲癇患者,並開始尋找行進波。他們首先尋找顯示相同頻率振盪的電極簇。近三分之二的電極是這些簇的一部分,這些簇存在於 96% 的患者中(頻率從 2-15 赫茲,跨越 4-8 赫茲的 θ 波段和 8-12 赫茲的 α 波段)。研究人員接下來透過分析振盪的時間來評估哪些簇代表真正的行進波。如果連續振盪是行進波的一部分,則每個振盪將略微延遲或提前,具體取決於行進方向。(想想人群中的人浪如何以輕微的延遲彼此跟隨。)檢測到的簇中有三分之二是行進波,從皮層的後部移動到前部。這些涉及近一半的電極,並且發生在患者大腦的所有葉和兩個半球中。
該團隊接下來給參與者佈置了一項工作記憶任務,並發現人們在被提示回憶資訊後半秒,其額葉和顳葉中的行進波變得更有組織性。這些波從朝各個方向移動變為主要協同移動。重要的是,它們這樣做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參與者的反應速度。“更一致的波對應於更好的任務表現,”雅各布斯說。“這提出了一種測量大腦活動以理解認知的新方法,這或許可以產生新的、改進的腦機介面。”(BCI 是將人腦連線到執行某些任務的機器的裝置,例如移動假肢。)
這些發現應有助於消除一些研究人員對這種波的重要性的揮之不去的疑慮。“這篇文章是對皮層行進波研究的有力貢獻,補充了先前關於它們在人類認知中的作用的工作,”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心理學家大衛·亞歷山大 (David Alexander)說,他沒有參與這項工作。“這真的會讓人們不再擔心這些波是訊號穿過顱骨模糊的偽影。”他還說,作者對這些發現的新穎性提出了不合理的說法,並且未能承認之前的一些研究。 “先前關於行進波的工作表明,它們是在工作記憶任務期間誘發的,”他說,並指出 2002 年的一項腦電圖研究發現 θ 波方向反轉的時間與記憶表現相關。有趣的是,亞歷山大本人於 2009 年發表的一項腦電圖研究發現,與健康個體相比,經歷過首次精神分裂症發作的人在工作記憶任務期間,從頭部前部到後部移動的波較少,這表明行進波行為的差異可能與精神症狀有關。他還聲稱,該團隊用於評估行進波的方法與他在 2016 年的一項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相似。“亞歷山大的工作真的很有趣,但不清楚他的發現是否與我們論文中的訊號相同,”雅各布斯指出。“他報告的模式實際上涉及整個大腦,而我們的發現僅限於特定區域。”雅各布斯還指出了記錄技術和記錄訊號性質的差異。
確認行進波的重要性為神經科學創造了新的視野。“發現如此廣泛的振盪是行進波表明它們涉及跨不同大腦區域的協調活動,”雅各布斯說。“這開闢了新的關鍵研究領域,例如理解這種協調到底由什麼組成。”他認為,至少在當前研究的背景下,這些波會傳播資訊。
另一個觀點認為,波透過在皮層區域反覆移動,調節神經元的敏感性,從而在例如大腦的視覺處理區域掃過“注意力的探照燈”。“行進波的概念與你如何將皮層維持在最佳狀態密切相關,在這種狀態下,它對其他輸入最敏感並且能夠最佳地發揮作用,”塞諾夫斯基說。對行進波的興趣無疑將繼續增加。“你現在看到的是從一個概念框架到一個全新框架的轉變,”他補充道。“這是一次正規化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