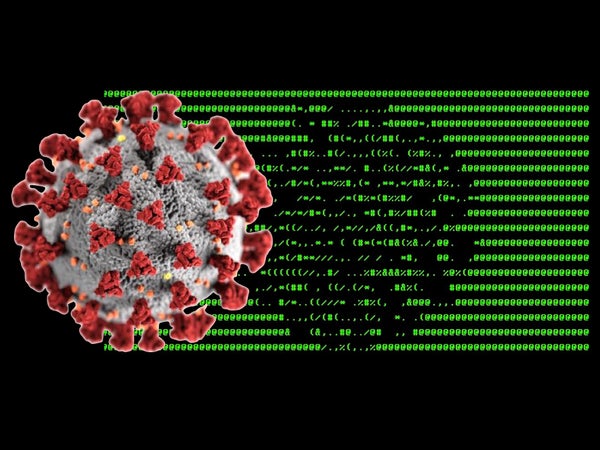正在進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似乎並不是思考生物超越性的明顯提示。但奇怪的是,在我們應對這場危機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在不知不覺地參與這樣一件事情。
超越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有各種各樣的名稱和偽裝。在許多宗教中,它抓住了神祇或現象以某種方式獨立於物理宇宙甚至超越物理定律而存在的概念。像伊曼努爾·康德這樣的哲學家修改了這個概念的某些方面,併為那些字面上不可知且存在於知識本身之外的事物建立了一個標籤。
但在最近,超越性已與人類超越我們預設的意識形式的概念聯絡起來;經常與“提升”到某種更高形式存在的神秘觀念混淆——這種比喻已被大量不那麼努力的科幻故事、電影 和 未來學家 熱情地採用。這些推測中稍微更實際的版本大多認為人類和機器融合成某種新的事物。也許我們的意識和記憶——我們的“自我”——可以上傳到不朽的數字形式,在網際網路上或在某種全能的超級計算機中盤旋。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這些幻想非常誘人(而且它們現在確實是幻想;我們不瞭解意識或記憶和行為的完整物理基礎,因此將“你”對映到機器中的可能性似乎非常渺茫)。它們也極大地分散了我們對當下正在發生的、在我們眼皮底下的此類轉變的令人驚訝且非常真實的例子的注意力。
以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為例。它的遺傳物質是一條單鏈 RNA,包含 29,903 個核苷酸(所有已知地球生命的通用遺傳密碼的“字母”),其中包含約 30 個用於製造蛋白質的基因的資訊。(用生物學家彼得和珍·梅達沃的名言來說,病毒“僅僅是被蛋白質包裹的壞訊息”。)
無論這種特定型別冠狀病毒的確切起源是什麼,直到 2020 年初,該 RNA 鏈的資訊內容從未以生化聚合核苷酸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存在於世界上。每個 SARS-Cov-2 副本都只是一堆分子而已。但是,幾乎一夜之間,它就跳到了一個全新的基質上。
從 PCR 測序系統和 奈米孔裝置 等技術(字面上是將 DNA 或 RNA 鏈拉過分子感測器,該感測器記錄不同核苷酸的不同電荷)的內部結構開始,病毒 RNA 被轉換為數字資料;符號表示本身被編碼為矽儲存器或硬碟中的微小電或磁位元。從這裡開始,病毒 RNA 的資訊內容被複制:跨儲存裝置、透過網際網路、進入雲伺服器、到人們的筆記型電腦、手機、快閃記憶體驅動器,並在某種程度上進入他們的大腦,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仔細研究基因序列及其相關的分子機制。
然而,這種病毒超越性不僅僅停留在符號資訊的複製上。現在,相同的資訊以病毒 RNA 鎖定時無法做到的方式與世界互動。現在它影響著人類的活動和行為。我們執行計算機程式碼,我們撰寫科學文章,我們在實驗室中人工構建 RNA 片段,並且在我們的 mRNA 疫苗的情況下,我們生成數萬億甚至數千萬億個原始 RNA 小片段的副本,即刺突蛋白編碼的十四行詩,並將它們運送到世界各地,在那裡它們進入人體組織和細胞以及核糖體機制。
這種病毒的資訊內容以所有這些形式(電子的和人工的)傳播到地球各地,其程度甚至可以與原始生物形式本身的可怕效率相媲美。它現在也以原始形式永遠無法做到的方式對其所包含的環境施加了影響。每次測序研究和每次檔案下載或蛋白質結構預測都伴隨著電流的流動。實驗室裝置和疫苗生產設施已被製造或擴建,並且隨著基因組資訊被爭論和研究,人類也匆匆忙忙地來回奔波。
從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講,冠狀病毒已將自身上傳到機器形式,甚至更遠。即使我們要從世界上根除其生物形式,它也會作為數字物種繼續存在,也許在很大程度上處於休眠狀態,但從自我繁殖資訊的角度來看,時間在某種程度上是無關緊要的。如果病毒的數字化版本在一個世紀或兩個世紀內未被檢查,那也沒關係,它仍然繼續存在,因為它能夠存在,從而贏得了達爾文進化博弈。
就像我們自己的“自私基因”一樣,由核苷酸構建的病毒基因實際上只是一種方便的實現或例項化,它描述了自身傳播過程的一種資訊型別(儘管是以壓縮形式)。但是,正是像我們這樣的物種的進化發展,以及我們隨後的技術進化,才創造了病毒超越到完全非生物形式的機會。其中可能蘊含著一個教訓:我們可能希望認為我們可以在某一天實現我們自己的某種超越版本,但也許會是其他事物創造了這個機會,並且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它,無論我們是否希望它發生。我們可能不會將自己上傳到機器形式;機器可能會上傳我們,就像我們對病毒所做的那樣。
在我的新書《資訊的提升》(Riverhead,2021 年 6 月)中,更詳細地探討了資訊在世界中傳播的方式。
這是一篇觀點和分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