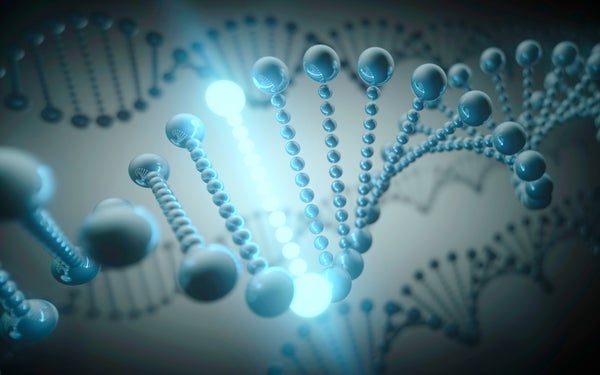芝加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希望您提供六管血樣。
他們的科學家還希望採集您的尿液樣本,測量您的腰圍,並訪問您的電子健康記錄和您手腕上可穿戴感測器的資料。如果您不介意分享,他們能得到您的社會安全號碼嗎?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要求,而且是針對一個同樣龐大的群體——該機構最終希望在 2003 年一篇論文中四位研究人員所稱的“生物研究革命”的下一步中招募超過 100 萬名參與者。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工作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有助於確保關於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然而,這些呼籲與在精準醫學上的有史以來最大賭注相符,現在這項研究已經進行了十多年。該論文的主要作者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從專案啟動之初就致力於此,他將其對更精確的醫療世界的美好願景帶到了他目前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職位。
柯林斯和其他人表示,這項名為“我們所有人”的資料收集實驗是使個性化醫療在世界各地成為現實的重要一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希望這些資訊有一天能使醫生能夠使用越來越精確的診斷測試。最終,科學家們可以根據個人的基因特徵來制定治療方案。
但是,柯林斯提出的目標之一是確保超過一半的參與者來自歷史上在生物醫學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社群——這是一個賭注。
“人們害怕被當做實驗物件,”伊利諾伊大學癌症中心主任兼該專案的主要研究者羅伯特·溫博士說。
研究人員知道,要找到成千上萬沒有理由讓政府對其 DNA 進行測序,但可能願意為了他們的孩子更健康的未來而冒險的人,這並不容易。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在招聘、超過 2.3 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和營銷方面都將該專案的外展部門放在首位。
他們還買了一輛卡車。
上週的大部分時間裡,這輛卡車都停在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醫學園區的附近人行道上。
它的工作人員——僱傭的營銷人員,他們開著卡車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已經在路上花了六個星期,以整天嘗試吸引路人的形式進行休息。裡面是一個移動展覽,塑膠白牆上安裝了高畫質螢幕,多語言展示上裝飾著諸如“我想活著看到我的孫子長大”之類的短語。
參觀者觀看解釋精準醫學的影片,由“我們所有人”的“社群合作伙伴”和工作人員解答問題,如果他們同意參與,則使用觸控式螢幕填寫同意書。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認為,這種社群外展對於招募超出典型研究樣本(不成比例的白人、受過教育的、富裕的和男性)的參與者至關重要。研究人員表示,如果結果不會擴大從研究中受益的社群數量,那麼組織一項前所未有的精準醫學計劃就毫無意義。
到目前為止,結果令人鼓舞。埃裡克·迪什曼,一位前英特爾高管,柯林斯聘請他擔任“我們所有人”專案主管,上週宣佈該專案在其測試階段已招募了超過 2,500 名參與者——其中一些直接來自“移動參與單元”的互動。
但是社群組織者和其他一些人擔心這種外展活動還不夠。
“進進出出正是建立不信任的原因,”溫說。“或者認為對社群的興趣與撥款期限有關。”
這就是為什麼接受聯邦資金為低收入人群服務的衛生中心成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外展戰略的核心。溫工作的芝加哥邁爾廣場健康中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群資源——居民知道它下週和十年後都會在那裡。
全國各聯邦合格醫療中心中,超過三分之二的患者的年收入低於貧困線。溫說,他看到一些年輕人聽說了縱向研究——“我們將在未來 10 年內進行跟蹤”——並且告訴他,考慮到他們社群的槍支暴力,他們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活那麼久。
但至少他們在和溫交談,溫是當地社群的固定人物,而不是研究人員、營銷人員或其他未知實體。對於他來說,他們可能會放下不信任,並表示他們願意加入該計劃。在全國其他 FQHC 合作站點也是如此。
但這種對話通常只是容易的部分。困難的部分是安排未來的預約和管理後勤。在大多數合作站點和移動參與單元的大多數展覽站點,參與者無法簡單地填寫檔案並走到街對面的房間抽取血液。
相反,大多數參與者需要單獨預約,以便提供商處理他們的生物樣本並進行身體測量。這還不包括那些尤其對於英語不太好和計算機技能不高的人來說,可能需要長達一個小時的檔案工作。
“你如何接觸那些不識電腦,並且在許多情況下無法上網的人群?”田納西州切羅基健康系統(另一個 FQHC 合作伙伴)的內科醫生菲比·華萊士博士問道。
“我們服務於阿巴拉契亞農村地區。前幾天我參加了一個小組——我照顧一些病情更嚴重的糖尿病患者——我問房間裡的人:你們有多少人可以上網?在 14 個人中,沒有一個人。”
迪什曼說,醫療保健提供商正在開發不同的處理流程。他補充說,無論他們選擇哪條路線,都必須“確保參與者明白‘我們所有人’的訪問是用於研究,並且與醫療保健完全分開。”
如果不提及海瑞塔·拉克斯,就幾乎不可能談論少數族裔社群和生物醫學研究。她 1951 年在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進行的活檢產生了癌症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細胞系之一。她在那年晚些時候去世,從未得知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這些細胞是在她不知情或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獲得的。
這也是為什麼溫和“我們所有人”專案的首席參與官達拉·理查森-海倫博士與拉克斯的三位後代組成了一個小組,在六月份在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校園裡對擠滿的劇院發表演講。拉克斯的家人同意支援該專案,因為他們相信這次的情況不同——而且這次,每個社群都應該獲得一席之地。
“我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了第一個研究和醫學家族,”拉克斯的曾孫女維羅妮卡·羅賓遜在活動結束後告訴記者。“我的家人現在正在參與這一遺產,我們正在努力彌合社群、科學和醫學之間的差距。”
理查森-海倫承認,這種宣傳可能看起來有悖常理。她和拉克斯家族基本上是在解釋,要對抗生物醫學研究人員數十年的忽視或公然虐待,方法是全力投入他們迄今為止最雄心勃勃的專案。
正如她所說,這個想法是“或許甚至完全消除我們在社群中每天看到的健康差距。”
非裔美國人和生物醫學研究人員之間不信任的例子早於海瑞塔·拉克斯,包括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美國公共衛生部門招募黑人男性進行一項觀察未經治療的梅毒進展的研究,但以免費醫療保健為幌子。
在最近一項由 Research!America 委託進行的研究中,接受調查的 50% 的非裔美國人將“缺乏信任”列為參與臨床試驗的障礙,低於 2013 年的 61%,這兩項資料在所有人口統計資料中均為最高,並且大大高於白人之間的不信任程度。
但是,許多少數族裔社群對臨床研究的想法感到不安——這是溫和他在全國各地的同行們都承認並試圖應對的現實。
例如,在拉丁裔社群的許多招募工作中,必須考慮到當前的政治氣候。介紹“我們是聯邦政府的,我們希望對你的基因組進行測序,我們需要你的社會安全號碼”並不一定受歡迎。
“這始終是一個挑戰,而 [2016 年的選舉] 並沒有幫助,”國家西班牙裔健康聯盟高階副總裁,該專案最早的社群合作伙伴之一阿道夫·法爾孔說。“這項研究及其設計和立法授權始終表示,所提供的任何資訊都不能用於任何其他目的。我們已經與該專案合作,以找到強調這一點的更多方法。”
社會安全號碼也是可選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更希望參與者提交該號碼,以便他們能夠確保電子健康記錄正確匹配參與者,但可以沒有。
也許在大多數社群中,最困難的道德對話甚至還沒有開始。它們將在一年後開始——屆時“我們所有人”將開始招募兒童。
像“我們所有人”這樣規模的專案在其他地方基本上沒有經過測試,除了少數幾個專案,包括卡達的一個規模小得多的精準醫療專案和英國的“十萬基因組計劃”。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正在執行“百萬退伍軍人計劃”——這是一項影響深遠的研究,但僅限於退伍軍人。
因此,局外觀察者很難判斷“我們所有人”專案目前是否成功。該專案取消了在2016年向參與者傳送調查問卷的計劃,但迪什曼表示,這僅僅是因為他和其他人決定調整招募時間表。
迪什曼說:“我仍然有人告訴我,‘嘿,埃裡克,你晚了’,但實際上,我們很早就開始了。”他指出,該專案比預期提前收集生物醫學樣本。“人們只是不明白,我們去年必須啟動的任何專案在範圍上都將非常小。”
迪什曼說,迄今為止,測試樣本比典型的生物醫學研究更加多樣化,但他以專案目前範圍有限且處於早期階段為由,拒絕分享人口統計資料。
儘管如此,該專案正在快速發展。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現在在全國各地的醫療中心和醫療服務提供機構都有附屬機構,這些機構正在分階段進行測試階段的招募工作。
研究人員還在聖地亞哥啟動了一項“直接志願者招募”的試驗,即在城市血站排隊等候的人也被詢問是否願意參加該研究。
在該模式下,研究人員假設潛在參與者至少對精準醫療和基因組測序有一定的瞭解,並允許那些想要註冊的人直接走過去登記。
然而,在大多數地點,招募仍然是一件不確定的事情。萬達·蒙塔爾沃是康涅狄格州米德爾敦社群健康中心的護士,她正在那裡協助“我們所有人”的研究,並決定親自參與該研究。但即使作為研究合作伙伴,她在點選允許訪問她的電子健康記錄的按鈕之前仍然猶豫了。
蒙塔爾沃說:“我認為這是因為在那一刻,你會意識到你正在授權一些你技術上不習慣提供和分享的東西。”
但隨後她想到了她的家族史。
蒙塔爾沃說:“我的曾祖母活到105歲,我的祖母活到103歲,我們沒有患痴呆症,而且我的家人沒有真正的癌症病史。”
她希望“我們所有人”專案能找到有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