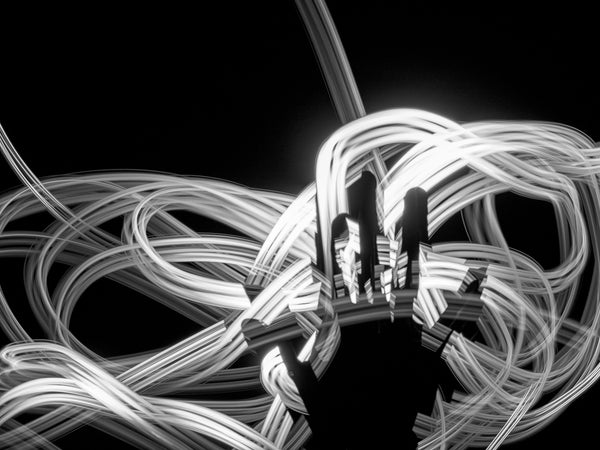同時處於活著和死亡狀態是什麼感覺?
這個問題在 20 世紀 60 年代困擾並啟發了匈牙利裔美國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他對量子力學(支配微觀領域的理論)的變幻莫測所引起的悖論感到沮喪。量子力學表明,在觀察量子系統之前,它不一定具有確定的屬性,這只是眾多違反直覺的事情之一。以他的物理學家同事埃爾溫·薛定諤著名的思想實驗為例,其中一隻貓被困在一個盒子裡,如果放射性原子衰變,就會釋放毒藥。放射性是一個量子過程,因此在開啟盒子之前,故事是這樣的,原子既衰變了,又沒有衰變,這使得不幸的貓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所謂的生死疊加。但貓會體驗到處於疊加態嗎?
維格納透過想象他的一位(人類)朋友被關在實驗室裡測量一個量子系統,加劇了這種悖論。他認為,除非維格納開啟實驗室的門,否則說他的朋友處於既看到衰變又沒有看到衰變的疊加態是荒謬的。“‘維格納的朋友’思想實驗表明,如果觀察者也被觀察,事情可能會變得非常奇怪,”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諾拉·蒂施勒說。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現在,蒂施勒和她的同事們進行了一個版本的維格納的朋友測試。透過將經典思想實驗與另一個稱為量子糾纏的量子難題(一種將粒子跨越遙遠距離連線起來的現象)相結合,他們還推匯出了一個新的定理,他們聲稱該定理對現實的根本性質施加了迄今為止最強的約束。他們的研究於 8 月 17 日發表在《自然物理學》雜誌上,對意識可能在量子物理學中發揮的作用,甚至量子理論是否必須被取代都具有影響。
多倫多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埃夫拉姆·斯坦伯格說,這項新工作是“實驗形而上學領域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他沒有參與這項研究。“這是一個巨大的研究計劃的開始,我對此充滿期待。”
品味問題
在 20 世紀 20 年代量子物理學出現之前,物理學家期望他們的理論是確定性的,能夠確定地預測實驗結果。但量子理論似乎本質上是機率性的。教科書版本——有時稱為哥本哈根解釋——認為,在測量系統的屬性之前,它們可以包含無數的值。只有當系統被觀察時,這種疊加才會坍縮成單一狀態,物理學家永遠無法精確預測該狀態會是什麼。維格納當時流行的觀點是,意識以某種方式觸發了疊加的坍縮。因此,他假設的朋友在進行測量時會辨別出一個確定的結果——而維格納永遠不會看到她或他處於疊加態。
這種觀點後來失寵。“量子力學基礎領域的人們迅速駁斥了維格納的觀點,認為它既怪異又不明確,因為它使觀察者變得特殊,”紐約大學的哲學家和認知科學家大衛·查爾默斯說。如今,大多數物理學家都同意,無生命的物體可以透過稱為退相干的過程將量子系統從疊加態中擊出。當然,試圖在實驗室中操縱複雜量子疊加的研究人員可能會發現他們的辛勤工作被快速移動的空氣粒子與他們的系統碰撞而破壞。因此,他們在超低溫下進行測試,並嘗試將他們的裝置與振動隔離。
幾十年來,出現了幾種相互競爭的量子解釋,它們採用了不太神秘的機制,例如退相干,來解釋疊加如何分解而無需呼叫意識。其他解釋則持有更激進的立場,即根本沒有坍縮。每種解釋都對維格納的測試有其自身奇怪而奇妙的看法。最奇異的是“多世界”觀點,它認為,每當您進行量子測量時,現實就會分裂,創造出平行宇宙來容納每種可能的結果。因此,維格納的朋友會分裂成兩個副本,並且“憑藉足夠好的超級技術”,他確實可以從實驗室外測量到這個人處於疊加態,特拉維夫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和多世界愛好者萊夫·維德曼說。
另一種“玻姆”理論(以物理學家大衛·玻姆命名)認為,在基本層面上,量子系統確實具有確定的屬性;我們只是對這些系統瞭解得不夠,無法精確預測它們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朋友有一個單一的體驗,但維格納仍然可能因為他自己的無知而測量到該個體處於疊加態。相比之下,一個名為 QBism 解釋的新來者全心全意地接受量子理論的機率元素(QBism,發音為“cubism”,實際上是量子貝葉斯主義的縮寫,指的是 18 世紀數學家托馬斯·貝葉斯關於機率的工作。)QBists 認為,一個人只能使用量子力學來計算如何校準他對在實驗中將要測量的東西的信念。“測量結果必須被視為對進行測量的代理人是私人的,”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魯迪格·沙克說,他是 QBism 的創始人之一。根據 QBism 的原則,量子理論不能告訴您任何關於現實的潛在狀態的資訊,維格納也不能使用它來推測他朋友的經歷。
另一種有趣的解釋,稱為逆因果關係,允許未來的事件影響過去。“在逆因果關係的解釋中,維格納的朋友絕對會體驗到某些東西,”聖何塞州立大學的物理學家肯·沃頓說,他是這種時間扭曲觀點的倡導者。但朋友在測量點體驗到的“某些東西”可能取決於維格納稍後如何觀察此人的選擇。
問題在於,每種解釋在預測量子測試的結果方面都同樣好——或壞——因此,在它們之間進行選擇取決於品味。“沒有人知道解決方案是什麼,”斯坦伯格說。“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擁有的潛在解決方案列表是否詳盡。”
其他模型,稱為坍縮理論,確實做出了可測試的預測。這些模型附加了一種機制,當量子系統變得太大時,會強制其坍縮——解釋了為什麼貓、人和其他宏觀物體不能處於疊加態。正在進行實驗以尋找此類坍縮的跡象,但到目前為止,他們尚未發現任何東西。量子物理學家也在將越來越大的物體置於疊加態:去年,維也納的一個團隊報告說,他們用一個 2,000 個原子的分子做到了這一點。大多數量子解釋都認為,只要研究人員能夠在原始的實驗室條件下設計出正確的實驗,以便避免退相干,那麼這些擴大疊加態的努力就沒有理由不永遠向上繼續。然而,坍縮理論假設,無論實驗準備得多麼仔細,有一天都會達到極限。“如果你嘗試操縱一個經典的觀察者——例如人——並將其視為量子系統,它會立即坍縮,”義大利的裡雅斯特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和坍縮理論的支持者安傑洛·巴斯說。
觀察維格納朋友的方法
蒂施勒和她的同事們認為,分析和執行維格納的朋友實驗可以闡明量子理論的侷限性。他們受到新一波理論和實驗論文的啟發,這些論文透過將糾纏引入維格納的經典設定來研究觀察者在量子理論中的作用。假設您取兩個光粒子,或光子,它們被極化,因此它們可以水平或垂直振動。光子也可以置於同時水平和垂直振動的疊加態,就像薛定諤的悖論貓在被觀察之前可以同時處於活著和死亡狀態一樣。
這種光子對可以一起製備——糾纏——因此當觀察到它們時,它們的極化總是被發現處於相反的方向。這似乎並不奇怪——除非您記住這些屬性在被測量之前是固定的。即使一個光子被給予了澳大利亞的物理學家艾麗斯,而另一個光子被運送到她在維也納實驗室的同事鮑勃,糾纏也確保一旦艾麗斯觀察到她的光子,例如,發現它的極化是水平的,鮑勃的光子的極化立即同步到垂直振動。由於這兩個光子似乎以比光速更快的速度進行通訊——這違反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種現象深深地困擾著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稱之為“幽靈般的超距作用”。
這些擔憂仍然是理論性的,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物理學家約翰·貝爾設計了一種方法來測試現實是否真的具有幽靈般的性質——或者糾纏夥伴之間的相關性背後是否可能存在更平凡的解釋。貝爾設想了一種常識理論,該理論是局域的——也就是說,影響不能在粒子之間瞬間傳播。它也是確定性的而不是本質上是機率性的,因此原則上可以確定地預測實驗結果,前提是物理學家對系統的隱藏屬性有更多的瞭解。它是現實的,對於量子理論家來說,這意味著即使沒有人觀察系統,系統也會具有這些確定的屬性。然後,貝爾計算了這種局域、確定性和現實理論可以支援的一系列糾纏粒子之間的最大相關性水平。如果在實驗中違反了該閾值,則該理論背後的一個假設必定是錯誤的。
自那時以來,已經進行了這種“貝爾測試”,並在 2015 年進行了一系列嚴謹的版本,它們證實了現實的幽靈般的性質。“量子基礎是貝爾[定理]真正開始實驗的領域——現在已經超過 50 年了。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重新實施這些實驗,並討論它們的含義,”斯坦伯格說。“人們能夠提出超越貝爾的新測試是非常罕見的。”
布里斯班團隊的目標是推匯出並測試一個新的定理,該定理將做到這一點,對現實的性質提供更嚴格的約束——“局域友善性”界限。與貝爾的理論一樣,研究人員的假想理論也是局域的。他們還明確禁止“超決定論”——也就是說,他們堅持認為實驗者可以自由選擇測量什麼,而不會受到未來或遙遠過去事件的影響。(貝爾也隱含地假設實驗者可以做出自由選擇。)最後,該團隊規定,當觀察者進行測量時,結果是世界上的一個真實的、單一的事件——它不相對於任何人或任何事物。
測試局域友善性需要一個巧妙的設定,包括兩個“超級觀察者”艾麗斯和鮑勃(他們扮演維格納的角色),觀察他們的朋友查理和黛比。艾麗斯和鮑勃各自都有自己的干涉儀——一種用於操縱光子束的裝置。在被測量之前,光子的極化處於水平和垂直疊加的狀態。製備成對的糾纏光子,這樣如果測量到一個光子的極化是水平的,那麼它的夥伴的極化應該立即翻轉為垂直的。來自每對糾纏光子的一個光子被髮送到艾麗斯的干涉儀中,它的夥伴被髮送到鮑勃的干涉儀中。查理和黛比實際上並不是這個測試中的人類朋友。相反,它們是每個干涉儀前端的光束位移器。當艾麗斯的光子擊中位移器時,它的極化實際上被測量了,並且它根據它突然進入的極化方向向左或向右偏轉。這個動作扮演了艾麗斯的朋友查理“測量”極化的角色。(黛比也同樣位於鮑勃的干涉儀中。)
然後艾麗斯必須做出選擇:她可以立即測量光子新的偏離路徑,這相當於開啟實驗室的門並詢問查理他看到了什麼。或者她可以讓光子繼續它的旅程,穿過第二個光束位移器,該位移器重新組合左右路徑——相當於保持實驗室的門關閉。然後艾麗斯可以直接測量她的光子離開干涉儀時的極化。在整個實驗過程中,艾麗斯和鮑勃獨立選擇做出哪些測量選擇,然後比較筆記以計算在一系列糾纏對中看到的相關性。
蒂施勒和她的同事們進行了 90,000 次實驗。正如預期的那樣,相關性違反了貝爾的原始界限——並且至關重要的是,它們也違反了新的局域友善性閾值。該團隊還可以修改設定,透過在光子對中的一個光子進入其干涉儀之前使其繞道而行,輕輕地擾亂夥伴之間完美的和諧,從而降低光子之間糾纏的程度。當研究人員在糾纏程度略低的情況下執行實驗時,他們發現一個點,在該點相關性仍然違反了貝爾的界限,但沒有違反局域友善性。蒂施勒說,這個結果證明了兩組界限不是等價的,並且新的局域友善性約束更強。“如果你違反了它們,你就會更多地瞭解現實,”她補充道。也就是說,如果你的理論說“朋友”可以被視為量子系統,那麼你必須要麼放棄局域性,要麼接受測量沒有觀察者必須同意的單一結果,要麼允許超決定論。這些選項中的每一個都具有深刻的——並且對於某些物理學家來說,非常令人厭惡的——含義。
重新審視現實
“這篇論文是一項重要的哲學研究,”紐約市量子計算公司 Turing 的聯合創始人米歇爾·賴利說,他沒有參與這項工作。她指出,研究量子基礎的物理學家經常努力提出可行的測試來支援他們的大想法。“我很高興看到哲學研究背後的實驗,”賴利說。斯坦伯格稱該實驗“非常優雅”,並讚揚該團隊正面解決了觀察者在測量中的作用之謎。
儘管量子力學迫使我們放棄一個常識性假設並不令人意外——物理學家從貝爾那裡就知道了這一點——但“這裡的進步在於我們正在縮小範圍,確定是哪些假設,”沃頓說,他也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不過,他指出,大多數量子解釋的支持者不會因此失眠。逆因果關係的支持者,例如他自己,已經與超決定論達成了和解:在他們看來,未來測量影響過去結果並不令人震驚。與此同時,QBists 和多世界擁護者很久以前就拋棄了量子力學規定每個觀察者都必須同意的單一結果的要求。
玻姆力學和自發坍縮模型都已經在響應貝爾時愉快地放棄了局域性。此外,坍縮模型認為,真正的宏觀朋友首先不能作為量子系統來操縱。
維德曼也沒有參與這項新工作,但他對此不太熱情,並批評將維格納的朋友等同於光子。論文中使用的方法“荒謬;朋友必須是宏觀的,”他說。紐約大學的物理學哲學家蒂姆·莫德林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他也同意。“沒有人認為光子是觀察者,除非你是泛靈論者,”他說。由於沒有物理學家質疑光子是否可以置於疊加態,莫德林認為該實驗缺乏力度。“它排除了一些東西——只是排除了一些沒有人提出過的東西,”他說。
蒂施勒接受了批評。“我們不想過分誇大我們所做的事情,”她說。格里菲斯大學的物理學家、團隊成員霍華德·懷斯曼補充說,未來實驗的關鍵將是擴大“朋友”的規模。他說,最引人注目的結果將涉及使用人工智慧,體現在量子計算機上,作為朋友。懷斯曼指出,一些哲學家推測,這種機器可能具有類似人類的體驗,這種立場被稱為強人工智慧假設,儘管目前尚無人知曉這種想法是否會成真。但如果該假設成立,那麼這種基於量子的通用人工智慧 (AGI) 將是微觀的。因此,從自發坍縮模型的角度來看,它不會因其大小而觸發坍縮。如果進行這樣的測試,並且沒有違反局域友善性界限,那麼該結果將暗示 AGI 的意識不能置於疊加態。反過來,這個結論將表明維格納關於意識導致坍縮的觀點是正確的。“我不認為我會活著看到這樣的實驗,”懷斯曼說。“但這將是革命性的。”
然而,賴利警告說,希望未來 AGI 能夠幫助他們找到現實的基本描述的物理學家是本末倒置。“對我來說,量子計算機很可能會成為通往 AGI 的正規化轉變,”她說。“最終,我們需要一個萬物理論才能在量子計算機上構建 AGI,句號,到此為止。”
這個要求可能會排除更宏大的計劃。但該團隊還提出了更適度的中間測試,涉及機器學習系統作為朋友,這吸引了斯坦伯格。他說,這種方法“有趣且具有啟發性”。“越來越有可能以量子方式測量更大規模的計算裝置。”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ETH Zurich) 的量子物理學家雷納託·倫納提出了更強烈的說法:他說,無論未來是否可以進行實驗,新定理都告訴我們,量子力學需要被取代。2018 年,倫納和他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同事丹妮拉·弗勞奇格發表了一個基於維格納的朋友的思想實驗,並用它來推匯出一個新的悖論。他們的設定與布里斯班團隊的設定不同,但也涉及四個觀察者,他們的測量結果可能會糾纏在一起。倫納和弗勞奇格計算出,如果觀察者彼此應用量子定律,他們最終可能會在同一個實驗中推斷出不同的結果。
“這篇新論文再次證實,我們當前的量子理論存在問題,”倫納說,他沒有參與這項工作。他認為,今天的量子解釋都無法擺脫所謂的弗勞奇格-倫納悖論,除非支持者承認他們不在乎量子理論是否給出一致的結果。倫納說,QBists 提供了最令人滿意的逃脫手段,因為從一開始,他們就說量子理論不能用於推斷其他觀察者將測量什麼。“但這仍然讓我擔心:如果一切都只是我個人的,那我怎麼能對你說任何相關的事情呢?”他補充道。倫納現在正在研究一種新的理論,該理論提供了一組數學規則,允許一個觀察者計算出另一個觀察者應該在量子實驗中看到什麼。
儘管如此,那些堅信自己最喜歡的解釋是正確的人認為蒂施勒的研究沒有什麼價值。“如果你認為量子力學是不健康的,並且需要被取代,那麼這是有用的,因為它告訴你新的約束,”維德曼說。“但我不同意這是事實——多世界解釋了一切。”
目前,物理學家將不得不繼續同意對哪種解釋最好或是否需要全新的理論持有不同意見。“這就是我們在 20 世紀初結束的地方——我們真的對此感到困惑,”賴利說。“但這些研究正是思考這個問題應該做的正確事情。”
免責宣告:作者經常為基礎問題研究所撰稿,該研究所贊助物理學和宇宙學研究,併為布里斯班團隊的研究提供部分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