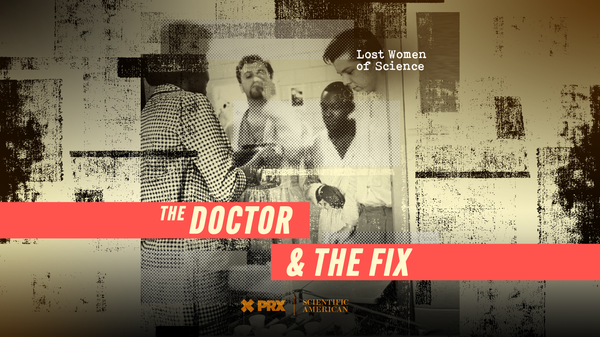在多年令人失望的海洛因成癮治療結果之後,瑪麗·尼斯萬德非常渴望嘗試新的方法。當她在著名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現為洛克菲勒大學)遇到一位傑出的醫生時,兩人開始了一項實驗,這項實驗將定義他們兩人的職業生涯,並徹底改變未來幾十年成癮的治療方法。但並非所有人都對此感到高興。
[不熟悉《科學失落的女性》這一季?請先收聽第一集此處,然後收聽第二集。]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發現和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劇集文字稿
《科學失落的女性》播客是為耳朵製作的。我們的目標是使我們的文字稿儘可能準確,但仍可能發生一些錯誤。此外,語音的重要方面,如語氣和強調,可能無法完全捕捉,因此我們建議儘可能收聽劇集,而不是閱讀文字稿。
——
凱蒂·哈夫納:嘿,這是我們關於瑪麗·尼斯萬德系列的第三集。我們想提醒您,其中將包含一些成人內容和一些檔案音訊,其中包括關於藥物成癮的相當過時的語言。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在 1960 年代初期,一位名叫文森特·多爾的醫生每天從紐約市北部富裕的郊區萊伊通勤到他在曼哈頓上東區的辦公室。
到目前為止,文斯的生活一直很順利。他出生於芝加哥一個富裕的家庭,就讀於斯坦福大學,然後是哈佛醫學院,現在他在著名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專門研究肥胖和新陳代謝。文森特·多爾是該領域的知名人物。
凱蒂·哈夫納:但他的工作變得不再令人滿意。他發現自己參加同樣的會議,一遍又一遍地遇到同樣的人,還有他的病人。在 1982 年,他告訴歷史學家大衛·考特賴特,他會幫助他們減肥,但然後 -
文森特·多爾:通常在您稍微放鬆常規後不久,他們就會恢復到以前的狀態。換句話說,他們就像一個恆溫器,設定在某個體重。
凱蒂·哈夫納:通常,僅僅是虛榮心才把他們帶到他的辦公室。
文森特·多爾:女士們會進來並宣佈她們想減肥或將體重轉移到不同的部位,嗯,我只是覺得我被當作美容用途。這真的不一定有醫學意義。
凱蒂·哈夫納:文斯不僅僅是被期望他幫助她們減肥的女士們激怒了。他感到厭倦了。如果不是因為他每天通勤的一個怪癖,他可能會一直待在他舒適、無聊的泡沫中。他會從威徹斯特的通勤火車在 125 街下車,然後,他會步行幾個街區穿過東哈萊姆區,到達另一輛將他帶到洛克菲勒的火車。那次步行?令人大開眼界。
文森特·多爾:我有點感覺像是在兩個高度特權的綠洲之間通勤,穿過一片真正的痛苦的海洋。
凱蒂·哈夫納:這種流行病是海洛因成癮。正如我們在上一集中討論的那樣,在 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期,東哈萊姆區受海洛因成癮的打擊尤其嚴重,而且這個問題還在日益嚴重。
如果他沒有換乘火車,他可能永遠不會對此進行過多思考——也許只是瞥一眼窗外,在他上班時就忘記了,就像成千上萬的其他通勤者一樣。但在那次步行中,文斯被迫真正看到他的城市正在發生什麼。
文森特·多爾:我開始意識到,我的科學家群體或萊伊的人們沒有人對那個世界有任何概念,即使這個地方就在紐約。我們基本上生活在流行病之中,卻對此視而不見。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現在,成癮遠遠超出了文斯的專業範圍。但是,他思考了他所知道的,即新陳代謝,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想法開始形成。對藥物的渴望是否與對食物的渴望有共同之處?許多人認為肥胖僅僅是暴飲暴食的結果,但一些研究發現,有些人即使吃得與其他人的量相同,也會體重增加,而且他們的身體在做同樣的事情時消耗的能量更少。文斯認為,他們的代謝狀態也可能導致對食物的更大渴望。
如果這裡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呢?某種與藥物成癮者的代謝有關的事情,使他們的身體以其他人的身體不會的方式渴望藥物?
現在,這是一個適當的研究難題,一個深入相對開放的科學領域的機會,一個等待有人抓住它的機會。也許那個人可以是他。也許著名的肥胖專家文森特·多爾甚至可以阻止一場流行病。他所需要的只是真正瞭解一些關於成癮的知識。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這裡是《科學失落的女性》。我是卡羅爾·薩頓·劉易斯。
凱蒂·哈夫納:我是凱蒂·哈夫納。本季,《醫生與治療:瑪麗·尼斯萬德如何改變了成癮的局面》。在今天的劇集中——一項意想不到的突破。
艾米麗·杜夫頓:多爾的級別非常高。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那是艾米麗·杜夫頓,作家和藥物歷史學家。
艾米麗·杜夫頓:我記得采訪過一個人,他說他們真的相信,如果多爾繼續研究肥胖和新陳代謝,他就會獲得諾貝爾獎。就像,這項工作受到了如此高的尊重,以至於他放棄它,然後說,嗯嗯,海洛因成癮——這就是他正在玩的賭注。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文斯正在考慮涉足一個他沒有經驗的領域。但是,儘管他對成癮非常陌生,也沒有做過任何自己的研究,但文斯有人脈。有一天,當他與其中一個人脈聊天時,一個機會落到了他的頭上。
這個人脈是劉·托馬斯。劉易斯·托馬斯是紐約市衛生局麻醉品委員會主席。在那一天,文斯告訴劉他對成癮的新興趣,並說,你知道,這個領域沒有更多好的研究真是太可惜了?正如文森特所說,那時劉基本上把王國的鑰匙交給了他。
文森特·多爾:他說,嗯,這是一件好事。他說,我正要休假去法國,我還沒有看到這個委員會取得什麼成果。你為什麼不成為它的主席呢?我說,好吧,我來做。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就是這樣。
凱蒂·哈夫納:好的。我只需要打斷一下,說,等一下,你在開玩笑嗎?也許是因為對成癮知之甚少,或者他的人脈太廣,但他竟然成為了某個麻醉品委員會的主席,對麻醉品一無所知?然而,瑪麗·尼斯萬德投入了所有的時間——我的意思是,她完全沉浸其中。她出版了一整本關於成癮的書。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更重要的是,這表明他們對成癮委員會有多麼不在意,以至於他們會任命一個對此完全沒有背景的人來負責。我的意思是,有瑪麗·尼斯萬德醫生,我相信還有其他真正關注這個問題的人,但僅僅因為他是他的朋友,就將主席職位交給這個人?
凱蒂·哈夫納:是的,好吧,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是的,他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來,就被任命為負責人,但至少文斯知道自己有很多東西要學。
艾米麗·杜夫頓:所以他開始自己閱讀關於成癮的書籍,只是給自己做了可用的文獻的調查,因為他從未上過關於成癮的課。他去了哈佛醫學院,沒有人談論過它。他在這方面沒有任何指導。洛克菲勒也沒有關於它的對話。所以他開始自學,他偶然發現了瑪麗的文章,他也偶然發現了她的書。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1956 年,在瑪麗出版《性臣服的力量》之前幾年,她出版了一本關於成癮的書,名為《吸毒者作為病人》。在這本書中,瑪麗有效地總結了她所瞭解的關於成癮的一切——藥物對身體的影響、緩解戒斷症狀的方法、美國犯罪化的歷史,以及當時關於成癮的一些理論。
但最重要的是,她認為成癮是一種疾病,而不是犯罪問題,懲罰人們或強迫他們接受治療是行不通的。文斯喜歡他讀到的內容。多年後,他告訴大衛·考特賴特,瑪麗·尼斯萬德是唯一一個讓他感到有道理的人。他在她身上看到的,不僅僅是一位可以諮詢的專家,也是一位潛在的合作者。因此,在 1962 年末或 1963 年初的某個時候,文斯給她打了個電話。他聯絡到了一位非常疲憊和沮喪的瑪麗。
瑪麗·尼斯萬德:到那時,我已經用盡了所有可用的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方式。你能說出來的,催眠、團體療法、將病人轉移到世界各地。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自從瑪麗出版關於成癮的書以來,已經過去了將近七年。在職業上,她做得很好。她仍然在公園大道擁有自己的私人診所,並在紐約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但是,所有這些年治療成癮的經歷,都讓她感到疲憊不堪。
艾米麗·杜夫頓:多年來,她一直碰壁,試圖,你知道,幫助她的病人好轉,但他們卻在死亡。所以文森特·多爾說,你知道,嘿,來和我談談。我得到了洛克菲勒大學的支援,它提供了聲望和,嗯,可敬性。我從紐約市得到了一大筆錢,試圖找出如何解決成癮問題。你想來幫我嗎?你想成為洛克菲勒大學的僱員,幫助我嘗試解決成癮問題,我們有錢這樣做嗎?她說,是的,我認為這聽起來是個非常好的主意。因為誰會不願意呢?
凱蒂·哈夫納:文斯也很高興能與瑪麗合作。文斯對瑪麗的反應將在多年後被其他人所回應。首先,她很有魅力,而且她對病人的真誠同情心,她幫助他們的決心。在我們製作這一季的過程中,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和聽到這句話:她看到了她的病人——從外表到內心深處。
文森特·多爾:她給我的印象是一位非常專注和聰明的,嗯,人,她在一個絕對毫無希望的行政劣勢下工作,因為她孤身一人,有一顆善良的心和飽滿的精神,嗯,試圖與整個機構從上到下作鬥爭。
凱蒂·哈夫納:瑪麗顯然也在文斯身上看到了深刻的東西。從一開始,我們就假設,他們之間有化學反應。儘管並非所有人都對此感到高興。特別是瑪麗的丈夫,倫納德·華萊士·羅賓遜。卡羅爾,還記得倫納德寫的那本我們之前談到的書,名叫《愛美之人》,都是關於他心愛的人的嗎?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嗯哼。
凱蒂·哈夫納:是的。嗯,你讀過嗎?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沒有。
凱蒂·哈夫納:哦,好的。讓我告訴你。虛構的文斯在書中佔有重要地位。在書中,文森特·多爾變成了“瑟曼·坎特韋爾”,一位紐約醫生,他招募了“伊麗莎白”,也就是瑪麗,也就是書中的美人,來幫助他尋找治療酒精中毒的方法。
在“瑟曼”邀請“伊麗莎白”加入研究團隊後,伊麗莎白引用“興奮得閃閃發光”——是的,你沒聽錯,閃閃發光。
顯然,倫納德不喜歡文斯/瑟曼這個角色,所以她是美人,瑟曼是野獸。在本書的大部分內容中,他都是野獸。倫納德對這個人,文斯/瑟曼/野獸的描述,並不討人喜歡。他形容他有點“鬥雞眼”,身體有點令人困惑:“6 英尺高”,“拳擊手的鼻子”,以及奇怪的“長頭,像螞蟻一樣”。與病人幾乎沒有床邊禮儀。與文學倫納德不同,瑟曼說話非常笨拙,但最糟糕的是,倫納德寫道,這個人很無聊。
我再次強調,這是一個虛構的敘述。也許是一位丈夫在看著自己的妻子對一個他並不瞭解的全新世界感到興奮時,所懷有的願望。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嗯哼。回到非虛構的敘述。瑪麗於 1964 年 1 月正式被聘用。同月,文斯將另一位成員帶入團隊——一位名叫瑪麗·珍妮·克里克的二年級住院醫師。
瑪麗·珍妮·克里克:現在,你應該問我 1964 年我到達洛克菲勒時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在 2017 年的這次口述歷史採訪中,在她去世前幾年,瑪麗·珍妮習慣於同時扮演採訪者和受訪者的角色。在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後,她立即開始回答。
瑪麗·珍妮·克里克:嗯,那很棒。女性非常稀少,說得客氣點。多爾教授在面試時告訴我,我很喜歡他,但他告訴我穿上白色連衣裙。
凱蒂·哈夫納:白色連衣裙。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是的,顯然,那是當時在洛克菲勒工作的女性穿的衣服。那裡有著裝規範。女性技術員穿白色連衣裙,儘管醫生穿實驗服,瑪麗·珍妮就是醫生,所以不清楚為什麼她被要求穿連衣裙。
瑪麗·珍妮·克里克:我說不,我被告知下樓去創始人樓的女士餐廳,那裡每個人都穿著白色連衣裙。我說不,不。正如我們現任校長瑞克·利夫頓去年九月第一次見到我時所說,他說,我希望你說的是“他媽的不”。我說,不,瑞克,我沒有說髒話,因為我從小就被教導不要那樣說。現在我會說髒話了,但我只是說了不,不。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所以瑪麗·珍妮繼續穿著她平常的衣服。幸運的是,事實證明女性仍然可以穿著這些衣服做研究。
好的,那是我們的研究三人組——瑪麗、文斯和瑪麗·珍妮。正如瑪麗·珍妮解釋的那樣,她是團隊中的臨床醫生,這意味著她做的事情包括觀察反應和監測副作用。
瑪麗是精神科醫生,她可以接觸到病人,並且最熟悉成癮者的行為和心理。
文斯做了大部分的計劃和研究設計,策劃實驗的樣子
凱蒂·哈夫納:他們首先在城裡四處走動,採訪成癮者。很快,很明顯,他們即將偏離劇本,嘗試一些非常不正統的事情,至少在當時的美國是這樣:放棄戒斷的目標。
瑪麗·珍妮·克里克:瑪麗、文斯和我過去常常在與病人交談後進行這些智囊團會議,我們會聽到這樣的故事——你喜歡海洛因嗎?不是真的。你必須服用越來越多的劑量。你最多隻能興奮 10 分鐘、20 分鐘。然後,你大約可以正常一兩個小時。如果你服用過多,你會昏昏欲睡,打瞌睡。然後你會進入戒斷期,你每天必須這樣做四到六次。這太可怕了。但是,當我停止服用時,我感覺不正常。當他們把我送到監獄,我沒有任何藥物,或者把我放在一個無毒的環境中時,我感覺不正常。這不是說我沒有它就無法興奮。非常重要的區別。而是我沒有它就感覺不正常。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這開始聽起來像是一種身體狀況,而不是一種心理狀況。 病人們描述的方式,成癮真的不是為了追求快感的興奮。他們渴望一些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就無法正常運作的東西,幾乎像某種缺陷。
凱蒂·哈夫納:文斯實際上已經考慮這個問題一段時間了,並提出了他後來稱之為成癮“代謝理論”來解釋它。這個想法是這樣的:成癮者的生物化學成分中存在某種東西,使他們渴望藥物。也許成癮者不是某種性格缺陷,而是在一開始就具有“神經易感性”,並且在反覆使用藥物後,他們的神經元會發生代謝變化——儘管文斯當時無法確切地說出這些變化是什麼。
這與其說是一個經過充分論證的理論,不如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它將他們指向了一個特定的方向——因為如果問題是生化失衡,那麼治療可能需要是藥理學的。洛克菲勒團隊和其他人會一遍又一遍地回到糖尿病的類比。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島素。身體沒有它就無法正常運作,而阿片類藥物成癮者可能只需要阿片類藥物。無限期地。
從這個角度來看,戒斷藥物的方法永遠行不通。但是,那麼替代方案是什麼呢?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在多年嘗試一切方法都失敗後,瑪麗非常渴望嘗試新的方法。她想知道,如果只是給人們藥物會發生什麼?嗯,這實際上是一個可以透過經驗回答的問題。
即將到來:實驗。
==== 分隔符 ====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在 1960 年代初期,當洛克菲勒三人組開始進行他們的第一次實驗時,他們敢於提出一個當時有爭議,現在也有爭議的問題:海洛因到底有什麼問題?
文森特·多爾:那是我問的第一個問題之一,我說,哎呀,如果它沒有明顯地殺死這些人,我看不出這有什麼不好。當然,在街上吸毒會殺死他們,並且透過他們必須支付的高價以及搶劫造成的犯罪來殺死社會。我說,我真的不明白大家在談論什麼。讓他們吸毒吧。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是的。我相信你們中的一些人在這裡有強烈的反應。我想明確一點,海洛因絕對對你不好。在美國,每年有數萬人死於海洛因和其他阿片類藥物過量。儘管芬太尼(一種合成阿片類藥物)已經大大超過了海洛因,但海洛因每年仍然殺死數千人。它會抑制你的呼吸驅動——如果你服用過多,你的呼吸會變得越來越慢、越來越淺,直到你完全停止呼吸。
凱蒂·哈夫納:正如文斯所看到的那樣,使危險加劇的是犯罪化,人們被迫採取各種手段來獲取海洛因。再加上街頭毒品質量不可靠。也許,如果藥物在安全合法的受控環境中給藥——仔細劑量且沒有汙染——那麼這些藥物不一定那麼危險?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維持療法:這種想法是,你可以透過讓吸毒者繼續吸毒來讓他們感到舒適,並且能夠正常運作——或者至少更好。在維持療法下,患者不必處理反覆的戒斷症狀或持續不斷的渴望。他們不必為了獲取毒品而違法。他們不必擔心一旦拿到毒品後,毒品中到底有什麼。他們可以專注於其他事情。這實際上是當時英國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
正如瑪麗所說,她對這個想法的最初反應是震驚。有一次,她會見了一位著名的醫學作家布萊克·卡博特。他們坐在那裡聊天,他對瑪麗說,你有沒有停下來想過,給吸毒者毒品到底有什麼問題?
瑪麗·尼斯萬德:我差點暈倒,我差點把他趕出家門。我離開了房間,這簡直就像說了一句帶有偏見的陳述,你知道。我只是——我必須控制住自己。所以,我——顯然在那裡做出了一些情感上的飛躍。(嗯哼)而且,嗯,然後我開始收集不同的資訊,就像你總是做的那樣,你知道,你排除與你的想法不符的資訊。(嗯哼)
凱蒂·哈夫納:卡羅爾,我想談談這個整體概念。事實上,大衛·考特賴特寫了一篇關於它的論文,名為“有準備的頭腦”。這就是我們在科學中經常看到的,是有準備的頭腦引導你發現。
因此,在多年嘗試其他方法都失敗後,她準備嘗試新的方法,瑪麗·珍妮、瑪麗和文斯團隊決定從基礎開始——找出藥物實際上對人有什麼作用。這意味著將人們帶到非常正直的洛克菲勒研究所,並給他們藥物。
瑪麗·珍妮·克里克:想想看。這是一個原始的環境,美麗的花園,安靜的科學家,以及 1900 年代初期建立的可愛的小醫院。我們想帶入活躍的海洛因成癮者,哦,我的天哪。
凱蒂·哈夫納:這不僅會引起一些人的側目,而且在法律基礎上也值得懷疑,或者至少根據聯邦麻醉品管理局的說法是這樣。他們認為,根據 1914 年的《哈里森麻醉品法案》,這是非法的,該法案是一項限制麻醉品銷售和處方的大型聯邦反毒品法律。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而且管理局可能很可怕。三十年來,它由哈里·安斯林格領導,他是華盛頓最有權勢的人之一,也是美國曆史上一個傳奇人物。瑪麗形容他的方式,他就像一個卡通反派。
瑪麗·尼斯萬德:就像一個暴君的電影角色[笑]。他有點禿頂,脖子很粗,臉色紅潤,不太愛笑。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在安斯林格的領導下,管理局逮捕了過度處方阿片類藥物的醫生——管理局決定了什麼算作過度處方。哈里·安斯林格最終於 1962 年退休,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在一年後接受巴爾的摩電視臺的採訪。
哈里·安斯林格:在這個國家的城市街道上行走的普通吸毒者就像麻風病人一樣。他傳播疾病。嗯,他必須被清除出流通。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清除出流通。”令人不寒而慄。
凱蒂·哈夫納:這就是瑪麗和她的團隊所處的背景。瑪麗在這一點上已經與管理局發生了一些衝突好幾年了。由於她早期對成癮患者的工作,她引起了管理局的注意——特工開始不請自來地來到她的辦公室和會議。她和她的新合作者計劃的事情至少可以說很大膽,而且他們不想惹麻煩。幸運的是,團隊有文森特·多爾,他傾向於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
文森特·多爾:我首先問,嗯,布朗克是洛克菲勒的校長,如果我進入這樣一個政治上有爭議的領域,是否會給他帶來任何問題,我說,據我所知,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國家的任何醫生或機構來說都太棘手了。他說,如果是這樣,他說,那麼這是我們的工作。他從來沒有對我的任何壓力提出任何疑問,我想他可能是透過他的權威來轉移了這些壓力。
凱蒂·哈夫納:就這麼簡單。他們也有法律支援。洛克菲勒的律師得出結論,與管理局所說的相反,法律實際上站在醫生一邊,《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實際上並沒有禁止他們開阿片類藥物,如果他們認為這對於治療或臨床研究是必要的。然而,幾十年來,管理局一直在恐嚇和逮捕醫生,直到他們對受人尊敬的文森特·多爾嘗試這樣做。
文森特·多爾:不久之後,麻醉品管理局派來了一名特工,他以最專橫、傲慢的方式進來,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說,你正在違法。我說,嗯,我一直在調查這件事,據我所知,我沒有。他們說,嗯,你就是違法了,如果你不停止,我們就會讓你倒閉。所以我說,嗯,也許那是應該做的事情。我說,鑑於你們的理解,你們應該做的事情是起訴我。
凱蒂·哈夫納:就好像他說了一句咒語——文斯完全解除了特工的武裝。
文森特·多爾:他突然結束了討論,並說他必須與他的上級進一步討論。這種型別的互動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重複了一兩次,直到他們確信真的沒有簡單的方法可以透過威脅迫使我們退出。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就這樣,團隊可以開始工作了。他們只需要研究物件。他們從兩名男性開始,一名 30 多歲的義大利裔美國人和另一名 20 多歲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兩人都對海洛因成癮。
瑪麗·尼斯萬德:無論如何,帶來了兩名[笑]安靜而虛弱——嗯,沒那麼虛弱——的癮君子,讓他們服用麻醉品,我被允許讓他們服用任何我想服用的麻醉品,任何劑量。我們只是試圖讓他們感到舒適。
凱蒂·哈夫納:計劃是讓這些病人住在洛克菲勒,服用各種藥物,並讓醫生觀察效果。一旦試驗開始,觀察他們就成了團隊的全職工作。文斯、瑪麗和瑪麗·珍妮開始一起在診所裡度過很多時間,尤其是瑪麗和文斯。
在倫納德的虛構敘述中,他描述了瑪麗/伊麗莎白是如何開始改變她的社交生活的。再次,我請我的丈夫鮑勃來朗讀。他對他的朗讀變得非常自信了。
鮑勃飾演倫納德:她轉到生物學領域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她不得不比我見過的任何時候都更努力地工作。她現在工作到很晚,我們的社交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的朋友變成了我的朋友,反之亦然——主要是畫家、詩人、教師。但是現在,又增加了科學家。
凱蒂·哈夫納(麥克風外):不錯,不錯。
鮑勃:是的,那還不錯,那還不錯。
凱蒂·哈夫納:所以,是的,她正在逐漸遠離倫納德,進入這個新角色,進入硬科學的世界,更深入地進入她的病人的世界。她在哈萊姆區的老病人進進出出她的生活,但現在她的病人是她全職護理的研究物件。
瑪麗·尼斯萬德:我只是試圖讓兩名服用麻醉品的病人感到舒適。
凱蒂·哈夫納:那麼,什麼藥物能讓病人感到舒適呢?正如瑪麗多年後告訴大衛·考特賴特的那樣,團隊嘗試了他們能想到的一切——嗎啡、二氫嗎啡酮、止咳藥,甚至常規劑量的海洛因本身!但沒有任何效果。
瑪麗·尼斯萬德:病人們很不高興。他們看著手錶,一會兒戒斷,一會兒又舒服一點,可能就舒服一個小時。從來不穿衣服。除了等待下一次注射,沒有任何其他目標。劑量不斷增加,但這並不是一個讓他們興奮的專案,而只是為了讓他們感到舒適。我無法讓他們正常生活。我根本無法讓他們正常生活。因此,在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個月,劑量變得如此之高之後,很明顯這是一個失敗。
凱蒂·哈夫納:在瑪麗看來,他們似乎已經嘗試了一切,但有一種藥物團隊還沒有嘗試過——鹽酸美沙酮。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實際上,美沙酮在那時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它在近二十年前從戰後德國傳入美國。
大衛·考特賴特:嗯,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當美國人開始研究他們從德國帶走的所有技術和科學資訊時,他們發現,哦,嘿,德國人有這種新的合成藥物。果然,測試很快證實,它的效果與嗎啡類似。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它是由德國公司法本公司開發的,該公司與納粹政權密不可分,有時被稱為“魔鬼的化學家”。法本公司在戰爭期間使用了數萬名奴隸勞工,其中許多來自奧斯威辛集中營,在其工廠工作。它生產了齊克隆B——毒氣室中使用的毒藥。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他們還生產了美沙酮,德國人稱之為amidon。像所有阿片類藥物一樣,它是一種強效止痛藥,事實證明,它比嗎啡強大得多。
大衛·考特賴特:而且,這種藥物的影響,嗯,很快在醫學界和舊的聯邦麻醉品管理局變得顯而易見。
嗯,醫學界認為它是一種潛在的有價值的合成阿片類鎮痛藥,而麻醉品管理局也這樣認為,但也認為它是一種存在成癮或轉移風險的藥物,需要像其他麻醉藥品一樣受到監管。
因此,這裡存在一些法律上的策略,但最終管理局佔了上風,並將其歸類為像嗎啡一樣的麻醉藥品。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在肯塔基州的列剋星敦麻醉品農場,研究中心也對美沙酮感興趣,他們對患者進行了實驗。這與瑪麗在那裡的時候很接近——甚至可能是在同一時間。
大衛·考特賴特:果然,它滿足了他們的渴望。它阻止了他們進入戒斷狀態。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至少根據早期的一項研究,問題是,一些患者似乎太喜歡美沙酮了。當研究人員將其給予對嗎啡上癮的人時,他們聽到這樣的評論:“這東西太棒了。”“我真不敢相信合成藥物會如此像嗎啡。”“你能在外面弄到嗎?”研究人員的結論是,這種藥物有風險——如果它變得可以自由獲得,肯定會被濫用。在那之後,美沙酮就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凱蒂·哈夫納:因此,回到1964年,洛克菲勒團隊一直在嘗試他們能想到的一切,但沒有任何效果。他們的患者服用了高劑量的阿片類藥物,但他們仍然易怒、分心和不滿。然後,醫生們決定嘗試美沙酮。由於他們的患者一直在服用高劑量的其他阿片類藥物,他們給他們服用了等量高劑量的美沙酮——大概是為了避免嚴重的戒斷症狀。
現在,當美沙酮用於戒毒時,劑量大約是15到25毫克,最多可能是40毫克。但是,為了匹配他們已經給這兩個男人服用的高水平阿片類藥物,團隊必須將美沙酮劑量提高很多。
瑪麗·尼斯萬德:這些劑量非常大,達到90毫克、80毫克、90毫克、100毫克。我們對這個劑量感到非常害怕。
凱蒂·哈夫納:但他們還是繼續進行了。第二天或後天,出現了兩個年輕人,與他們之前見過的任何人都不同。病人們衣著整潔,臉色紅潤。他們看起來好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瑪麗·尼斯萬德:我不相信。我經歷的時間太長了,見過太多後來證明無效的奇蹟。所以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沒有這種過去失敗經歷的瑪麗·珍妮·克里克,一開始就注意到了並相信了這一點。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瑪麗不願意抱太大希望。但瑪麗·珍妮,她能看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發生。文斯也注意到了。他已經養成了每天與病人聊天大約兩三個小時的習慣。只是隨意地交談,以便更好地瞭解他們。當他們開始服用美沙酮時,他注意到了一種轉變。
文森特·多爾:我們的談話開始進入軌道,比如,嗯,棒球和政治,以及你可能會遇到的更一般性的話題,而不是沒完沒了地回憶,嗯,吸毒經歷。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病人們似乎再次對自己的生活感興趣了。他們甚至要求回到學校完成學業。洛克菲勒的醫生們在他們嘗試過的其他任何方法中都沒有見過這種情況。
凱蒂·哈夫納:因此,在這一點上,美沙酮看起來很有希望。但到目前為止,這些病人一直全天候生活在這個受控的醫院環境中。是的,這種治療似乎改變了病人。但是,如果他們真的走出去進入社會會發生什麼呢?只有一種方法可以找出答案。但是,瑪麗很緊張。
瑪麗·尼斯萬德:我不知道我想信任它到什麼程度。嗯,我現在可以看到他們說他們不想要任何藥物。好的。但是,現在當他們走在街上時,當他們走在街上,看到吸毒者時,這種美沙酮會起作用嗎?他們仍然會不注射就回家,他們會回來嗎?
凱蒂·哈夫納:在醫院外生活,遇到城市中所有的艱辛和誘惑,那才是真正的考驗。考驗即將開始。病人們仍然睡在醫院裡,但在白天,他們可以自由地去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有一天,他們出發了。
瑪麗·尼斯萬德:我晚上會坐在這裡等著他們回來,每天晚上都完全恐懼,在他們回來之前我不會回家。我不能告訴他們,因為我不想給他們施加壓力。
凱蒂·哈夫納:但他們確實在第一天回來了。第二天,以及之後的一天。一遍又一遍,病人們都回來了。有一次,他們告訴瑪麗這個故事,他們告訴她,是的,我們看到有人在街對面買毒品,但我們沒有感到誘惑。
有了美沙酮,他們就不再渴望海洛因了。那天他們渴望的是什麼呢?冰淇淋。是的,她的病人告訴她,他們沒有買海洛因,而是去買了冰淇淋甜筒。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這些結果令人震驚,但這僅僅是一個僥倖嗎?接下來,洛克菲勒的醫生們將美沙酮的研究擴大到另外六名患者,這是一個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的多樣化群體。結果再次相同。
瑪麗·尼斯萬德:他們看起來都很棒,並且去上學了。而且,你從來沒有見過六個如此漂亮、有魅力的年輕人。我們請了一些緝毒人員來見他們並與他們交談。在那些日子裡,我們邀請人們進來。所以,我想有兩三個緝毒人員來了,我們正在談論麻醉品,然後我們將他們介紹給病人,說,嗯,這裡有一些吸毒者。你們想和他們談談嗎?他們說,哦,這些人不是癮君子。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瑪麗和她的團隊似乎找到了一種可能有效的治療方案。但他們找到了嗎?
下一次:瑪麗和文森特與世界分享了他們的發現——但並非所有人都喜歡。
凱蒂·哈夫納:《迷失的科學女性》播客由我,凱蒂·哈夫納主持——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和我,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本集由佐伊·庫爾蘭、諾拉·馬蒂森和我們的高階製片人伊拉·費德爾製作,艾莉克薩·林、艾瑪·沙利文、麥肯齊·塔塔南尼和多米尼克·賈尼提供幫助。
凱蒂·哈夫納:我們得到了丹雅·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事實核查幫助。我們所有的音樂都由莉齊·尤南創作。D·彼得施密特為本集混合和設計了聲音。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再次衷心感謝大衛·考特賴特,他與我們分享了他的口述歷史收藏。它名為《倖存的癮君子》,其中包括您聽到的對瑪麗·尼斯萬德和文森特·多爾的採訪以及更多內容。
凱蒂·哈夫納:我要感謝我在“迷失的科學女性”的聯合執行製片人艾米·沙夫。我們部分由阿爾弗雷德·P·斯隆基金會和施密特未來基金資助。我們的播客由PRX發行,並與《大眾科學》合作釋出。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有關節目註釋和更多關於製作該節目的整個團隊的資訊,請訪問lostwomenofscience.org。最後,如果您喜歡您聽到的內容,請告訴您認識的一個人!今天就告訴!這對節目真的很有幫助!
凱蒂·哈夫納:是的。你告訴一個人,然後五個人就會知道。
卡羅爾·薩頓·劉易斯:[笑] 什麼?凱蒂瘋了。
凱蒂·哈夫納:下週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