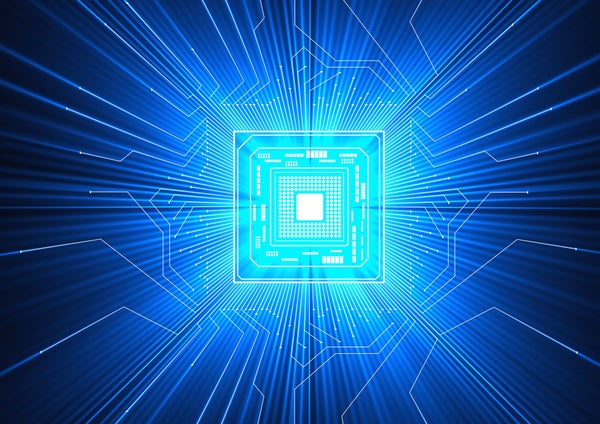在成為一名理論物理學家之前,斯蒂芬妮·韋納是一名駭客。像那個領域的多數人一樣,她從小就自學成才。15歲時,她用積蓄購買了她的第一個撥號調變解調器,在她德國維爾茨堡父母的家中使用。到了20歲,她已經獲得了足夠的街頭信譽,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由其他駭客創辦的荷蘭網際網路提供商那裡找到了一份工作。
幾年後,當韋納擔任網路安全專家時,她上了大學。在那裡,她瞭解到量子力學提供了一些當今網路非常缺乏的東西——無法被駭客攻擊的通訊潛力。現在,她將自己舊的痴迷轉向了一個新的渴望。她想重塑網際網路。
量子粒子處於未定義狀態的能力——就像薛定諤那隻著名的貓,既活著又死去——已經被使用多年來增強資料加密。但是,現在在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韋納和其他研究人員認為,他們可以透過利用自然界將遙遠物體連線或糾纏在一起,並在它們之間傳送資訊的神奇能力,利用量子力學做更多的事情。韋納說,起初,這一切聽起來都非常理論化。現在,“人們有了實現它的希望”。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關於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支持者說,這種量子網際網路可以開啟一個經典通訊無法實現的全新應用領域,包括將量子計算機連線在一起;使用廣泛分離的觀測站構建超清晰望遠鏡;甚至建立探測引力波的新方法。有些人認為它有一天會取代當前形式的網際網路。維也納大學的物理學家安東·蔡林格說:“我個人認為,在未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通訊都將是量子的。”他於 1997 年領導了第一個量子隱形傳輸實驗。
代爾夫特的一個團隊已經開始構建第一個真正的量子網路,該網路將連線荷蘭的四個城市。該專案預計將於 2020 年完成,它可能是量子版的 ARPANET,這是美國軍方在 1960 年代後期開發的一種通訊網路,它為當今的網際網路鋪平了道路。
參與這項工作的韋納還在協調一個更大的歐洲專案,稱為量子網際網路聯盟,旨在將荷蘭的實驗擴充套件到整個歐洲大陸。作為該過程的一部分,她和其他人正試圖將計算機科學家、工程師和網路安全專家聚集在一起,以幫助設計未來的量子網際網路。
許多技術細節仍需理清,一些研究人員警告說,現在就斷言量子網際網路可能帶來多大的成果還為時過早。但韋納說,透過儘早考慮安全性,她希望避免網際網路從 ARPANET 繼承來的漏洞。“也許我們有機會從一開始就把它做好。”
量子金鑰
量子通訊的最初提案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左右。當時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年輕物理學家斯蒂芬·威斯納看到了量子力學最基本原理之一的潛力:不可能在不改變系統的情況下測量系統的屬性。
威斯納提出,資訊可以編碼在諸如孤立原子之類的物體的狀態中,這些原子的“自旋”可以向上或向下指向——就像經典位的 0 和 1 一樣——但也可以同時處於兩種狀態。這種量子資訊單元現在通常被稱為量子位或量子位元。威斯納指出,由於無法在不改變數子位元狀態的情況下測量其屬性,因此也不可能製作出精確的副本或“克隆”。否則,有人可以簡單地透過測量其克隆來提取有關原始量子位元狀態的資訊,而不會影響它。這種禁止後來被稱為量子不可克隆,事實證明,它對安全性有利,因為駭客無法在不留下痕跡的情況下提取量子資訊。
受威斯納的啟發,1984 年,紐約州約克鎮高地的 IBM 的計算機科學家查爾斯·貝內特和他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合作者吉勒斯·布拉薩德提出了一個巧妙的方案,兩個使用者可以透過該方案生成一個只有他們知道的牢不可破的加密金鑰。該方案依賴於光可以被偏振的事實,因此電磁波可以在水平面或垂直面中振盪。一個使用者將隨機的 1 和 0 序列轉換為編碼在兩個偏振狀態中的量子金鑰,並將其流式傳輸給另一個人。透過一系列步驟,接收者測量金鑰並確定傳輸沒有受到竊聽者的測量干擾。在確信金鑰安全性的情況下,雙方可以隨後對任何由經典位組成的訊息(例如,影像)進行加擾,然後像透過傳統網際網路或任何其他通道傳送其他加密訊息一樣傳送它。
1989 年,貝內特領導的團隊首次透過實驗演示了這種“量子金鑰分發”(QKD)。如今,使用類似方案的 QKD 裝置已在市場上銷售,通常出售給金融或政府組織。例如,ID Quantique 是一家於 2001 年在瑞士日內瓦成立的公司,構建了一條量子鏈路,該鏈路十多年來一直保護著瑞士的選舉結果。
去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學家潘建偉的傑作“墨子號”衛星對該方法進行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演示。該航天器使用貝內特和布拉薩德協議的變體,建立了兩個金鑰,然後在飛過時將一個金鑰傳送到北京的地面站,另一個金鑰傳送到維也納。然後,一個車載計算機將兩個秘密金鑰組合在一起,建立一個新的金鑰,並以經典方式將其向下傳送。維也納和北京的團隊透過本質上減去他們自己的金鑰來解擾該組合金鑰,從而瞭解對方的秘密金鑰。有了這兩個金鑰,一個團隊可以解密另一個團隊使用其金鑰加密的傳輸。去年 9 月,潘和蔡林格使用這種方法建立了首次洲際影片聊天,該聊天部分是透過量子金鑰進行保護的。
諸如墨子號之類的衛星可以幫助解決當今量子通訊安全性的主要挑戰之一:距離。建立加密金鑰所需的光子會被大氣吸收,或者(在地面網路的情況下)被光纖吸收,這使得量子傳輸在幾十公里後變得不切實際。
由於量子態無法複製,因此傳送多個量子位元副本以希望至少一個會到達是不可行的。因此,目前,建立長距離 QKD 鏈路需要構建“可信節點”作為中介。如果有人侵入可信節點(該節點以量子和經典形式處理金鑰),他們將能夠複製金鑰而不會被發現——當然,運營該節點的政府或公司也可能這樣做。對於地面上的可信節點和墨子號來說都是如此。“衛星知道一切,”潘說。但是,經過的衛星可以減少連線遙遠點所需的可信節點的數量。
潘說,可信節點對於某些應用來說已經向前邁進了一步,因為它們減少了網路易受攻擊的點。他還領導了廣泛的北京-上海量子通訊骨幹網的建立。該骨幹網於 9 月份啟動,使用超過 2,000 公里的光纖將 4 個城市與 32 個可信節點連線起來,並且正在測試銀行和商業通訊,例如連線網際網路購物巨頭阿里巴巴的資料中心,潘說。
量子連線
但是,涉及可信節點的網路只是部分量子化的。量子物理學僅在節點如何建立加密金鑰方面起作用;隨後的資訊加密和傳輸完全是經典方式。真正的量子網路將能夠利用糾纏和隱形傳輸在長距離上傳輸量子資訊,而無需易受攻擊的可信節點。
構建此類網路的主要動機之一是使量子計算機能夠相互通訊,無論是在國家之間還是在單個房間內。可以打包到任何一個計算系統中的量子位元數量可能受到限制,因此將系統聯網在一起可以幫助物理學家擴大它們的規模。“在這一點上,可以公平地說,你可能能夠構建一個擁有幾百個量子位元的量子計算機,”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家米哈伊爾·盧金說。“但除此之外,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法是使用這種模組化方法,涉及量子通訊。”
在更大的規模上,研究人員設想了一個量子計算雲,其中有少數高度複雜的機器可以透過量子網際網路從大多數大學實驗室訪問。“額外的酷炫之處在於,這種雲量子計算也是安全的,”代爾夫特的實驗物理學家羅納德·漢森說。“伺服器上的人無法知道你正在執行哪種程式以及你擁有的資料。”
研究人員提出了許多其他網際網路應用提案——例如拍賣、選舉、合同談判和高速交易——這些應用可以利用量子現象使其比經典應用更快或更安全。
但量子網際網路的最大影響可能在於科學本身。一些研究人員表示,利用糾纏同步時鐘可以將全球定位系統(GPS)類導航網路的精度從米級提高到毫米級。盧金等人還提議使用糾纏將遠距離原子鐘組合成一個精度大大提高的單一時鐘,他說這可能會帶來探測引力波的新方法。在天文學方面,量子網路可以將數千公里外的遙遠光學望遠鏡連線起來,從而有效地使它們獲得與該距離相同的單個天線的解析度。這種稱為甚長基線干涉測量法的技術已在射電天文學中得到常規應用,但在光頻下執行則需要目前無法達到的時間精度。
幽靈般的安全
在過去的十年左右,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的物理學家克里斯托弗·門羅和其他人開創的實驗已經證明了構建真正量子網路所需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將編碼在量子位元中的資訊從一個地方瞬移到另一個地方(參見“建立量子網際網路”)。
為了瞭解瞬移(也由貝內特和布拉薩德提出)的工作原理,想象一下兩位使用者:愛麗絲和鮑勃。愛麗絲持有一個量子位元,它可以是一個俘獲的離子或其他量子系統,她想將其儲存的資訊轉移給鮑勃。幸運的是,愛麗絲和鮑勃擁有兩個“代理”粒子,它們也是彼此糾纏的量子位元。如果愛麗絲能夠將她的量子位元和代理粒子糾纏在一起,那麼該量子位元也會因此與鮑勃的粒子糾纏在一起。為此,愛麗絲對她的兩個粒子進行一種特殊的聯合測量。然後,她與鮑勃分享該測量的結果(這些結果是普通的經典資料)。為了完成瞬移過程,鮑勃然後使用該資訊來操縱他的粒子,使其最終處於與愛麗絲的量子位元最初相同的狀態。
出於實際目的,愛麗絲和鮑勃如何獲得糾纏的代理粒子並不重要。例如,它們可以是由手提箱運送的單個原子,或由第三方發射到這對粒子的光子。(去年,墨子號的一項實驗將糾纏的光子對傳送到中國兩個地面站,距離超過了創紀錄的1200公里。)愛麗絲和鮑勃也可以透過將光子傳送到第三個位置進行互動,從而使他們持有的量子位元糾纏在一起。
量子瞬移的美妙之處在於量子資訊在技術上並不沿網路傳輸。傳輸的光子僅用於在愛麗絲和鮑勃之間建立連結,以便隨後可以傳輸量子資訊。如果一對糾纏的光子未能建立連線,則會使用另一對。這意味著如果光子丟失,量子資訊不會丟失。
連結與重複
量子網際網路將能夠在任何兩個使用者之間按需產生糾纏。研究人員認為,這將涉及透過光纖網路和衛星鏈路傳送光子。但是,連線遠距離使用者將需要一種能夠擴充套件糾纏範圍的技術,即在使用者之間以及沿中間點中繼糾纏。
盧金及其合作者在2001年提出了量子中繼器的一種工作方式。在他們的方案中,可以使用可以儲存量子位元並對其執行簡單操作的小型量子計算機,來使上游站的量子位元與下游站的量子位元糾纏。沿著網路路徑重複應用這種“糾纏交換”過程最終會在任意兩個使用者之間產生糾纏。
2015年,漢森及其合作者展示瞭如何構建網路的一條腿,當時他們連線了由金剛石晶體中單個原子雜質構建的兩個量子位元,它們之間的距離為1.3公里。兩個量子位元發射的光子向中間站傳播,然後在那裡相互作用,從而建立了糾纏。“這表明可以真正地在兩個遙遠的量子資訊處理器之間建立糾纏——強大的、可靠的糾纏,”馬薩諸塞州劍橋市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塞思·勞埃德說。
研究人員正在研究構建和操縱量子位元的其他方法,包括使用懸浮在真空中的單個離子(由門羅和其他人開創),以及使原子和在腔體內兩個鏡子之間反彈的光子配對的系統。
與漢森的金剛石系統一樣,這些量子位元可用於構建量子中繼器和量子計算機。對於希望加強量子通訊的人們來說,幸運的是,中繼器的要求可能不如成熟的量子計算機的要求高。巴黎狄德羅大學的量子計算研究員約爾達尼斯·凱雷尼迪斯在去年9月在奧地利塞費爾德舉行的量子中繼器研討會上提出了這一論點。“如果你告訴實驗人員你需要1000個量子位元,他們會笑,”他說。“如果你告訴他們你需要十個——好吧,他們就笑得少了。”
建立量子網際網路的前景現在正在成為一個系統工程問題。“從實驗的角度來看,人們已經展示了量子網路的各種構建模組,”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的物理學家特蕾西·諾瑟普說,她的團隊致力於腔量子位元的研究,並且是韋納泛歐量子網際網路聯盟的一部分。“但是將它們放在一個地方——我們都看到了這是多麼具有挑戰性,”諾瑟普說。
目前,韋納的聯盟仍處於早期階段,正在尋求公共資金以及企業合作伙伴。與此同時,荷蘭的示範網路——韋納與漢森和荷蘭研究機構TNO的聯合系統工程師埃爾文·範·茲韋特共同領導——一直在向前發展。漢森和他的同事們一直在提高系統的速度,在2015年的實驗中,他們在相當於約9天的時間裡只糾纏了245個量子位元對。另一個關鍵挑戰是可靠地將來自金剛石量子位元的可見波長的光子轉換為可以在光纖中良好傳輸的較長紅外波長的光子;這很棘手,因為新的光子仍然必須攜帶舊光子的量子資訊,但又不可能克隆它。今年早些時候,漢森和他的同事透過使光子與較長波長的雷射束相互作用實現了這一目標。該技術將使量子位元能夠在光纖上以數十公里的距離連線起來。
漢森的團隊現在正在代爾夫特和海牙之間建立一個連結,這兩個地方相隔10公里。到2020年,研究人員希望連線四個荷蘭城市,每個站點都有一個站點充當量子中繼器。如果成功,該專案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量子瞬移網路。該小組的目標是向其他有興趣遠端進行量子通訊實驗的團隊開放該網路,就像IBM的量子體驗一樣,該體驗允許遠端使用者訪問基本的量子計算機。
該網路可以成為研究人員修復網際網路的一些缺陷的試驗平臺,尤其是使用者偽造或竊取身份的便利性。“從一開始,加入網路而無需建立身份的想法就是一個問題,”電信裝置巨頭思科的網路工程師羅伯特·布羅伯格在塞費爾德會議上說。韋納和其他人提出了量子技術,該技術將允許使用者透過證明他們擁有正確的秘密程式碼(一系列經典位元)來證明其身份,而無需傳輸該程式碼。相反,使用者和伺服器使用程式碼建立一系列量子位元,並將它們傳送到中間的“黑匣子”。黑匣子(例如,可以是一臺自動取款機)可以比較這兩個序列以檢視它們是否匹配,而無需知道基礎程式碼。
但是一些研究人員警告不要過度宣傳這項技術的潛在影響。“今天的網際網路永遠不會完全是量子的,就像計算機永遠不會全部是量子的一樣,”瑞士日內瓦大學的物理學家,ID Quantique的聯合創始人尼古拉斯·吉辛說。並且人們希望透過量子網路實現的許多事情可以透過更傳統的技術來完成。“有時,乍一看某個東西似乎是個好主意,然後事實證明,在沒有量子效應的情況下很容易實現,”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物理學家諾伯特·呂特肯豪斯說,他正在幫助制定未來量子網際網路的標準。
時間會證明量子網際網路的承諾是否會實現。據我們所知,瞬移是一種雖然在物理上可行,但不會在自然界中發生的現象,Zeilinger說。“所以這對人類來說真的是全新的。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韋納對物理學和網路安全的熟悉使她成為該領域人們的參考點。在完成了許多核心量子理論工作之後,她很享受有機會塑造這些未來的網路。“對我來說,”她說,“這真的是一個完整的迴圈。”
更正 2018年2月22日:本故事的早期版本指出,羅納德·漢森正在領導荷蘭示範網路的建設。該專案有三位共同負責人。
本文經許可轉載,並於2018年2月14日首次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