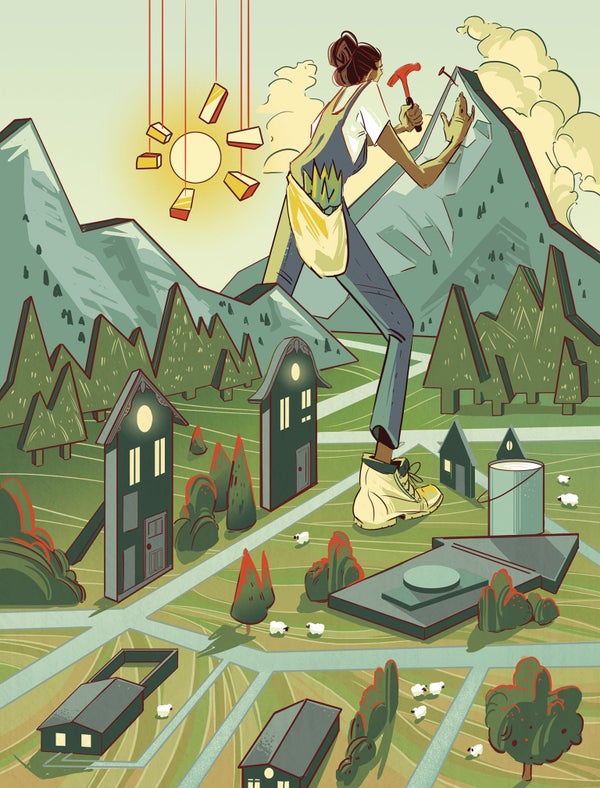“我們不是如實地看待事物,而是以我們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
——摘自阿奈斯·寧 (Anaïs Nin) 的《牛頭怪的誘惑》(1961 年)
On the 10th of April 2019 Pope Francis, President Salva Kiir of South Sudan and former rebel leader Riek Machar sat down together for dinner at the Vatican. They ate in silence, the start of a two-day retreat aimed at reconciliation from a civil war that had killed some 400,000 people since 2013. At about the same time in my labora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in England, Alberto Mariola, then a Ph.D. student, was starting to work on an experiment in which volunteers experienced being in a room they believed was there but was not. In psychiatry clinics across the globe, people arrive complaining that things no longer seem “real” to them, whether it is the world around them or their own selves. In the fractured societies in which we live, what is real—and what is not—seems to be increasingly up for grabs. Warring sides may experience and believe in different realities. Perhaps eating together in silence can help because it offers a small slice of reality that can be agreed on, a stable platform on which to build further understanding.
我們無需求助於戰爭和精神病來尋找截然不同的內心世界。2015 年,一張曝光不良的連衣裙照片在網際網路上瘋傳,將世界分為兩類人:看到它是藍色和黑色的人(包括我)以及看到它是白色和金色的人(我的半個實驗室)。那些以一種方式看到它的人如此確信自己是對的——連衣裙確實是藍色和黑色或白色和金色——以至於他們幾乎無法相信其他人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它。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一張曝光不良的連衣裙照片,有些人看到是藍色和黑色,另一些人看到是白色和金色。
Swiked.tumblr.com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感知系統很容易被愚弄。視覺錯覺的流行證明了這一現象。事物看起來是一種樣子,但實際上是另一種樣子:兩條線看起來長度不同,但測量後它們是完全相同的;我們在我們知道是靜止的影像中看到運動。通常關於錯覺的故事是,它們利用了感知迴路中的怪癖,因此我們感知到的東西偏離了實際存在的東西。然而,這個故事隱含的假設是,一個正常運作的感知系統會將事物精確地呈現給我們的意識,就像它們本來的樣子。
更深層次的真相是,感知永遠不是通往客觀現實的直接視窗。我們所有的感知都是主動構建的,是大腦對一個世界的本質的最佳猜測,這個世界永遠被感官面紗所遮蔽。視覺錯覺是“駭客帝國”中的裂縫,是對這個更深層次真相的短暫一瞥。
以顏色的體驗為例——比如,我桌子上咖啡杯的鮮紅色。這個杯子看起來確實是紅色的:它的紅色看起來和它的圓形和堅固一樣真實。我體驗的這些特徵似乎是世界上真實存在的屬性,由我們的感官檢測到,並透過複雜的感知機制揭示給我們的心靈。
然而,自從艾薩克·牛頓以來,我們就知道顏色並不存在於外部世界中。相反,它們是由大腦從不同波長的無色電磁輻射的混合物中“烹製”出來的。顏色是進化出的一個巧妙的技巧,可以幫助大腦在不斷變化的光照條件下跟蹤表面。而我們人類只能感知到完整電磁頻譜的一小部分,它位於紅外線的低端和紫外線的高階之間。我們感知的每一種顏色,我們視覺世界的每一個部分,都來自這薄薄的一層現實。
僅僅知道這一點就足以告訴我們,感知體驗不可能是對外部客觀世界的全面表徵。它既比那少,又比那多。我們體驗到的現實——事物看起來的樣子——並不是對實際存在的事物的直接反映。它是大腦為大腦巧妙構建的。如果我的大腦與你的大腦不同,那麼我的現實也可能與你的現實不同。
預測性大腦
在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中,囚犯們終生被鎖在空白的牆壁上,以至於他們只能看到身後火焰旁經過的物體投下的陰影,他們給陰影命名,因為對他們來說,陰影才是真實的。一千年後,但仍然是一千年前,阿拉伯學者伊本·海賽姆寫道,此時此地的感知依賴於“判斷和推斷”的過程,而不是直接訪問客觀現實。又過了數百年,伊曼努爾·康德意識到,不受限制的感官資料的混亂總是毫無意義,除非透過預先存在的概念或“信念”賦予其結構,對他來說,這些概念或“信念”包括先驗框架,如空間和時間。康德的術語“本體”指的是“自在之物”——Ding an sich——一種客觀現實,它對人類感知來說永遠是無法接近的。
今天,這些思想透過一系列有影響力的理論獲得了新的動力,這些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大腦是一種預測機器,對世界(以及其中的自我)的感知是一個基於大腦的關於感官訊號原因的預測過程。
這些新理論通常可以追溯到德國物理學家和生理學家赫爾曼·馮·亥姆霍茲,他在 19 世紀後期提出,感知是一個無意識推斷的過程。在 20 世紀末,亥姆霍茲的觀點被認知科學家和人工智慧研究人員所採納,他們將其重新表述為現在普遍稱為預測編碼或預測處理的概念。
預測性感知的核心思想是大腦試圖透過不斷地對其感官輸入的成因做出和更新最佳猜測來弄清楚世界(或身體內部)中存在什麼。它透過將先前的期望或關於世界的“信念”與傳入的感官資料結合起來,以一種考慮到感官訊號可靠性的方式形成這些最佳猜測。科學家通常將這個過程理解為貝葉斯推斷的一種形式,貝葉斯推斷是一種框架,它規定了當信念或最佳猜測都充滿不確定性時,如何用新資料更新它們。
在預測性感知理論中,大腦透過不斷生成關於感官訊號的預測並將這些預測與到達眼睛和耳朵(以及鼻子和指尖以及身體內外所有其他感官表面)的感官訊號進行比較來近似這種貝葉斯推斷。預測的和實際的感官訊號之間的差異產生了所謂的預測誤差,大腦使用這些預測誤差來更新其預測,為下一輪感官輸入做好準備。透過努力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儘量減少感官預測誤差,大腦實現了近似貝葉斯推斷,而由此產生的貝葉斯最佳猜測就是我們感知到的。
為了理解這種觀點如何顯著地改變我們對感知神經基礎的直覺,從大腦中訊號流動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向來思考是有幫助的。如果我們假設感知是通往外部現實的直接視窗,那麼很自然地會認為感知的content是由自下而上的訊號攜帶的——那些從感官表面向內流動的訊號。自上而下的訊號可能會對感知到的東西進行情境化或潤色,但僅此而已。稱之為“事物看起來的樣子”的觀點,因為它看起來好像世界正在透過我們的感官直接向我們揭示自身。
預測機器的場景非常不同。在這裡,感知的繁重工作是由傳達感知預測的自上而下訊號完成的,而自下而上的感官流僅用於校準這些預測,以某種適當的方式將它們與它們在世界中的成因聯絡起來。在這種觀點中,我們的感知來自內部,就像來自外部一樣多,甚至更多。感知不是對外部客觀現實的被動記錄,而是作為一種主動構建的過程而出現——一種受控的幻覺,正如它已為人所知的那樣。
為什麼是受控的幻覺?人們傾向於將幻覺視為一種虛假的感知,與真實的、符合現實的正常感知形成鮮明對比。預測機器的觀點相反,它暗示了幻覺和正常感知之間的連續性。兩者都依賴於自上而下的、基於大腦的預測和自下而上的感官資料之間的相互作用,但在幻覺期間,感官訊號不再將這些自上而下的預測適當地與其在世界中的成因聯絡起來。那麼,我們所說的幻覺,只是一種不受控制的感知形式,正如正常的感知是一種受控的幻覺形式一樣。
這種感知觀點並不意味著沒有什麼東西是真實的。17 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對“第一性”和“第二性”品質進行了有影響力的區分。物體的第一性品質,如堅固性和空間佔用,獨立於感知者而存在。相比之下,第二性品質僅與感知者相關而存在——顏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區分解釋了為什麼將感知理解為受控幻覺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跳到公共汽車前面。公共汽車具有堅固性和空間佔用等第一性品質,這些品質獨立於我們的感知機制而存在,並且可能對我們造成傷害。公共汽車在我們眼中呈現的方式是一種受控的幻覺,而不是公共汽車本身。
實驗室中的迷幻體驗
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援感知是受控幻覺的觀點,至少在它的廣闊輪廓中是這樣。威爾士卡迪夫大學的克里斯托夫·圖費爾及其同事在 2015 年的一項研究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這項研究中,對早期精神病且易患幻覺的患者評估了識別所謂雙色調影像的能力。
看一下下面的照片——一個雙色調影像的樣本。你可能只會看到一堆黑白斑點。現在看看下面的圖片。然後再看看第一張照片;它應該看起來相當不同。在以前是斑點狀混亂的地方,現在有清晰的物體,並且正在發生一些事情。

在你看到完整影像之前,這張雙色調影像看起來像一堆黑白斑點。
Richard Armstrong/EyeEm/Getty Images
我發現這個練習 remarkable 的地方在於,在你第二次檢查第一張影像時,到達你眼睛的感官訊號與你第一次看到它時完全沒有改變。所有改變的只是你的大腦對這些感官訊號成因的預測。你獲得了一個新的高層次感知期望,這改變了你意識到的東西。
如果你給人們展示許多雙色調影像,每張影像之後都跟著完整圖片,他們隨後可能會識別出很大一部分雙色調影像,儘管不是全部。在圖費爾的研究中,早期精神病患者在看過完整影像後,比健康的對照組更能識別雙色調影像。換句話說,易患幻覺與感知先驗對感知產生更強的影響有關。如果精神病中的幻覺依賴於感知先驗的過度加權,以至於它們壓倒了感官預測誤差,使感知最佳猜測脫離了它們在世界中的成因,那麼這正是預期的結果。
過去幾年的研究揭示了更多關於這個故事的資訊。在 2021 年的一項研究中,紐約大學的何碧玉及其同事讓神經外科患者觀看模糊影像,例如內克爾立方體,即使感官輸入保持不變,這些影像也會在兩種不同的外觀之間不斷翻轉。透過分析從患者大腦內部記錄的訊號,他們發現,當感知的外觀與患者的偏見一致時,資訊以自上而下、“由內而外”的方向流動得更強,如果感知預測在這種情況下很強,這是可以預期的。當感知的外觀與預先存在的偏見不一致時,資訊流以自下而上的方向流動得更強,這表明存在“預測誤差”訊號。這是在繪製受控幻覺的大腦基礎方面令人興奮的新進展。

感知轉變:觀看這張照片會改變一個人在雙色調影像中意識到的東西。
Richard Armstrong/EyeEm/Getty Images
在我的實驗室裡,我們採取了不同的方法來探索感知和幻覺的本質。我們沒有直接研究大腦,而是決定使用由 VR 大師鈴木圭介 (Keisuke Suzuki) 設計的獨特虛擬現實裝置來模擬過度活躍的感知先驗的影響。我們開玩笑地稱之為“幻覺機器”。
我們使用 360 度攝像頭,首先在星期二午餐時間錄製了蘇塞克斯大學校園繁忙廣場的全景影片片段。然後,我們透過基於谷歌 AI 程式 DeepDream 的演算法處理了這些片段,以生成模擬幻覺。發生的情況是,該演算法採用了一個所謂的神經網路——人工智慧的主力之一——並向後執行它。我們使用的網路經過訓練可以識別影像中的物體,因此如果你向後執行它,更新網路的輸入而不是輸出,那麼網路有效地將它“認為”存在的東西投射到影像上和影像中。它的預測壓倒了感官輸入,將感知最佳猜測的平衡傾向於這些預測。我們特定的網路擅長對不同品種的狗進行分類,因此影片異常地充滿了狗的存在。
許多透過 VR 頭顯觀看過處理後的片段的人評論說,這種體驗與其說是讓人聯想到精神病的幻覺,不如說是讓人聯想到迷幻之旅的 exuberantly 現象學。
最近,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實現了幻覺機器,以模擬不同型別的 altered 視覺體驗。透過擴充套件我們的演算法以包括兩個耦合的神經網路——一個“鑑別器網路”,很像我們原始研究中的那個,以及一個經過訓練可以重現(“生成”)其輸入影像的“生成器網路”——我們已經能夠模擬不同型別的幻覺。例如,我們已經模擬了帕金森病和某些形式痴呆症患者報告的複雜幻覺體驗;黃斑視力喪失後出現的有圖案的幾何幻覺,正如查爾斯·邦內綜合徵中發生的那樣;以及一系列類似迷幻藥的幻覺。我們希望透過更好地理解幻覺,我們也能夠更好地理解正常體驗,因為預測性感知是我們所有感知體驗的根源。
現實的感知
儘管幻覺機器無疑是 trippy 的,但體驗過它的人完全意識到他們所體驗到的不是真實的。事實上,儘管 VR 技術和計算機圖形技術飛速發展,但目前還沒有 VR 設定能夠提供足夠令人信服的體驗,以至於無法與現實區分開來。
這就是我們在蘇塞克斯設計新的“替代現實”裝置時所面臨的挑戰——當我們與薩爾瓦·基爾和裡克·馬查爾一起在教皇方濟各召集靜修會時,我們正在研究的裝置。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系統,志願者在其中體驗到一個環境是真實的——並相信它是真實的——而實際上它不是真實的。
基本想法很簡單。我們再次預先錄製了一些全景影片片段,這次是我們的 VR 實驗室內部,而不是外部校園場景。來到實驗室的人被邀請坐在房間中央的凳子上,戴上一個前面裝有攝像頭的 VR 頭顯。我們鼓勵他們環顧房間,並透過攝像頭看到房間的真實樣子。在某個時候,在沒有告訴他們的情況下,我們切換了 feed,以便頭顯顯示的不是即時的真實世界場景,而是預先錄製的全景影片。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繼續體驗他們所看到的是真實的,即使它現在是虛假的預先錄製。(這實際上在實踐中非常棘手——它需要仔細的色彩平衡和對齊,以避免人們注意到任何差異,從而讓他們意識到這種轉變。)
我發現這個結果令人著迷,因為它表明有可能讓人體驗到一個不真實的環境,使其感覺完全真實。僅此演示就為 VR 研究開闢了新的前沿:我們可以測試人們將體驗和相信什麼是真實的極限。它還使我們能夠研究將事物體驗為真實如何影響感知的其他方面。在我們的一個實驗中,我們旨在找出當人們相信他們所經歷的是真實的時,他們是否更難檢測到房間中意外的變化。這項研究因全球疫情而嚴重延遲,但我們希望當我們恢復工作時,我們將瞭解它是否可以支援這樣一種觀點,即感知事物為真實本身充當了一種高層次的先驗,可以實質性地塑造我們的感知最佳猜測,從而影響我們感知的內容。
現實的現實
我們的經驗世界可能不是真實的想法是哲學和科幻小說,以及深夜酒吧討論中持久不變的比喻。電影《駭客帝國》中的尼奧吃了紅色藥丸,墨菲斯向他展示了他認為的真實是如何精心設計的模擬,而真正的尼奧則俯臥在人體農場中,這是一個反烏托邦人工智慧的缸中之腦電源。牛津大學哲學家尼克·博斯特羅姆主要基於統計資料論證說,我們很可能生活在後人類時代建立的計算機模擬中。我部分不同意這種論點,因為它假設意識可以被模擬——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安全的假設——但它仍然是發人深省的。
儘管這些 chunky 形而上學主題很有趣,但它們可能無法解決。相反,我們在本文中一直在探討的是我們意識感知中外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其中這種外觀的一部分是事物本身看起來是真實的外觀。
這裡的核心思想是,感知是一個積極解釋的過程,旨在透過身體與世界進行適應性互動,而不是在頭腦中重建世界。我們感知世界的內容是受控幻覺,是對感官訊號最終不可知的成因的大腦最佳猜測。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在大多數時候,這些幻覺都被體驗為真實的。正如說唱歌手兼科學傳播者巴巴·布林克曼向我建議的那樣,當我們對我們的幻覺達成一致時,也許那就是我們所說的現實。
但我們並不總是達成一致,我們也不總是將事物體驗為真實的。患有分離性精神疾病(如現實解體或人格解體綜合徵)的人報告說,他們的感知世界,甚至他們自己,都缺乏真實感。某些型別的幻覺,包括各種迷幻幻覺,將不真實感與感知生動性結合在一起,就像清醒夢一樣。患有聯覺症的人始終有額外的感官體驗,例如在觀看黑色字母時感知顏色,他們認識到這些顏色不是真實的。即使是正常的感知,如果你直視太陽,你也會體驗到隨後的視網膜後像不是真實的。有很多這樣的方式讓我們體驗到我們的感知並非完全真實。
這對我的意義在於,我們大多數感知所具有的真實性屬性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這是我們大腦就其感官成因的貝葉斯最佳猜測達成一致的另一種表現。因此,人們可能會問它有什麼用途。也許答案是,包含真實屬性的感知最佳猜測通常比不包含真實屬性的感知最佳猜測更適合目的——也就是說,更能指導行為。當我們體驗到咖啡杯、迎面而來的公共汽車或我們伴侶的精神狀態是真實存在時,我們會對它們做出更適當的行為。
但這其中存在權衡。正如連衣裙錯覺所說明的那樣,當我們體驗到事物是真實的時,我們不太能夠理解我們的感知世界可能與他人的感知世界不同。(對服裝的不同感知的一種流行解釋認為,大部分清醒時間都在日光下度過的人看到它是白色和金色;主要暴露在人造光下的夜貓子看到它是藍色和黑色。)即使這些差異一開始很小,但隨著我們繼續以不同的方式收集資訊,選擇與我們個人新興的世界模型最一致的感官資料,然後根據這些有偏差的資料更新我們的感知模型,這些差異也可能會變得根深蒂固並得到加強。我們都從社交媒體的迴音室和我們選擇閱讀的報紙中熟悉了這個過程。我建議,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更深層次,即在我們社會政治信仰之下,一直到我們感知現實的結構。它們甚至可能適用於我們對自我的感知——成為“我”或成為“你”的體驗——因為成為自我的體驗本身就是一種感知。
這就是為什麼理解感知的建設性、創造性機制具有意想不到的社會相關性。也許一旦我們能夠欣賞散佈在這個星球數十億個感知大腦中的經驗現實的多樣性,我們將找到新的平臺,在這些平臺上建立共同的理解和更美好的未來——無論是在內戰各方之間、不同政黨的追隨者之間,還是在兩個合住一所房子並面臨洗碗問題的人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