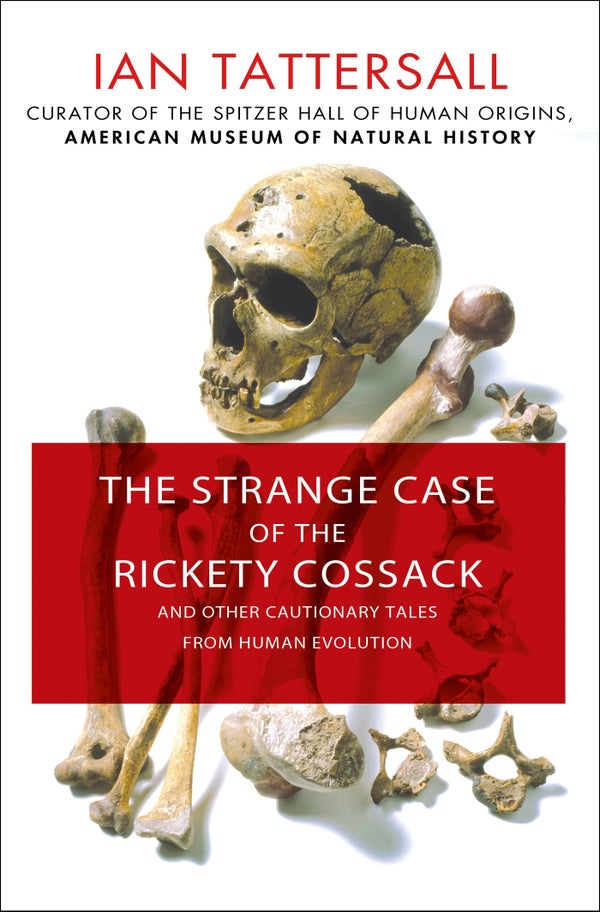摘自《搖搖晃晃的哥薩克人的怪異案例,以及人類進化中的其他警示故事》,作者:伊恩·塔特索爾。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2015年。版權所有©2015年。經許可轉載。(《大眾科學》是麥克米倫出版社的一部分。)
如果我必須選擇二十世紀古人類學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年,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 1950 年。當然,狄奧多西·多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早在 1944 年就將綜合進化論引入了古人類學領域,但當時正值戰時,似乎沒有人立即注意到。儘管如此,多布贊斯基對人類進化的看法指向了未來,在許多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就是他的文章發表後的那一年,也標誌著古人類學領域舊衛隊的沒落。1948 年,年邁但仍然勤奮的亞瑟·基思(Arthur Keith)出版了一本名為《人類進化新理論》的書,但這本書實際上並沒有兌現其標題。如果說它還被人記住的話,也是因為它含糊的反猶太立場。現在是新一代人物登上古人類學舞臺的時候了。
新一代生物人類學家中的領軍人物是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沃什伯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在哈佛接受了相當傳統的培訓,在 1940 年加入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後,他熱情地擁抱了新進化綜合論。正是透過這位精力充沛的皈依者,綜合進化論最終得以進入古人類學領域。1950 年,沃什伯恩(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和多布贊斯基共同組織了一場由長島冷泉港實驗室主辦的會議。這次國際會議以“人類的起源和進化”為宏大主題,彙集了包括綜合進化論的三位巨頭在內的眾多古人類學和相關科學領域的知名人士。因此,會議星光熠熠,但事後看來,其中一個貢獻不僅是會議上最受關注的演講,也是古人類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基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由古人類學家提出的。它是由鳥類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提出的。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邁爾在印刷版上和在演講中一樣有力——儘管他的出版版本帶有匆忙準備的所有痕跡——他毫不客氣地直言不諱。他毫不含糊地告知在場的大多數人,所有那些人族物種和屬所暗示的人類進化複雜圖景是完全錯誤的。首先,他宣稱,解剖學家區分它們的理論和形態標準都是完全不合適的。例如,如果你將一對果蠅物種放大到人類大小,它們看起來會比任何一對活著的靈長類動物的成員彼此之間的差異更大。化石人族的情況也是如此。
雖然這個比喻非常不相關,但它引起了觀眾的共鳴,他們不安地意識到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薄弱。它讓觀眾為邁爾更具體的說法做好了準備,即所謂的人族屬和物種的多樣性根本不存在。邁爾繼續說,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原則上,這種多樣性也不可能存在,因為物質文化的存在如此顯著地擴大了使用工具的人族的生態位,以至於世界上永遠不可能同時容納不止一種人類物種。
邁爾說,總而言之,這些各種實際的和理論的考慮因素決定了,所有已知的人類化石都應該被歸入一個單一的、不斷進化的多型譜系。而且,在這個譜系中,只有三個物種可以識別,而且每個物種都屬於一個屬:人屬。正如邁爾所認為的那樣,南方古猿(南方古猿)產生了直立人(包括爪哇猿人、北京猿人等等),而直立人又進化成了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事情就是這樣。
儘管如此——似乎他總覺得事情不可能如此簡單——邁爾明確詢問,為什麼與幾乎任何其他成功的哺乳動物科不同,人科沒有產生一系列物種。“是什麼,”他問道,“導致人族停止物種形成,儘管它在進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功?”他對這個優秀問題的巧妙回答,又讓他回到了“人類巨大的生態多樣性”。邁爾宣稱,人類已經“專注於非專業化”。更重要的是,“人類佔據的生態位比任何已知的動物都多。如果單一物種的人類佔據了所有為類似人屬生物開放的生態位,那麼很明顯,他不能物種形成”(我的重點)。邁爾還注意到關於“人類”的另一個非常特殊的事情,至少在他看來,這支援了他對人類系統發育的重構,即今天的無處不在的智人無限地倒退回過去:“人類顯然特別不能容忍競爭者……入侵的克羅馬農人消滅尼安德特人只是一個例子。”
邁爾在他的演講結束時接受了提問。當被問到(當然不是古人類學家)化石人族之間發現的顯著形態差異如何才能被壓縮到一個屬中時,他巧妙地回答說,“由於沒有絕對的屬特徵,因此不可能在純粹的形態學基礎上定義和劃分屬。”當時沒有人覺得應該對此提出質疑。沒有人指出顯而易見的事實:形態學是古生物學家唯一可以使用的東西,而且,雖然他可能在技術上正確地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屬特徵”——無論這到底意味著什麼——但化石屬必須從它們的形態學中識別出來。也沒有人認為,不能容忍競爭可能僅僅是智人的一個特徵,使其與即使是最親近的親戚區分開來。也沒有人質疑邁爾的其他任何廣泛而高度推測性的宣告——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他具有挑釁性的評論發表後的幾年裡。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如此順從地接受他對該領域的各種批評的原因是,邁爾的猛烈抨擊使古人類學家中極少數的精英人士陷入了某種早就應該進行的內省。他們最終開始意識到,他們及其前輩一直在一個理論真空狀態下運作,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人——或許除了弗蘭茨·魏登賴希(Franz Weidenreich)——曾費心思考過可能支援他們關於化石的故事的程序,或者他們的運作假設如何與已知的大自然其他部分是如何進化的相適應。而邁爾,這位自我肯定的綜合進化論的架構師,對他們的科學進行了雄辯而全面的分析:該分析將對形態學的認可與對進化過程、系統學、物種形成理論和生態學的考慮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關鍵因素都是古人類學家現在開始感到內疚地基本上忽略的——從而產生了關於人類進化的連貫而有力的論述。在沒有思想退路的情況下,他們除了屈服還能做什麼?在這種令人不安的認識論境況中,幾乎沒有人介意邁爾的設想遠非牢固地紮根於化石本身的研究中。
對這種瞬間投降的主要英語國家例外是羅伯特·布魯姆(Robert Broom)的年輕助手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他詳細指出,纖細型和粗壯型南方古猿之間的形態異質性——以及他看到的一些南非和早期爪哇材料之間的一些相似性——表明,在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至少存在兩個共存的人族譜系。儘管邁爾勉強承認羅賓遜確實有道理,但這一承認被埋藏在一份古人類學家不讀的期刊上發表的一堆註釋中,一旦羅賓遜指出了這一點,他的大多數同事都同意,粗壯型南方古猿最好被排除在邁爾的線性方案之外。屬名南方古猿繼續用於所有纖細型南方古猿(對一些古人類學家,主要是羅賓遜來說,粗壯分支繼續被稱為傍人屬)。羅賓遜自己也繼續使用“湯加普人”(他的引號)這個名字來稱呼來自斯沃特克蘭斯(Swartkrans)的神秘、非常輕巧的人族化石——以及從斯泰克方丹(Sterkfontein)的一個區域來的,到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該區域也開始生產一些粗糙的石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