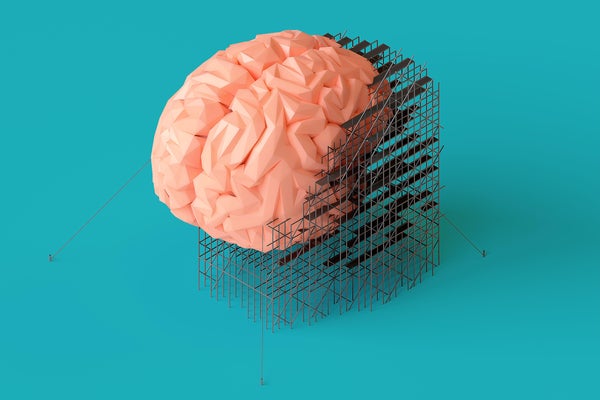人類大腦適應和改變的能力,即神經可塑性,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科學界和公眾的想象力。這是一個帶來希望和魅力的概念,特別是當我們聽到一些非凡的故事時,例如,失明人士發展出增強的感官,使他們能夠僅憑回聲定位在雜亂的房間中穿梭,或者中風倖存者奇蹟般地重新獲得曾經認為喪失的運動能力。
多年來,諸如失明、耳聾、截肢或中風等神經系統挑戰導致大腦功能發生劇烈而顯著變化的觀點已被廣泛接受。這些敘事描繪了一個高度可塑的大腦,它能夠進行戲劇性的重組,以補償喪失的功能。這是一個吸引人的概念:大腦為了應對損傷或缺陷,會釋放未開發的潛力,重新佈線以實現新的能力,並重新利用其區域以實現新的功能。這種想法也可能與廣泛流傳的、但本質上是錯誤的迷思有關,即我們只使用了大腦的 10%,這表明我們有大量的神經儲備可以在需要時依靠。
但是,這種對大腦適應性重組能力的描述有多準確呢?我們真的能夠在受傷後利用未使用的腦力儲備嗎?或者,這些引人入勝的故事是否導致了對大腦真正可塑性的誤解?在我們為 eLife 期刊撰寫的論文中,我們深入探討了這些問題的核心,分析了經典研究,並重新評估了關於皮質重組和神經可塑性的長期以來的信念。我們的發現為大腦如何適應變化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新視角,並挑戰了一些關於其靈活恢復能力的流行觀念。
支援科學新聞事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事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這種迷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神經科學家 邁克爾·默岑尼奇 (Michael Merzenich) 的開創性工作,並透過諾曼·多伊奇 (Norman Doidge) 的《改變自身的大腦》等書籍而廣為人知。默岑尼奇的見解建立在諾貝爾獎得主神經科學家大衛·休伯爾 (David Hubel) 和託斯滕·維厄塞爾 (Torsten Wiesel) 的有影響力的研究基礎上,他們探索了小貓的眼優勢。他們的實驗包括縫合小貓的一隻眼瞼,然後觀察視覺皮層由此產生的變化。他們發現,視覺皮層中通常會對閉上的眼睛的輸入做出反應的神經元,開始更多地對睜開的眼睛做出反應。眼優勢的這種轉變被認為是大腦能夠重組其感覺處理通路以響應早期生活中感覺體驗改變的明確跡象。然而,當休伯爾和維厄塞爾測試成年貓時,他們無法複製這些眼偏好的深刻轉變,這表明成年大腦的可塑性要差得多。
默岑尼奇的工作表明,即使是成年大腦也不是曾經認為的那樣不可改變的結構。在他的實驗中,他細緻地觀察到,當猴子的手指被截肢後,最初代表這些手指的皮質感覺圖譜如何變得對相鄰的手指產生反應。在他的描述中,默岑尼奇描述了皮質中的區域如何擴張以佔據或“接管”先前代表被截肢手指的皮質空間。這些發現被解釋為證據,表明成年大腦確實可以重新佈線其結構以響應感覺輸入的改變,這個概念既令人興奮,又充滿了增強大腦恢復過程的潛力。
這些開創性的研究,以及許多其他關注感覺剝奪和腦損傷的研究,強調了一個稱為大腦重繪的過程,即大腦可以重新分配一個大腦區域(例如,屬於某個手指或眼睛的區域)以支援不同的手指或眼睛。在失明的情況下,人們認為視覺皮層被重新用於支援失明人士經常表現出的增強的聽覺、觸覺和嗅覺能力。這種想法超越了分配給特定功能的現有大腦區域中的簡單適應或可塑性;它暗示了大腦區域的全面重新利用。然而,我們的研究揭示了一個不同的故事。
在好奇心和懷疑主義的共同驅動下,我們選擇了神經科學領域中最典型的 10 個重組示例,並從全新的角度重新評估了已發表的證據。我們認為,在成功的康復案例中經常觀察到的,不是大腦在以前不相關的區域創造新功能。相反,更多的是利用自出生以來就存在的潛在能力。這種區分至關重要。這表明,大腦適應損傷的能力通常不涉及徵用新的神經領地用於完全不同的目的。例如,在默岑尼奇的猴子研究和休伯爾與維厄塞爾的小貓研究案例中,更仔細的檢查揭示了大腦適應性的更細緻入微的圖景。在前一種情況下,皮質區域並沒有開始處理全新的資訊型別。相反,即使在截肢之前,被檢查的大腦區域中也已經準備好利用其他手指的處理能力。科學家們只是沒有過多地注意到它們,因為它們比即將被截肢的手指中的處理能力弱。
同樣,在休伯爾和維厄塞爾的實驗中,小貓眼優勢的轉變並不代表創造了新的視覺能力。相反,在現有的視覺皮層中,對另一隻眼睛的偏好進行了調整。最初適應閉上眼睛的神經元並沒有獲得新的視覺能力,而是增強了對睜開眼睛輸入的反應。我們也沒有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天生失明者的視覺皮層或中風倖存者未受傷的皮層發展出原本自出生以來就不存在的新穎功能能力。
這表明,通常被解釋為大腦透過重新佈線進行戲劇性重組的能力,實際上可能是其完善現有輸入能力的一個例子。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大腦更有可能增強或修改其預先存在的結構,而不是完全重新利用區域來執行新任務。對神經可塑性的這種重新定義意味著,大腦的適應性並非以無限的改變潛力為標誌,而是以戰略性和高效地利用其現有資源和能力為標誌。雖然神經可塑性確實是我們大腦真實而強大的屬性,但其真實性質和程度比流行敘事中經常描繪的廣泛而全面的變化更受約束和具體。
那麼,失明人士如何僅憑聽覺導航,或者中風倖存者如何重新獲得運動功能呢?我們的研究表明,答案不在於大腦進行戲劇性重組的能力,而在於訓練和學習的力量。這些才是神經可塑性的真正機制。對於失明人士發展敏銳的回聲定位技能或中風倖存者重新學習運動功能,需要進行強化、重複的訓練。這種學習過程證明了大腦非凡但受約束的可塑效能力。這是一個緩慢的、漸進的旅程,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和練習。
我們對先前被描述為“重組”的許多案例進行了廣泛分析,表明在這個大腦適應的旅程中沒有捷徑或快速通道。快速釋放隱藏的大腦潛力或利用大量未使用的儲備的想法更多的是一廂情願,而非現實。瞭解大腦可塑性的真實性質和侷限性至關重要,這既是為了為患者設定切合實際的期望,也是為了指導臨床醫生進行康復治療。大腦的適應能力雖然令人驚歎,但受到內在約束的限制。認識到這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每個康復故事背後的艱苦工作,並相應地調整我們的策略。通往神經可塑性的道路絕非神奇轉化的領域,而是一條奉獻、堅韌和循序漸進的道路。
這是一篇觀點和分析文章,作者或作者表達的觀點不一定代表《大眾科學》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