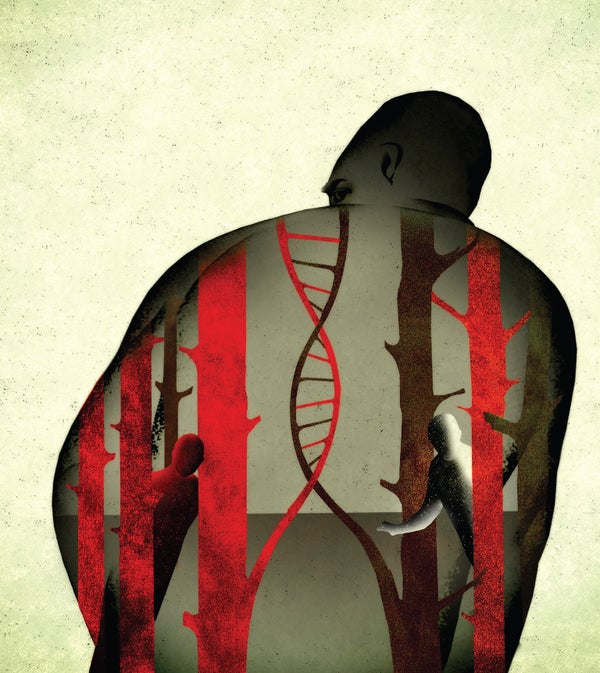今天很難想象,但在人類進化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地球上都存在著多種類人物種。就在4萬年前,智人還與包括尼安德特人和矮小的弗洛勒斯人在內的幾種同類物種共同生活。幾十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爭論智人究竟是如何起源併成為最後倖存的人類物種的。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20世紀80年代的基因研究,一種理論脫穎而出,成為明顯的領先者。這種觀點認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並擴充套件到舊世界的其他地區,完全取代了現有的古老群體。這種新穎的形式究竟是如何成為地球上最後的人類物種仍然是個謎。也許入侵者殺死了他們遇到的本地人,或者在陌生人的地盤上擊敗了他們,或者僅僅是以更高的速度繁殖。無論如何,新來者似乎在沒有與競爭對手雜交的情況下消滅了他們。
近期非洲起源說模型,正如其名稱所示,在過去30年左右的時間裡,基本上一直是現代人類起源的正規化。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它是錯誤的。DNA測序技術的最新進展使研究人員能夠大幅擴大從活人和已滅絕物種收集資料的規模。使用日益複雜的計算工具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表明,我們的家族史故事並不像大多數專家認為的那麼簡單。事實證明,今天的人們攜帶從尼安德特人和其他古人類那裡繼承的DNA,這表明早期智人曾與這些其他人種交配,併產生了能夠將這種遺傳遺產傳遞數千代的有生育能力的後代。除了顛覆關於我們起源的傳統觀念外,這些發現還推動了對雜交程度、發生雜交的地理區域以及現代人類是否顯示出從我們史前表親的任何基因貢獻中獲益的跡象的新探索。
神秘的起源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報道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為了充分理解這些最新的基因發現對科學家理解人類進化產生的影響,我們必須回顧20世紀80年代,當時關於智人崛起的爭論正酣。透過檢查化石資料,古人類學家一致認為,我們屬的早期成員直立人大約在兩百萬年前起源於非洲,並在此後不久開始從非洲大陸擴充套件到舊世界的其他地區。然而,他們對智人的祖先如何從那種古老的形式過渡到我們現代的形式(具有圓形的顱腔和精巧的骨骼——這些特徵大約在19.5萬年前出現在化石記錄中)存在分歧。
所謂的“多地起源說”模型的支持者,由密歇根大學的米爾福德·H·沃爾波夫及其同事提出,他們認為這種轉變在非洲、歐亞大陸和 Oceania 各地的古老人群中逐漸發生,原因是遷徙和交配的結合使有益的現代特徵在所有這些人群中傳播開來。在這種情景中,儘管所有現代人類在過渡結束時都具有特定的身體特徵,但一些從古老祖先那裡繼承的具有區域特徵的特徵仍然存在,這可能是因為這些特徵幫助人群適應當地環境。“多地起源說”模型的一個變體,由現在在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的弗雷德·史密斯提出,稱為“同化模型”,承認來自非洲的人群對現代特徵的貢獻更大。
相比之下,“替代模型”(也稱為“走出非洲模型”等),包括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克里斯托弗·斯廷格在內的支持者認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作為一個獨特的物種起源於一個地方——撒哈拉以南非洲——並隨後完全取代了各地所有的古人類,而沒有與他們雜交。德國漢堡大學的 Günter Bräuer 提出的一個較寬鬆的理論版本——“雜交模型”——允許在這些現代人類和他們在向新土地推進時遇到的古老群體之間偶爾產生雜交後代。
僅憑化石證據,這場辯論似乎陷入了僵局。遺傳學改變了這種局面。隨著DNA技術的出現,科學家們開發出透過分析當代人類群體中的遺傳變異並用其重建單個基因的進化樹來拼湊過去的方法。透過研究基因樹,研究人員可以推斷出給定基因的所有變異的最後共同祖先存在的時間和地點,從而深入瞭解祖先序列的起源人群。
在1987年發表的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艾倫·C·威爾遜及其同事報告說,線粒體(細胞的能量產生成分)中發現的DNA的進化樹可以追溯到大約2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人群中的一位女性祖先。(線粒體DNA,或mtDNA,從母親傳給孩子,在祖先研究中被視為單個基因。)這些發現符合“替代模型”的預期,隨後的核DNA小片段研究,包括父系遺傳的Y染色體,也是如此。
對“替代模型”的進一步基因支援來自十年後,當時現在在德國萊比錫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所的斯萬特·帕博及其同事成功地從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並分析了一段mtDNA。研究發現,尼安德特人的mtDNA序列與當代人類的mtDNA序列不同,並且沒有跡象表明他們之間存在雜交——隨後的對其他尼安德特人樣本的mtDNA研究證實了這一結果。

來源:MICHAEL F. HAMMER;圖表:Jen Christiansen
對於許多研究人員來說,這些古代mtDNA的發現為“多地起源說”和“同化模型”敲響了喪鐘。然而,其他人則認為他們的推理存在一個根本問題。在基因組的任何單個獨立區域(如mtDNA)中缺乏雜交訊號,並不一定意味著基因組的其他區域也缺乏雜交跡象。此外,即使確實發生了雜交,任何特定的基因組區域在測試中都可能缺乏雜交跡象,因為來自其他物種的DNA(滲入的DNA)如果對智人沒有提供生存優勢,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偶然地從基因庫中消失。
因此,解決智人是否與尼安德特人等古老物種雜交的最佳方法是比較他們基因組的許多區域,或者理想情況下,是他們的整個基因組。然而,即使在古人類的此類資料可用之前,一些早期對現代人類DNA的基因研究就逆流而上,發現了與“替代模型”相悖的資料。一個明顯的例子來自2005年由丹尼爾·加里根領導的一項研究,當時加里根是我的實驗室的博士後研究員。加里根研究了來自X染色體非功能區域(稱為RRM2P4)的DNA序列。對其重建樹的分析表明,該序列的起源地不是非洲,而是大約150萬年前的東亞,這意味著該DNA來自一個與最初來自非洲的智人混雜的亞洲古老物種。同樣,同年,我們的實驗室在X染色體的另一個非功能區域Xp21.1中發現了變異,其基因樹顯示出兩個不同的分支,這兩個分支可能在完全隔離的情況下進化了大約一百萬年。其中一個分支據推測是由非洲古老物種引入到解剖學上的現代人群中的。因此,RRM2P4和Xp21.1的證據暗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曾與來自亞洲和非洲的古人類交配,而不是簡單地在沒有雜交的情況下取代他們。
我們的古老DNA
最近,測序技術的進步使科學家能夠快速測序整個核基因組——包括尼安德特人等已滅絕人類的核基因組。2010年,帕博的研究小組報告說,他們根據來自克羅埃西亞的幾個尼安德特人化石的DNA,重建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組的大部分。與該團隊的預期相反,這項工作表明,尼安德特人對現代人類基因庫做出了微小但意義重大的貢獻:如今的非非洲人在其基因組中平均表現出1%到4%的尼安德特人貢獻。為了解釋這一結果,研究人員提出,尼安德特人與所有非非洲人的祖先之間的雜交可能發生在兩個群體在中東重疊的有限時期,大約在8萬到5萬年前。
緊隨尼安德特人基因組宣佈之後,帕博的團隊揭示了一個更令人震驚的發現。研究人員從西伯利亞阿爾泰山脈丹尼索瓦洞穴中發現的一塊大約4萬年前的手指骨中獲得了一個mtDNA序列。儘管研究人員無法從骨骼的解剖結構中確定它代表什麼物種,但基因組序列表明,該個體屬於一個種群,該種群與尼安德特人的親緣關係略高於尼安德特人或尼安德特人與我們物種的親緣關係。此外,在將丹尼索瓦序列與現代人群中的對應序列進行比較後,該團隊在美拉尼西亞人、澳大利亞原住民、波利尼西亞人以及西太平洋地區的一些相關群體中發現了一個來自類似丹尼索瓦人的種群的大量DNA——貢獻率為1%到6%——但在非洲人或歐亞人中沒有發現。
為了解釋這種日益複雜的DNA共享模式,研究人員提出了現代人類和古老人群之間的兩次雜交事件:第一次是與尼安德特人的雜交,發生在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最初從非洲遷徙出來時;第二次是與類似丹尼索瓦人的雜交,發生在這些最初移民的後代前往東南亞時。然而,最新的證據支援幾次額外的雜交事件——例如,近東早期現代非非洲人之間的雜交,將基因引入了一部分尼安德特人的祖先,以及不同古老人群之間基因交換的其他情況。證據還表明,至少還有一次額外的事件增加了尼安德特人對現在居住在東亞的當代人群的貢獻。先前推斷的來自類似丹尼索瓦人的種群到美拉尼西亞現代人群的基因流,現在被認為在當今東亞和美洲原住民人群中留下了更廣泛的DNA特徵。
儘管關於人類進化中雜交的討論通常集中在歐洲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與尼安德特人或亞洲其他古老形式的交配上,但物種間交配的最大機會本應在非洲,在那裡,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和各種古老形式共存的時間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長得多。不幸的是,非洲熱帶雨林的熱帶環境不利於古代遺骸中DNA的儲存。在沒有非洲古代DNA序列可供參考的情況下,遺傳學家目前只能在現代非洲人的基因組中搜尋古老雜交的跡象。
為此,我的實驗室的謝炳勳旨在測試非洲古老人類和現代人類之間雜交的假設,而無需使用來自古老人類化石的古代DNA。我們分析了來自兩個當代中非俾格米狩獵採集人群的全基因組序列資料,並鑑定了250多個具有強烈古老DNA訊號的遺傳位點。我們的推論為非洲未鑑定的古老形式與解剖學上的現代非洲人之間的一次以上混合事件提供了證據,其中至少一次此類事件發生在過去3萬年內。
另一個關於非洲古老雜交的基因線索來自一項研究,該研究針對一位居住在南卡羅來納州的非裔美國男子的異常Y染色體序列,他的DNA已提交給一家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基因檢測公司進行分析。他特殊的變異以前從未見過。透過將他的Y序列與其他人類以及黑猩猩的Y序列進行比較,我的團隊確定他的序列代表一個以前未知的Y染色體譜系,該譜系增加了當代Y染色體共同祖先的年齡。然後,我們搜尋了一個包含近6000個非洲Y染色體的資料庫,並識別出11個匹配項——所有這些匹配項都來自居住在喀麥隆西部一個非常小區域的男性。最近,費爾南多·門德斯及其斯坦福大學的合作者將最近Y染色體共同祖先的時間重新估計為27.5萬年,這比解剖學上的現代化石在非洲出現的時間要早得多。在當代人中存在這種非常古老的譜系,這可能是智人與非洲中西部未知古老物種雜交的一個跡象。

來源:“基因組資料揭示了人類的複雜構成”,作者:ISABEL ALVES 等人,發表於PLOS GENETICS,第8卷,第7期;2012年7月19日;地圖:XNR Productions
最近,化石記錄也為非洲內部雜交的可能性提供了支援。就在2011年我們發表研究結果後不久,一組在奈及利亞Iwo Eleru遺址工作的古生物學家重新分析了一些遺骸,這些遺骸表現出介於古老人類和現代人類之間的顱骨特徵,並確定它們的年代僅為13,000年前——遠在解剖學上的現代智人首次出現之後。這些結果,以及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伊尚戈遺址的類似發現,表明非洲解剖學現代性的進化可能比現代人類起源的任何主要模型所設想的要複雜得多。要麼是古老人類在近代與現代人類並肩生活,要麼是同時具有現代和古老特徵的人群在數千年中雜交。
有益的貢獻?
對從古老祖先那裡繼承的DNA區域的詳細研究將有助於解決雜交(以及隨後的遺傳變異)是否為早期智人帶來了適應性優勢的問題。事實上,現在有幾個例子涉及與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組密切相關的古老基因區域,這些區域在當代人類群體中以特別高的頻率被發現。大約10%的歐亞大陸和 Oceania 人攜帶STAT2的尼安德特人類似變體,該變體參與人體抵抗病毒病原體的第一道防線。有趣的是,它在美拉尼西亞的發生頻率比在東亞高出大約10倍。分析表明,該DNA片段是透過積極的自然選擇(即因為它有助於生殖成功或生存)而不是僅僅透過偶然機會而上升到高頻率的,這意味著它使美拉尼西亞的解剖學上的現代人群受益。發現含有增強免疫力功能的基因的古老貢獻並不奇怪。很容易想象,當人類祖先從非洲擴充套件到新的棲息地時,獲得一種適應於抵禦非非洲環境中病原體的基因變體將立即使他們受益。
共享基因變體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可能涉及EPAS1基因,該基因參與人體對低氧水平的反應。最初的研究表明,該基因的DNA序列變異賦予了藏族人對高海拔的適應能力;隨後發現這些變異是從類似丹尼索瓦人的祖先那裡繼承來的。適應性滲入的遺傳變異的其他例子包括參與頭髮和皮膚生物學以及脂質代謝的基因。有趣的是,從尼安德特人那裡繼承的遺傳變異可能會增加人類疾病的風險,包括與精神、神經、免疫和皮膚病學疾病相關的疾病。
鑑於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解剖學上的現代智人與非洲境內外的古老人類之間存在雜交,“替代模型”不再站得住腳。現代和古老的人屬物種能夠產生有活力的雜交後代。因此,古老的形式可能會滅絕,但仍然在現代人類基因組中留下它們的遺傳足跡。儘管如此,今天的人們的基因組似乎主要來自非洲祖先——來自古老歐亞人的貢獻小於“多地起源說”或“同化模型”的預測。
許多研究人員現在傾向於 Bräuer 的“雜交模型”,該模型認為智人與古老物種之間的交配僅限於少數孤立的例子。但鑑於目前非洲境內外的情況,我更傾向於雜交在我們物種歷史上更為普遍的模型。鑑於非洲化石記錄的複雜性,該記錄表明,在Roughly 20萬到3.5萬年前,從摩洛哥到南非的廣闊地理區域內,生活著各種具有古老和現代特徵的過渡性人類群體,我傾向於一種涉及從古老到現代過渡期間的物種間交配的模型。有時被稱為“非洲多地起源說”,這種情況允許我們解剖學上現代的一些特徵可能是從過渡形式中繼承下來的,然後在它們滅絕之前。在我看來,“非洲多地起源說”模型最好地解釋了迄今為止的基因和化石資料。
在科學家能夠充分評估現代人類起源的這個模型之前,我們需要更好地瞭解哪些基因編碼解剖學上的現代特徵,並破譯它們的進化史。對古老和現代基因組的進一步分析應有助於研究人員查明混合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以及進入現代人類基因庫的古老基因是否使獲得它們的人群受益。這些資訊將幫助我們評估以下假設:與很好地適應當地環境的古老人群雜交,為智人賦予了促進其崛起為全球卓越地位的特徵。透過偶爾的物種間交配來共享基因是許多動植物物種中進化新事物出現的一種方式,因此,如果同樣的過程發生在我們自己的過去,也不足為奇。
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仍然存在。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現代人類的根源不僅可以追溯到非洲的單一祖先種群,還可以追溯到整個舊世界的種群。儘管古老人類經常被視為現代人類的競爭對手,但科學家現在必須認真考慮他們可能是智人成功的秘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