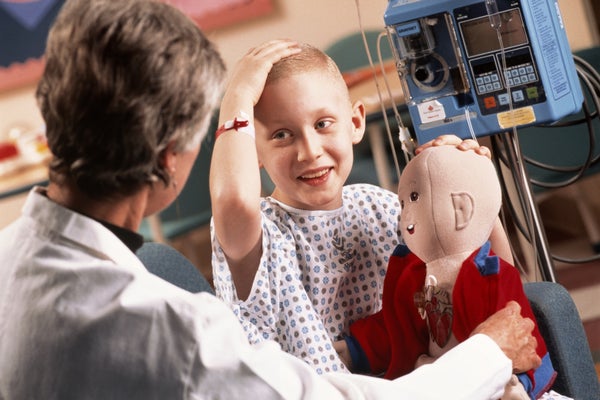九年前的一個星期一下午,密歇根州德威特市一位牧師的妻子和三個孩子的母親桑德拉·史密斯得知自己患有侵襲性乳腺癌。然而,真正糟糕的訊息會在當週晚些時候打擊這個家庭。
起初他們以為他們最小的六歲兒子安德魯只是得了流感。然後他開始嘔吐。他還出現了面部下垂,步態似乎也不穩。史密斯回憶說,即使他們衝到急診室,她還在想他們是否“小題大做”了。
事實遠非如此。MRI 掃描顯示安德魯的腦幹中有一大片腫脹區域——清楚地表明他患有一種致命的兒童癌症,這種癌症通常在四到十歲之間發病,並且大多數患者在確診後一年內死亡。與史密斯乳房中不受控制分裂的細胞不同,她兒子的癌症,稱為瀰漫性內生性腦橋神經膠質瘤 (DIPG),無法透過手術或傳統化療來對抗。在 DIPG 中,惡性細胞與控制呼吸和心率等關鍵功能的區域中的正常腦組織纏繞在一起,使得外科醫生無法切除。在 200 多項藥物試驗中,沒有任何方法比放射療法更有效,而放射療法本身只能將 DIPG 兒童的生命延長几個月。安德魯比“典型”的 DIPG 患者活得更久,在確診後兩年多後去世,於 2009 年底去世。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DIPG 約佔兒童腦部和脊髓腫瘤的 10%。它是第二常見的兒童腦腫瘤,也是兒童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DIPG 的治療方案和生存率在 40 年內沒有改變——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最新報告,這種困境可能促使腦癌超越白血病成為美國最致命的兒童惡性腫瘤。
然而,今天,由於基因測序方法的進步以及安德魯等因這些疾病失去孩子的家庭捐贈的腫瘤組織,DIPG 和其他兒童腦癌的前景看起來更加光明。近年來,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利用患者的腫瘤組織生成了數十種細胞系和小鼠模型,以研究兒童腦癌的基礎生物學。時機已經成熟。在精準醫學的曙光中,精準醫學旨在為個體患者定製疾病治療,遺傳學和基礎科學發現表明,為什麼過去的試驗可能會失敗,並正在指導未來和正在進行的努力,以確定針對這些毀滅性疾病的有效療法。
米歇爾·蒙傑是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病學助理教授,她大約在 2002 年作為那裡的醫學博士/博士生首次接觸到 DIPG。蒙傑說,她與她的臨床導師一起照顧一位因 DIPG 而瀕臨死亡的九歲女孩,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種我們不知道如何治療的疾病”。“我感覺與這位患者非常親近,並且因自己無能為力而感到沮喪。”
那時,關於 DIPG 的分子資料很少。沒有動物模型。沒有細胞培養物。生成此類研究工具需要患者的腫瘤樣本。然而,由於 MRI 掃描可以可靠地診斷典型的 DIPG,並且獲取腦幹組織並非易事,因此很少進行活檢。蒙傑說,由於實驗室中可供研究的腫瘤組織非常少,DIPG 的研究進展停滯了幾十年。
2007 年,法國的一個外科醫生團隊報告稱,他們使用立體定向技術安全地從 24 名 DIPG 兒童身上獲取了活檢樣本,該技術使用計算機成像來引導針頭放置。這項研究激發了達納-法伯/波士頓兒童癌症和血液疾病中心腦腫瘤中心臨床主任、兒科神經腫瘤學家馬克·基蘭長期以來的努力,他多年來一直在美國推動 DIPG 活檢,但最初沒有成功。
那時,技術進步使得從微小的組織碎片中讀取 DNA 序列成為可能,這進一步推動了現在已證明在訓練有素的人手中是安全的一項棘手的外科手術。波士頓團隊開始為患者提供在診斷和復發時活檢的腫瘤的基因組測序,以“瞭解腫瘤是如何進化的,並將適當的藥物重新定向到腫瘤”,基蘭說。腫瘤圖譜可以幫助確定哪些患者可能從一種稱為靶向療法的新型藥物中獲益,這種療法靶向腫瘤中的特定蛋白質,而不僅僅是殺死任何分裂的細胞。靶向療法是精準醫學的基石。
自 2009 年以來,達納-法伯的研究人員對近 1,000 名兒童的腦腫瘤進行了測序。在被歸類為低級別神經膠質瘤的兒童中,高達 10% 的兒童在一種名為BRAF的基因中發生突變,這種突變在某些成人皮膚腫瘤中也可見。幾年前,來自歐洲和北美的 32 名患有BRAF陽性神經膠質瘤的兒童參加了一項達拉非尼臨床試驗,達拉非尼是一種靶向療法,已獲准用於患有這種突變的黑色素瘤患者。在本月早些時候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基蘭報告稱,32 名兒童中有 23 名在使用 BRAF 抑制藥物後病情有所改善——這種反應率非常高,以至於他的團隊正在為攜帶這種突變的試驗參與者提供持續治療。
2012 年,基蘭和合作者啟動了一項臨床試驗,對 DIPG 兒童的腫瘤進行活檢,檢測幾種分子標記物,並根據結果分配四種治療策略之一。兩年前,由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兒科神經腫瘤學家薩賓·穆勒領導的團隊啟動了另一項 DIPG 試驗。這項研究使用更復雜的技術,全外顯子組測序來探測患者的腫瘤,該技術掃描基因組的整個蛋白質編碼部分,而不僅僅是檢查預先指定的標記物。根據每位患者的腫瘤圖譜,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團隊提出了多達四種似乎合適的藥物。還需要一到兩年才能看到這些藥物是否有幫助。
儘管精準醫學對某些個體有幫助,但它很昂貴,一些科學家懷疑它可能只會適度改善一般癌症患者的生活。單個腫瘤內的細胞可以獲得不同的突變,因此,“即使存在有效的藥物,它也可能益處有限,因為在腫瘤其他部分活躍的分子通路將導致來自不同腫瘤細胞克隆的腫瘤生長,”研究人員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9 月份發表的評論中寫道。並且在沒有針對 DIPG 的特定批准藥物的情況下,關於活檢是否為這些患者提供真正益處的爭論仍在繼續。
一些實驗室採取了一種爭議較少的 DIPG 樣本獲取途徑——從同意在孩子去世後捐贈腫瘤組織的家庭那裡獲得遺贈。密歇根州的母親史密斯在 2008 年春天透過一個線上 DIPG 支援小組瞭解了遺贈,那是她的兒子安德魯被診斷出患病半年後。史密斯回憶說,閱讀到死後取出大腦並捐贈組織的帖子“對我來說太可怕了”。“但我明白[如果沒有患者樣本],研究人員就無法研究這種腫瘤。”她在她和她的朋友主持的一個 DIPG 家庭雅虎群組中分享了這個想法。2008 年 11 月,雅虎列表中的一位母親驚慌失措地打電話給史密斯。她的女兒已進入彌留之際,家人想捐贈她的腫瘤組織,但尚未做出安排。
屍檢組織捐贈在後勤方面具有挑戰性。一旦孩子去世,需要在六小時內取出大腦,並將腫瘤組織放入無菌管中。然而,患者往往死在家中,遠離醫療中心,有時在半夜或節假日期間的暴風雪中。一些實驗室從靠近孩子居住地的組織回收團隊預訂隨叫隨到服務。為了產生最大的影響,樣本應該送到可以在同一天接收和處理它們的實驗室。
在史密斯幫助其他家庭安排腫瘤捐贈的過程中,她結識了一些頂尖的 DIPG 研究人員,包括蒙傑,蒙傑剛剛研究出一種方法培養屍檢組織中的細胞,並使用這些細胞建立 DIPG 小鼠模型。2011 年 7 月,史密斯得知一位名叫麥肯納的七歲女孩正在與 DIPG 作鬥爭。蒙傑和史密斯與這個家庭合作,“確保我們在時機到來時擁有所需的檔案”,麥肯納的母親克里斯汀·韋策爾說,她是一位加利福尼亞州亨廷頓海灘的高中教師。
麥肯納突然衰弱,家人決定在她去世後一小時內捐贈她的腫瘤組織。韋策爾說,儘管很痛苦,但這個決定“出乎意料地令人欣慰”。“這是一種反擊偷走我們女兒的怪物的方式。”韋策爾一家此後幫助其他 DIPG 家庭進行腫瘤捐贈,並建立了一個基金會,以提高人們對兒童腦癌的認識並資助相關研究。該基金會支付向蒙傑實驗室捐贈組織的費用,併為一名技術人員支付工資,該技術人員維護實驗室的 DIPG 培養物,並將樣本運送到世界各地約 80 個實驗室。蒙傑說,支援力度各不相同,但通常約為每年 10 萬美元。
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神經生物學和腦腫瘤專案負責人之一的神經生物學家蘇珊娜·貝克說,屍檢組織捐贈“將研究領域從一個由於缺乏研究材料而難以接近的問題,轉變為對 DIPG 基因組進行前所未有的分析”。
貝克、基蘭以及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和其他地方的其他研究人員發表的一系列論文揭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發現。儘管 DIPG 具有與其他腦癌不同的基因特徵,但這種罕見的兒童腫瘤有一個共同的顯著特徵:幾乎80% 的腫瘤在編碼一種名為組蛋白 H3 的蛋白質的基因中發生突變。組蛋白就像 DNA 纏繞在其上的線軸。組蛋白是表觀遺傳學——研究基因開啟或關閉的生物學機制——的關鍵參與者,它會影響酶訪問 DNA 的容易程度,這些酶將遺傳密碼翻譯成工作蛋白質。“組蛋白 H3 非常基礎……我認為許多癌症都會發生這些突變,”貝克說。然而,它們似乎是 DIPG 和兒童中約三分之一的非腦幹腫瘤所獨有的。
這些基因洞見來得正是時候。當一些實驗室忙於分析 DIPG 腫瘤細胞的全基因組測序資料時,另一些實驗室則在細胞培養物和小鼠模型中測試潛在藥物,這些細胞培養物和小鼠模型是從患者腦腫瘤樣本中生成的。其想法是在實驗室中仔細審查化合物,然後再選擇哪些化合物進行時間更長、成本更高的臨床試驗。這種方法並非革命性的。蒙傑說,一般來說,這是“你進行醫學研究的方式”。但對於 DIPG 來說,“幾十年來我們一直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一直沒有細胞培養物或模擬該疾病的實驗小鼠。
情況在 2010 年有所改善,當時時任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查爾斯·凱勒組織了一項全球篩選工作。那時,許多實驗室正在從 DIPG 腫瘤組織中建立細胞培養物。作為提議用於 DIPG 臨床試驗的藥物委員會的聯合主席,凱勒召集了蒙傑實驗室和其他 12 個小組,彙集資源進行合作研究。他的小組將 83 種潛在藥物分配到孔板上,並將它們送到其他實驗室進行測試。在這些遙遠的實驗室中,研究人員將孔板裝載 DIPG 細胞培養物,並尋找變成藍色的孔——這是一種化學指示,表明該藥物正在殺死腫瘤細胞。頂級候選藥物也提高了植入 DIPG 腫瘤的小鼠的存活率。
此外,這些實驗室還從其 DIPG 細胞系中純化了遺傳物質,並將 DNA 和 RNA 樣本送到俄勒岡州進行測序,以建立細胞基因故障與藥物反應之間的明確聯絡。凱勒說,檢查這些聯絡至關重要,因為許多基於 DIPG 細胞突變看起來很有希望的藥物在細胞分析中沒有顯示出任何效果。
但出現了一個贏家——一種名為帕比司他的藥物,它可以抑制化學修飾組蛋白的酶。巧合的是,當全球篩選手稿在自然醫學雜誌上發表時,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了帕比司他作為另一種癌症(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藥物。這些結果幫助啟動了一項帕比司他的臨床試驗,該試驗於 5 月開始招募患者。這項由蒙傑領導的試驗將測量副作用,並確定治療 DIPG 兒童的最佳藥物劑量。然而,帕比司他不會成為靈丹妙藥。實驗室資料顯示,一些 DIPG 細胞對該藥物產生耐藥性,這表明它需要與其他療法聯合使用才能在患者中獲得生存益處,蒙傑說。
帕比司他面臨的一個挑戰是許多腦癌療法共同面臨的挑戰——有效地將它們輸送到大腦中。“許多藥物無法穿過血腦屏障,因此它們無法到達腫瘤,”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穆勒說。一些研究人員正在使用一種稱為對流增強遞送的程式,透過細小的導管將藥物直接輸送到腦腫瘤中。另一些研究人員正在使用奈米技術來重新配製藥物,使其更具特異性和永續性——例如,透過插入分子標籤,將藥物定向到腫瘤上唯一發現的分子。穆勒說,DIPG 的好藥可能已經存在,但“我們只是不知道如何正確地輸送它們。”她正在計劃未來一項在 DIPG 兒童中使用對流增強遞送帕比司他的試驗。
與此同時,蒙傑的實驗室和其他小組正在使用表觀遺傳劑和聯合方案進行額外的藥物篩選,凱勒創立了一家非營利性癌症生物技術公司,以加速候選藥物從基礎科學研究到臨床試驗的轉移。每年,他的團隊都會組織一個為期一週的速成課程,向家庭介紹兒童腦癌,並解釋腫瘤組織捐贈如何推動研究。
一些家庭定期訪問實驗室,在顯微鏡下觀察孩子的細胞。韋策爾一家在女兒因 DIPG 去世八到九個月後訪問了蒙傑的實驗室。“當我第一次看到麥肯納的細胞時,我開始無法控制地哭泣,”韋策爾說。“我想拿起每一個培養皿……然後把它扔到牆上,摧毀細胞系,就像它摧毀了我的女兒一樣。”
現在,在每年大約一次的實驗室訪問之後,韋策爾的感覺有所不同。“我把它看作是麥肯納的最後一戰……她給世界和她之後的孩子們的禮物。如果麥肯納不能留在這裡,就讓她以她現在唯一能做的方式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這有助於我們認為她的死是有一些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