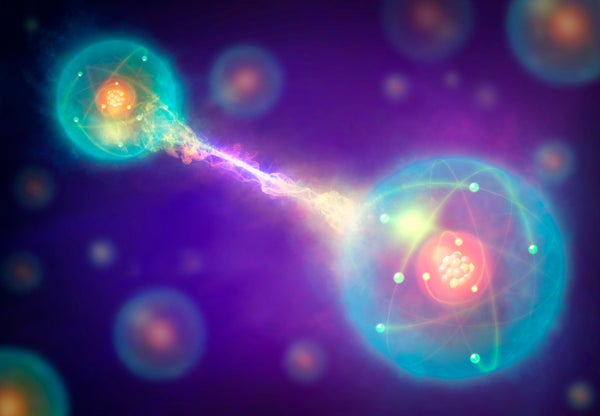量子世界是一個奇異的世界。理論上,並在一定程度上在實踐中,它的原則要求一個粒子可以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這種悖論現象被稱為疊加態——並且兩個粒子可以“糾纏”,透過某種仍然未知的機制在任意大的距離上共享資訊。
也許最著名的量子怪異例子是薛定諤的貓,這是埃爾溫·薛定諤在 1935 年設計的一個思想實驗。這位奧地利物理學家想象,根據奇怪的量子力學定律,一隻被放置在裝有潛在致命放射性物質的盒子裡的貓,可能同時處於既死又活的疊加態——至少在盒子被開啟並觀察其內容物之前是這樣。
儘管這聽起來很離奇,但這個概念已經在量子尺度上經過無數次實驗驗證。然而,當我們放大到看似更簡單、肯定更符合直覺的宏觀世界時,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沒有人見過恆星、行星或貓處於疊加態或量子糾纏態。但自從 20 世紀初量子理論最初形成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思考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究竟在哪裡交匯。量子領域究竟能有多大?它有可能大到足以使其最奇異的方面密切而清晰地影響生物嗎?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新興的量子生物學領域一直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提出並對活生物體進行實驗,以探索量子理論的極限。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這些實驗已經產生了一些誘人但沒有定論的結果。例如,今年早些時候,研究人員表明光合作用過程——生物體利用光製造食物的過程——可能涉及一些量子效應。 鳥類如何導航或我們如何聞到氣味也表明量子效應可能以不尋常的方式發生在生物體內。但這些只是淺嘗輒止地進入量子世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成功地誘導整個活生物體——甚至單個細菌——表現出量子效應,例如糾纏或疊加。
因此,牛津大學一個小組最近發表的一篇新論文引起了一些關注,因為它聲稱細菌已成功與光子(光粒子)糾纏。這項研究由量子物理學家基亞拉·馬萊托領導,於 10 月份發表在《物理學通訊雜誌》上,是對謝菲爾德大學的大衛·科爾斯及其同事於 2016 年進行的一項實驗的分析。在該實驗中,科爾斯及其公司將數百個光合綠硫細菌隔離在兩面鏡子之間,逐漸縮小鏡子之間的間隙,縮小到幾百奈米——小於人類頭髮的寬度。透過在鏡子之間反射白光,研究人員希望使細菌內的光合分子與腔體耦合或相互作用,這本質上意味著細菌將不斷吸收、發射和重新吸收反射的光子。實驗取得了成功;多達六個細菌似乎以這種方式耦合。
馬萊託及其同事認為,細菌不僅僅與腔體耦合。在他們的分析中,他們證明實驗中產生的能量特徵可能與細菌的光合系統與腔體內部的光糾纏一致。本質上,似乎某些光子同時擊中和錯過了細菌內的光合分子——這是糾纏的標誌。“我們的模型表明,記錄到的這種現象是光與細菌內部某些自由度之間糾纏的標誌,”她說。
牛津大學的另一位研究合著者特里斯坦·法羅表示,這是首次在活生物體中瞥見這種效應。“如果你願意的話,這當然是證明我們正在朝著‘薛定諤的細菌’這個想法邁進的關鍵,”他說。它暗示了自然產生的量子生物學的另一個潛在例項:綠硫細菌生活在深海中,那裡缺乏賦予生命的光,甚至可能刺激量子力學進化適應,以促進光合作用。
然而,對於如此有爭議的主張,存在許多警告。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該實驗中糾纏的證據是間接的,取決於人們如何選擇解釋從腔體限制的細菌中涓涓細流進出的光。馬萊託及其同事承認,不含量子效應的經典模型也可以解釋實驗結果。但是,當然,光子根本不是經典的——它們是量子的。然而,使用牛頓定律描述細菌和量子定律描述光子的更現實的“半經典”模型未能重現科爾斯及其同事在實驗室中觀察到的實際結果。這暗示量子效應在光和細菌中都發揮了作用。“這有點間接,但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只是試圖嚴格地排除事物,而不聲稱太多,”IBM 蘇黎世研究實驗室的量子計算研究員詹姆斯·伍頓說,他沒有參與這兩篇論文。
另一個警告:細菌和光子的能量是集體測量的,而不是獨立測量的。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西蒙·格羅布拉赫(Simon Gröblacher)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他認為這是一個侷限性。“似乎有一些量子現象正在發生,”他說。“但是……通常如果我們證明糾纏,你必須獨立測量這兩個系統”,以確認它們之間的任何量子相關性是真實的。
儘管存在這些不確定性,但對於許多專家來說,量子生物學從理論夢想轉變為有形現實只是時間問題,而不是是否會發生的問題。在生物系統外部,分子已經單獨和集體地在數十年的實驗室實驗中表現出量子效應,因此,對於細菌甚至我們自己體內相似的分子,尋找這些效應似乎是明智之舉。然而,在人類和其他大型多細胞生物中,這種分子量子效應應該被平均化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但它們在小得多的細菌中的有意義的表現不會太令人震驚。“我對[這一發現]有多令人驚訝有點矛盾,”格羅布拉赫說。“但如果你能在真正的生物系統中展示這一點,那顯然是令人興奮的。”
包括格羅布拉赫和法羅領導的幾個研究小組希望進一步推進這些想法。格羅布拉赫設計了一個實驗,可以將一種叫做水熊蟲的小型水生動物置於疊加態——由於水熊蟲的尺寸比細菌大數百倍,因此這個提議比將細菌與光糾纏要困難得多。法羅正在研究改進細菌實驗的方法;在 2019 年,他和他的同事希望將兩個細菌相互糾纏,而不是分別與光糾纏。“長期目標是基礎性和根本性的,”法羅說。“這是關於理解現實的本質,以及量子效應是否在生物功能中發揮作用。從根本上說,一切都是量子的,”他補充道,而最大的問題是量子效應是否在生物的運作方式中發揮作用。
例如,可能是“自然選擇已經為生命系統找到自然利用量子現象的方法,”馬萊託指出,例如前面提到的細菌在光線匱乏的深海中進行光合作用的例子。但要弄清真相,需要從小處著手。研究一直在穩步攀升到宏觀層面的實驗,最近的一項實驗成功地糾纏了數百萬個原子。證明構成生物的分子表現出有意義的量子效應——即使是為了微不足道的目的——也將是關鍵的下一步。透過探索這種量子-經典邊界,科學家們可以更接近理解宏觀量子化意味著什麼,如果這種想法是真實的話。
喬納森·奧卡拉漢是一位居住在倫敦的自由空間和科學記者。您可以在 Twitter 上關注他@Astro_Jo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