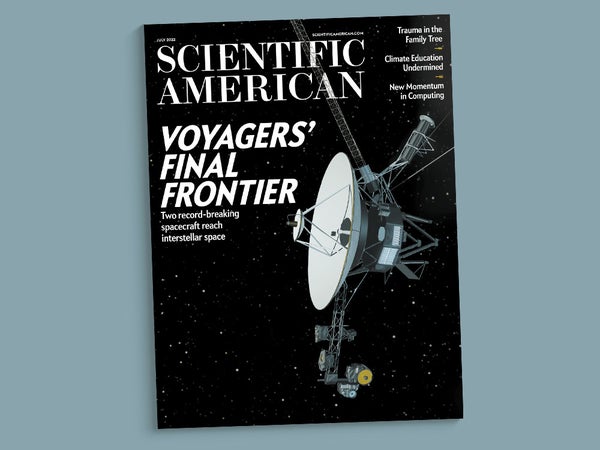旅行者號資料
我非常喜歡蒂姆·福爾傑的文章“旅行者號飛向群星”,文章介紹了旅行者號宇宙飛船的歷史和現狀。 但當他提到旅行者 1 號和 2 號將繼續它們的旅程,分別在 16,700 年和 20,300 年後經過最近的鄰近恆星比鄰星時,我感到困惑。
美國宇航局的網站說,旅行者號要 40,000 年才能到達比鄰星的中途點,並且要為此行駛兩光年。 如果我使用美國宇航局旅行者任務狀態網頁上給出的速度,並假設一年有 365.25 天,我得到旅行者 1 號和 2 號分別需要大約 70,000 年和 78,000 年才能行駛四光年。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 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繼續講述關於發現和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約翰·凱瑞 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託
“最長航程”框中的圖表顯示,兩個旅行者號宇宙飛船都偏離了太陽系平面。 這些航向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它們是預程式設計飛行改變的結果,還是離開太陽系的某個方面?
F. 特雷西·肖恩羅克 透過電子郵件
福爾傑回覆: 回答凱瑞:在 40,000 年後,旅行者號將到達奧爾特雲的外邊緣,這確實大約是到比鄰星的一半距離。 但在數萬年前,旅行者 1 號和 2 號將最接近這顆恆星,分別在約 3.5 光年和 2.9 光年範圍內。 這不是很近:太陽目前距離比鄰星約 4.2 光年。 在宇宙尺度上,太陽和旅行者號宇宙飛船與我們最近的恆星鄰居的距離基本相同。 但由於宇宙飛船正在遠離太陽,而比鄰星正在向太陽靠近,旅行者號最接近我們鄰近恆星的時間將發生在 16,700 年和 20,300 年後。
關於肖恩羅克的問題: 旅行者 1 號的軌跡被設計為儘可能接近土星的衛星土衛六。 該軌跡最終將旅行者 1 號“向北”帶出黃道面,即太陽系平面。 旅行者 2 號的路徑被設計為使其超越土星,到達天王星和海王星。 該路徑將旅行者 2 號“向南”送出黃道面。 這些不是航向修正。 相反,宇宙飛船隻是遵循能夠讓科學家們獲得外觀行星最佳觀測效果的路徑。
為氣候緊急情況付費
在“課堂上的氣候錯誤教育”中,凱蒂·沃思報道了化石燃料行業在德克薩斯州制定科學教育標準方面令人震驚的不相稱的影響力,這反過來又影響了美國大部分地區的教科書內容。 作為義大利一所國際學校的科學教育工作者和學校可持續發展負責人,我發現德克薩斯州基於志願者委員會制定標準以及州教育委員會成員做出決策的過程極其令人擔憂。 但我並不完全不同意他們推動納入能源資源的“成本效益分析”。 雖然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轉移人們對氣候行動需求的注意力的方式,但我也看到了一個機會。
通常,人類對環境的影響被簡化為“我的錯”描述,很少分析通常導致環境進一步破壞的決策機制。 學生必須承認並展示對環境不良決策是如何以及為何做出的理解,才能真實地提出替代方案。 透過讓他們分析與化石燃料使用相關的成本和收益——以及誰來支付——他們肯定會得出與任何其他理性科學家相同的結論: 儘管啟動成本很高,但將我們的社會轉變為可再生能源將使我們免受與繼續走當前道路相關的、急劇增加的健康、社會、經濟和環境成本。 而且,不,這不會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珍妮弗·哈恩 義大利都靈
歌唱偵探
亞當·費什拜因的精彩文章“鳥類如何聽到鳥鳴”[五月刊] 讓我想起我在自己對流行音樂歌唱的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問題。 對我來說,鳥類歌唱的“旋律”更多的是一種載體,用於傳遞它們實際上透過聲音“精細結構”交流的內容,這並不奇怪。 我發現這篇文章是基於一種非常西方的語言和音樂思維方式,即關注抽象概念而不是實際聲音。 但為費什拜因辯護,這種情況在該領域很普遍。
首先,將音樂的概念限制在單純的音符(我稱之為“抽象引數”)的想法,這種想法已被許多“傳統”音樂學家和音樂理論家所認同,現在正受到強烈質疑。 事實上,最近的研究表明,流行音樂聽眾,當然對音高(旋律)敏感,但也特別對與音色相關的聲音製作方面做出反應。 在流行音樂歌唱中,副語言(我們說話時發出的周圍聲音,通常被錯誤地認為是純粹的噪音)被系統地用於傳達相當具體的情感內容。 旋律雖然至關重要,但充當著這種副語言產生的載體。
那麼像普通話這樣的聲調語言呢? 研究表明,說中文的人透過耳朵識別音高的能力或“絕對音感”要好得多。 雖然大多數人在不同的音高中演唱給定旋律時,即使音調發生了變化,也能識別出旋律,但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聽到這種變化。 對於許多音樂家來說,每種調性在文化上都傳達著其自身的情感特徵。
在我同事和我進行的研究,以及全球許多其他音樂學家的研究中,我們研究了音色中的細微變化,這些變化與文章中使用相同工具(波形和頻譜圖)描述的精細結構非常相似。 許多研究人員對音樂中更精細的結構感興趣,正是因為人類對音色(甚至可能比對旋律結構)以及節奏中的細微變化非常敏感。 事實上,我們意識到,缺乏對人類精確感知這些更精細結構的能力的研究是基於千年來的西方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偏愛抽象而非具體。
我相信鳥鳴等主題將是真正跨學科研究的完美領域。 我們,作為微變音樂學的音樂學家,絕對準備好做出貢獻(好吧,至少,我準備好了!)。
塞爾日·拉卡斯 拉瓦爾大學音樂學正教授,魁北克
費什拜因回覆: 拉卡斯就音樂和語言中微變的重要性提出了很好的觀點。 我完全同意這個話題是跨學科研究的成熟領域。 鳥鳴研究通常試圖將語法和語言和音樂的其他更抽象的引數進行比較,但我認為人類和鳥類在從聲音的細微變化中提取情感內容時更相似。 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研究的鳴禽物種,在聽到精細結構變化方面似乎比人類要好得多。 這可能是由於內耳結構的基本解剖學差異造成的。 儘管不同文化中音樂的旋律結構有所不同,但聽到旋律的能力在人類中是普遍存在的。 鳴禽似乎根本不像我們那樣將聲音串聽作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