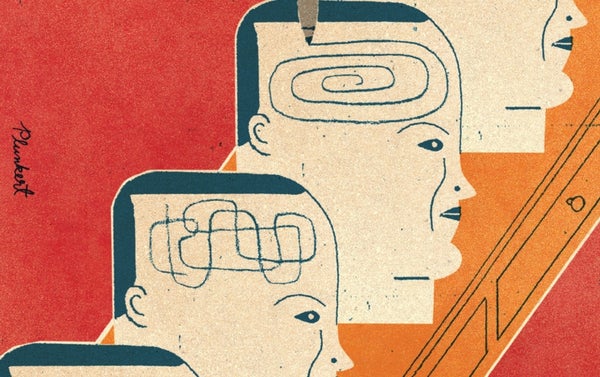對於年輕的心理學家來說,現在是艱難時期。這個想法最近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盤旋,因為我們剛剛完成在我們大學尋找一位新的心理學教授的工作。當我與候選人見面時,我不得不詢問他們領域中令人不安的重複性——以及信譽——危機。
我感覺好像在追問他們一些骯髒的私事,比如他們家族是否有酗酒史,但這個話題是不可避免的。檢驗任何科學研究有效性的一個關鍵標準是,其他科學家是否可以重複其結果。去年,一個名為“開放科學合作組織”的團體在《科學》雜誌上報告說,在主要心理學期刊上發表的100項研究中,超過一半未能透過該檢驗,儘管他們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來重現最初的實驗。
這個令人失望的訊息被廣泛報道,包括《大眾科學》。《紐約時報》在一篇頭版報道中宣稱,該報告“證實了長期以來一直擔心[心理學]需要強力糾正的科學家的最壞擔憂。經過審查的研究被認為是科學家理解人格、人際關係、學習和記憶動態的核心知識的一部分……如此多的研究受到質疑這一事實可能會在他們工作的科學基礎上播下懷疑的種子。”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今年三月,這場危機再次成為頭條新聞。一個由哈佛大學的丹尼爾·T·吉爾伯特領導的四位著名心理學家小組在《科學》雜誌上聲稱,2015年開放科學合作組織的研究在統計學上存在缺陷,並沒有證明其“心理科學的可重複性出奇地低”的說法。“事實上,”吉爾伯特及其合著者表示,“資料與相反的結論一致,即心理科學的可重複性非常高。”
在反駁中,參與開放科學合作組織的44位作者反駁說,吉爾伯特小組的“非常樂觀的評估”“受到統計學誤解和從選擇性解釋的相關資料中得出的因果推論的限制”。正如本尼迪克特·凱里在《紐約時報》中指出的那樣,“這次交流很可能會加劇關於如何最好地進行和評估所謂的研究重複專案的激烈辯論。”
這個評估過於樂觀了。這次交流揭示了心理學家甚至無法就達成“真理”(無論那是什麼)的基本方法達成一致。正如凱蒂·M·帕爾默在《連線》雜誌的一篇題為“心理學正處於危機之中,關於它是否處於危機之中”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兩組非常聰明的人正在研究完全相同的資料,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與此同時,壞訊息不斷傳來。一項新的研究對有影響力的“自我損耗”理論提出了質疑,該理論認為意志力是一種有限的資源,會隨著使用而減少。
在199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該論文已被引用數千次,羅伊·F·鮑邁斯特和其他三位心理學家提出了自我損耗的實驗證據。該理論據稱已得到數百項其他研究的證實,並支撐著鮑邁斯特和記者約翰·蒂爾尼在2011年出版的暢銷書《意志力:重拾人類最強大的力量》。
由科廷大學的馬丁·哈格和尼科斯·查齊薩蘭蒂斯領導的多中心團隊最近在一項涉及2141名受試者的研究中測試了自我損耗假說。在心理科學協會早期釋出的該論文的未經編輯版本中,該團隊得出結論:“如果存在任何[自我損耗]效應,它也接近於零。”
在回應中,鮑邁斯特和他的同事凱瑟琳·D·沃斯對哈格等人的方法提出異議,但承認“這場災難將舉證責任轉移到我們這些相信自我損耗效應是真實的人身上。”他們計劃明年進行自己的重複研究。
在《Slate》雜誌一篇標題為“一切都在崩潰”的末日文章中,記者丹尼爾·恩格伯指出,自我損耗並非“一些瘋狂的新想法,搖搖欲墜地堆積在一堆脆弱的資料之上;它是一個堅固的知識大廈,多年來由堅實的磚塊建成……如果如此完善的東西都可能瓦解,那麼接下來會是什麼?”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年輕的心理學家無疑正在為此苦惱。
過去,我曾嚴厲批評心理學,將其描述為令人不安的時尚。諸如精神分析和行為主義之類的正規化從未真正消亡——它們只是時興時衰。我喜歡引用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的話,他曾說過,我們可能總是從文學中學到更多關於我們自己的東西,而不是從心理學中學到更多。本著這種精神,我認為詹姆斯·喬伊斯的意識流傑作《尤利西斯》比任何科學研究都更能讓我們深入瞭解我們思想的運作方式。
但也許是因為我最近與有抱負的年輕心理學家會面,我對這個領域感到有些奇怪的保護。事實上,為了鼓勵年輕和年老的心理學家,我想提出以下四點
首先,心理學的信譽危機並非新鮮事。一個多世紀前,威廉·詹姆斯就擔心他幫助建立的這個領域可能永遠無法超越其“混亂和不完善的狀態”。霍華德·加德納在1987年認為,“詹姆斯的擔憂已被證明是完全合理的。心理學尚未加起來成為一門綜合科學,並且不太可能永遠達到這種地位。”
其次,心理學家仍在進行重要的、經驗上可靠的工作。最近在我校發表演講的兩位是恐怖管理理論的共同創立者謝爾頓·所羅門,該理論預測了對死亡的恐懼如何影響我們,以及“超級預測者”研究的領導者菲利普·泰特洛克,超級預測者是指在預測社會現象方面做得比許多所謂的專家更好的人。
第三,心理學家自己也幫助我們認識到,對知識的追求可能會如何出錯。想想丹尼爾·卡尼曼關於認知偏差的實驗,他在他的暢銷書《思考,快與慢》中對此進行了闡述,以及羅伯特·特里弗斯關於自我欺騙的研究,他在《愚人蠢事》中對此進行了介紹。為了幫助我的學生理解我們常常只看到我們正在尋找的東西,我給他們看了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爾·西蒙斯設計的“隱形大猩猩”影片。
第四,所有科學領域都面臨著重複性問題。統計學家約翰·約安尼迪斯在過去十年中進行的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同行評審的主張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在我看來,行為遺傳學和精神病學遠不如心理學可信,而弦理論和多重宇宙理論家甚至沒有經驗結果可以重複。
心理學可以說比許多其他領域更健康,這正是因為心理學家正在積極地揭露它的弱點,並尋求克服這些弱點的方法。我迫不及待地想在明年秋天與我們學校新來的心理學教授討論這些問題。
編者注:本文改編自 Cross-Check 系列中的一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