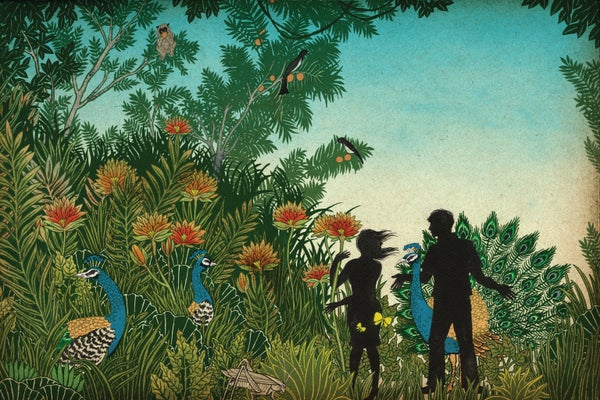澳大利亞最具挑釁性的藝術博物館之一,塔斯馬尼亞州霍巴特的舊藝術與新藝術博物館,在2016年和2017年舉辦了一個關於藝術進化的展覽。三位客座策展的進化科學家提出了他們對進化如何解釋不僅是變形蟲、螞蟻和羚羊的特徵,還有人類獨特的藝術事業的看法。其中一種解釋認為,藝術是一種進化特徵,類似於孔雀色彩鮮豔的尾巴,它透過發出作為配偶的優越訊號來提高其攜帶者的繁殖成功率。
如果這種情況讓您聯想到一位備受讚譽的女藝術家的形象,她以大膽突破藝術慣例而聞名,愉快地周旋於一系列英俊的年輕男性繆斯之間,請舉手?我們不這麼認為。
大膽放蕩的男人,以及與其對應的謹慎貞潔的女人,這種刻板印象根深蒂固。普遍的看法認為,男女之間的行為差異是與生俱來的,經過數千年的自然選擇磨練,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不同的生殖潛力。在這種觀點看來,男性憑藉其天生具有的冒險和競爭傾向,註定要在人類努力的各個領域的最高層次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是藝術、政治還是科學。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但仔細觀察人類和其他生物的生物學和行為,就會發現許多用於解釋性別差異的起始假設都是錯誤的。例如,在許多物種中,雌性從具有競爭性或玩弄感情中獲益。而且,在性生活方面,女性和男性通常有相似的偏好。而且,越來越清楚的是,遺傳的環境因素在適應性行為的發展中起著作用;在人類中,這些因素包括我們的性別文化。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兩性平等可能比以前認為的更易於實現。
快速的雄性,挑剔的雌性
過去和現在性別不平等的進化解釋的起源是查爾斯·達爾文的性選擇理論。他作為博物學家的觀察使他得出結論,在求偶和交配領域,除了少數例外,被選擇的挑戰通常主要落在雄性身上。因此,雄性,而不是雌性,進化出了諸如體型較大或大鹿角等特徵,以幫助擊敗對領地、社會地位和配偶的競爭。同樣,通常是雄性物種進化出純粹的審美特徵來吸引雌性,例如令人驚歎的羽毛、精心設計的求偶歌曲或精緻的氣味。
然而,是英國生物學家安格斯·貝特曼在 20 世紀中期對為什麼雄性傾向於導致性競爭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貝特曼研究的目標是檢驗達爾文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假設。與自然選擇一樣,性選擇導致一些個體比其他個體更成功。因此,如果性選擇對雄性的作用比雌性更強,那麼雄性應該具有更廣泛的繁殖成功範圍,從慘淡的失敗者到巨大的贏家。相比之下,雌性的繁殖成功率應該更加相似。這就是為什麼成為動物界中相當於傑出藝術家的個體,與平庸的藝術家相比,對雄性比對雌性更有益。

來源:“重新思考貝特曼原則:挑戰對性不情願的雌性和放蕩雄性的持久神話”,作者:Zuleyma Tang-Martínez,發表於《性研究雜誌》,第 53 卷,第 4-5 期;2016
貝特曼使用果蠅來檢驗這個想法。儘管當時還沒有親子鑑定技術,但他還是盡力推斷出雄性和雌性的親子關係和不同配偶的數量。他透過巧妙地使用具有不同基因突變的果蠅來做到這一點,包括一種使翅膀上的剛毛變得格外長的突變,另一種使翅膀向上捲曲的突變,還有一種使眼睛非常小或缺失的突變。這些突變有時在後代中很明顯,因此貝特曼可以透過計算倖存後代中不同突變體的數量來估計每個成年個體產生的後代數量。從他的資料中,他得出結論,雄性的繁殖成功率(以後代數量衡量)確實比雌性更具可變性。貝特曼還報告說,只有雄性的繁殖成功率隨著配偶數量的增加而增加。他認為,這就是為什麼雄性競爭而雌性選擇的原因:雄性的繁殖成功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可以使之受精的雌性數量的限制,而雌性只需一個配偶提供她所需的所有精子就能達到其上限。
學者們最初大多忽略了貝特曼的研究。但大約二十年後,當時在哈佛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羅伯特·特里弗斯將這項研究推向了科學界的盛名。他用雌性在繁殖中投入更多來表達貝特曼的觀點——大的、肥的卵子與小的、瘦的精子——並指出,這種最初的不對稱性可以遠遠超出配子,涵蓋妊娠、餵養(包括哺乳動物的哺乳)和保護。因此,正如消費者在選擇汽車時比選擇一次性的廉價小飾品要小心得多一樣,特里弗斯認為,投入較多的性別——通常是雌性——會為與之交配的最佳伴侶而等待。關鍵在於:投入較少的性別——通常是雄性——會以理想的方式儘可能廣泛地散佈廉價、豐富的種子。
這種邏輯如此優雅而引人入勝,難怪當代研究已經確定了許多所謂的貝特曼-特里弗斯原則似乎適用的物種,包括那些異常地雄性是投入較多的性別的物種。例如,在某些螽斯科物種中,也稱為灌木蟋蟀,由於雄性在交配期間提供富含營養的包裹以及精子,因此雄性在繁殖中的投入大於雌性。因此,雌性互相爭奪與雄性交配的機會。
貝特曼-特里弗斯原則似乎也為人類社會的性別動態提供了合理的解釋。例如,人們普遍認為女性對與多個伴侶的隨意性行為興趣較小,並且更具關懷性,較少競爭性和冒險性。應用貝特曼-特里弗斯邏輯,這些行為有助於保護她們的投入。因此,Facebook 營運長謝麗爾·桑德伯格給女性的當代建議是,在工作中“向前一步”,以晉升到頂峰,但這似乎被這樣一種觀點削弱了,即冒險和競爭的傾向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進化得更強,因為前者有更高的生殖回報。
打破規則
但事實證明,自然遠沒有這種推理所暗示的那麼簡單和整潔,即使對於非人類動物也是如此。自從貝特曼-特里弗斯原則形成以來的幾十年裡,它們的許多基本假設已被推翻。其中一個思維轉變涉及到男性繁殖的所謂廉價性。精子並不總是廉價的,也不總是豐富的:例如,雄性竹節蟲在長時間交配後可能需要幾周才能恢復性慾。而最近對果蠅繁殖習慣的仔細研究發現,雄性並不總是抓住交配機會。雄性的選擇性對許多昆蟲的雌性產生了影響,因為如果它們與廣泛交配過的雄性交配,它們就有可能獲得不足的精子。精子稀少或有限是雌性面臨的常見挑戰,這可能是它們反覆與不同雄性交配以獲得足夠精子的原因。
事實上,對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帕特里夏·戈瓦蒂實驗室的貝特曼資料的重新審查至關重要地揭示,雌性果蠅的繁殖成功率也隨著其交配頻率的增加而增加,這種模式已在許多其他動物物種中出現。此外,實地研究表明,對雌性來說,交配並不是科學家曾經認為的那樣理所當然。在數量驚人的物種中,很大一部分雌性沒有遇到雄性,因此無法繁殖。而且,濫交也不是雄性的標準做法。雄性單配製,即雄性只交配一次,並不少見,並且可能是最大化繁殖成功率的有效手段。
昆蟲並不是唯一挑戰貝特曼-特里弗斯原則的生物。即使在哺乳動物中,由於妊娠和哺乳對雌性造成了特別大的代價,導致繁殖投入特別傾斜,競爭不僅對雄性的繁殖成功率很重要,而且對雌性的繁殖成功率也很重要。例如,等級較高的雌性黑猩猩的幼崽出生率和存活率都高於等級較低的雌性黑猩猩的幼崽。
在我們人類物種中,傳統的故事因人類性活動效率低下而變得更加複雜。與許多其他物種不同,在其他物種中,性交在更大程度上或更小程度上受到激素協調,以確保性行為導致受孕,而人類則進行大量的非生殖性性行為。這種模式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這意味著任何一次性交行為產生嬰兒的可能性都很低,這一事實應該緩和對種子傳播可能帶來的繁殖回報的過於樂觀的假設。其次,這表明性行為的目的不僅僅是繁殖——例如,加強關係。

圖片來源:清水裕子
文化和社會的變化進一步要求重新思考貝特曼-特里弗斯原則在人類中的應用。上個世紀盛行的兩性二分法觀點已經讓位於一種觀點,即認為差異主要在於程度而不是種類。避孕藥和性革命帶來的女性性自主權的提高,導致女性,尤其是女性的婚前性行為和性伴侶數量顯著增加。而且,女性和男性報告說,他們的性生活偏好大致相似。例如,第二次英國全國性態度和生活方式調查,基於本世紀初對 16 至 44 歲之間超過 12,000 人的隨機抽樣調查,發現 80% 的男性和 89% 的女性更喜歡一夫一妻制。
與此同時,女權主義運動增加了女性進入傳統男性領域並在其中脫穎而出的機會。1920 年,在接納女性的 12 所頂尖法學院中,只有 84 名女性在讀,而那些女律師發現幾乎不可能找到工作。在 21 世紀,女性和男性從法學院畢業的人數大致相等,2015 年女性約佔權益合夥人的 18%。
風險和收益
當我們從這種對性別模式的粗略視角放大到對行為中性別差異的細緻審查時,熟悉的進化故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考慮一下冒險,曾經被認為是男性的性格特徵,這要歸功於它在提高男性繁殖成功率方面的作用。事實證明,人們在願意承擔的風險型別方面非常特立獨行。跳傘運動員並不比喜歡在健身房安全鍛鍊的人更可能賭博。解釋他們冒險意願的是人們對特定冒險行為的潛在成本和收益的看法,而不是他們對風險本身的看法。這些感知到的成本和收益不僅包括物質損失和收益,還包括對聲譽或自我概念的較不具體的衝擊。
這種細微差別很重要,因為有時風險和收益的平衡對於男性和女性來說並不相同,這可能是因為兩性之間的身體差異或性別規範,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例如,考慮一下隨意性行為的風險。對於男性來說,收益包括幾乎可以肯定地獲得性高潮,並可能提升他作為“種馬”的聲譽。根據密歇根大學的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及其同事 2012 年發表的一項針對北美學生的大規模研究,女性從隨意性行為中獲得性快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由於性雙重標準,她的聲譽更有可能因該事件而受損。例如,在年輕的澳大利亞人中,昆士蘭科技大學的社會學家邁克爾·弗拉德發現,“蕩婦”這個標籤在“應用於女性時,仍然具有更強的“道德和紀律約束力……”。此外,女性承擔著更大的身體風險,包括懷孕、性傳播疾病,甚至性侵犯。
不同風險和收益的視角還可以闡明兩性在工作中表現自己的不同傾向,正如桑德伯格建議女性做的那樣。很難想象,一位年輕的女律師,首先看看她所在級別的眾多年輕女性,然後再看看極少數的女性合夥人和法官,能夠像一位年輕的男律師那樣對向前一步併為自己的職業生涯做出犧牲的可能回報感到樂觀。而這還是在人們考慮到傳統男性職業(如法律和醫學)中存在的性別歧視、性騷擾和性別歧視的大局證據之前。
儘管如此,在許多人看來,一個非性別歧視的社會可以消除永恆的、持久的性別在生殖投入方面的差異所造成的心理影響,這種想法似乎是不切實際的。《經濟學人》2017 年的一篇文章,例如,將營銷驅動的鑽石訂婚戒指傳統等同於孔雀招搖的奢華尾巴,這是一種進化的求偶儀式,表明了男性的資源和承諾。這位記者寫道,“女性的更大平等似乎使男性求偶展示變得多餘。但擇偶偏好是經過數千年進化而來的,不會很快改變。”
環境影響
儘管性別肯定會影響大腦,但這種論點忽略了進化生物學中日益增長的認識,即後代不僅僅繼承基因。他們還繼承了特定的社會和生態環境,這些環境可以在適應性特徵的表達中發揮關鍵作用。例如,作為幼蟲來自稠密種群的成年雄性蛾子會發育出特別大的睪丸。這些增強的器官使雄性蛾子在與種群中許多其他雄性進行的激烈交配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人們可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尺寸慷慨的性腺是一種基因決定的適應性特徵。然而,在低密度種群中作為幼蟲飼養的同種成年雄性蛾子反而發育出更大的翅膀和觸角,這對於尋找廣泛分散的雌性來說是理想的。
如果與性別相關的身體特徵的發育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那麼與性別相關的行為也可能如此,這是有道理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來自前面提到的雌性螽斯科,它們根據貝特曼-特里弗斯原則,爭奪為它們帶來精子和食物的雄性。值得注意的是,當它們的環境變得富含營養豐富的花粉時,它們的競爭“本性”就會減弱。
環境對於哺乳動物的適應性行為也同樣重要。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開始發表的研究發現,雌性大鼠對雄性和雌性幼崽的照顧方式不同。雄性幼崽比雌性幼崽在肛門生殖器區域受到更多的舔舐,因為雌性大鼠被雄性幼崽尿液中較高水平的睪丸激素所吸引。有趣的是,來自這種更高強度舔舐的更大刺激在參與基本雄性交配行為的大腦部分中性別差異的發展中發揮了作用。
正如悉尼大學科學哲學家保羅·格里菲斯所觀察到的,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每代人可靠地重複出現的環境因素或經歷應該被納入到發育過程中,從而產生進化特徵。
在我們人類物種中,這些發育輸入包括賦予每個新生兒豐富的文化遺產。儘管性別的社會建構因時間和地點而異,但所有社會都賦予生物性別以沉重的文化意義。性別社會化從出生時就開始了,如果無情的自然選擇過程要利用它,那才是合乎邏輯的。在我們的進化歷史中,男性承擔這些或那些風險,或者女性避免這些風險,很可能具有適應性。但是,當文化發生變化時——與過去相比,創造了非常不同的獎勵、懲罰、規範和後果模式——行為中的性別差異模式也會隨之改變。
因此,《經濟學人》的作者在聲稱人類“擇偶偏好是經過數千年進化而來的,不會很快改變”時,並不完全正確。沒錯,它們不太可能像螽斯科那樣隨著花粉的灑入而迅速改變(儘管我們懷疑這不是它的意思)。創造文化轉變通常沒有什麼簡單快捷的方法。但是,改變肯定能夠而且肯定已經發生了,而且時間尺度比數千年要短。
例如,以男性和女性對伴侶的經濟資源、吸引力和貞潔的重視程度方面的性別差距為例。與幾十年前相比,“貞潔”一詞對今天的西方人來說非常古怪,這說明文化性別期望發生了快速變化。根據當時都在英國約克大學的馬塞爾·曾特納和克勞迪婭·米圖拉在 2012 年進行的一項研究,來自性別更平等的國家的女性和男性在所有這些伴侶偏好維度上都比來自性別較不平等的國家的女性和男性更相似。研究還表明,在美國,男性現在比幾十年前更重視女性伴侶的經濟前景、教育和智力,而不太在意她的烹飪和家務技能。與此同時,可憐的藍襪老處女的陳詞濫調已成為歷史遺蹟:儘管更富有和受過更好教育的女性曾經不太可能結婚,但現在她們更有可能這樣做。
那麼,我們是否會看到世界頂級美術館展出與男性一樣多的女性藝術品的那一天?我們當然不應該讓貝特曼的果蠅告訴我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