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恐懼?答案看似簡單,但關於其含義的激烈辯論一直在情感神經科學領域展開。這場辯論歷史悠久,但最近因 Joseph LeDoux 而再次被點燃,他提出我們不僅應該重新定義恐懼,還應該改變我們實驗性地研究這種情感的方式。這場辯論的核心觀點是,情感是意識的、主觀的狀態。例如,與恐懼相關的“感覺”,如恐懼或驚恐,是對一個人所處情境的認知性組合概念,而不是從動物那裡繼承來的預先形成的、天生的心理狀態。因此,LeDoux 認為,人類大腦的這種複雜狀態無法在動物身上進行研究。相反,他建議,應將作為防禦行為基礎的“防禦性生存迴路”作為動物研究的重點。這些硬連線的迴路被認為是與主觀恐懼狀態正交的,後者可能涉及更高階的迴路——它們可以調節但不能決定情感。Lisa Feldman Barrett 的“構建情感理論”提出了一個同樣具有挑釁性的理論,該理論認為,人類大腦構建恐懼例項,是預測和推斷來自身體(即,內感受和軀體感覺輸入)和世界(即,外感受輸入)的傳入感覺輸入原因的結果。Barrett 提出,大腦不斷地向前投射自身,預測骨骼運動和內臟運動的變化,並推斷這些運動行為將導致的感覺變化。Barrett 理論最受爭議的地方可能是,它提出恐懼與其他情感類別一樣,不具有硬連線的神經解剖學特徵,而是動態系統的一部分,在該系統中,預測訊號被理解為臨時的、抽象的類別或概念,這些類別或概念是從與當前條件相似的過去經驗中生成性地組裝而成的。在這種觀點中,大腦是一個分類機器,不斷建立與動物生態位相關的、在情境上相關的概念。
這些發人深省的觀點似乎與其他突出的觀點相悖,例如已故 Jaak Panksepp 和該領域其他著名人物(例如,Michael Davis、Robert Bolles、O. Hobart Mowrer)的基本(或主要)恐懼迴路理論。例如,Ralph Adolphs 強調防禦行為的普遍性,這增加了恐懼迴路在物種間相互映象並因此部分是天生的觀點的可信度。Michael Fanselow 提出,恐懼(和焦慮)可以沿著威脅迫近連續統進行放置,這充當了一般的組織原則,並且威脅強度可以與動機過程和防禦行為聯絡起來。同樣,Kay Tye 認為恐懼是一種負面的內在狀態,它驅動和協調防禦反應。這些觀點將防禦行為視為硬連線的恐懼(或生存)迴路的表現,並由認知上靈活的迴路控制和修改。雖然這場辯論已經開始衝擊臨床科學和實踐的海岸線,但在基礎科學和臨床科學領域之間,關於如何定義和研究恐懼和焦慮,仍然需要達成更多共識。在這裡,我們邀請了一些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來討論他們的觀點。涵蓋人類和動物研究,每個人都將針對以下討論要點提出一個論點。
問題 1:Dean Mobbs(主持人):您如何定義恐懼?您的定義如何得到神經科學的支援?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關於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Ralph Adolphs (RA): 恐懼只能根據對自然環境中行為的觀察來定義,而不是神經科學。在我看來,恐懼是一種具有特定功能特性的心理狀態,在概念上與有意識的體驗不同;它是一個潛在變數,為觀察到的與恐懼相關的行為提供因果解釋。恐懼指的是具有相似功能的一類粗略狀態;科學可能會修改這幅圖景,並向我們展示存在不同種類的恐懼(可能大約有十幾種),它們依賴於不同的神經系統。
定義恐懼狀態的功能特性是那些從進化角度來看,使這種狀態適應於應對特定類別的生存威脅(例如,捕食者)的特性。恐懼具有幾個功能特性——例如永續性、學習能力、可擴充套件性和普遍性——這些特性將情緒狀態與反射和固定行為模式區分開來,儘管後者當然也可以促進行為。
調節動物與恐懼相關的行為的神經迴路表現出許多相同的功能特性,包括在小鼠下丘腦中2,這是初步證據,表明這個大腦結構不僅僅參與將情緒狀態轉化為行為,而且在中心情緒狀態本身中也發揮作用。恐懼與其他情緒的神經心理學分離表明,恐懼是一個獨特的類別。
Michael Fanselow (MF): 恐懼是一種神經-行為系統,它進化出來是為了保護動物免受環境威脅,威脅到 John Garcia 稱之為外部環境(相對於內部環境)的事物,而捕食是這種進化背後的主要驅動力(例如,相對於毒素)。這是我對恐懼的定義背後的組織思想。完整的定義還必須包括引起恐懼的訊號(前因)和客觀可觀察的行為(後果)。對這種定義的神經科學支援是,許多外部威脅訊號,例如預示可能疼痛的線索、天然捕食者的存在以及最近經歷過外部威脅的同種氣味,都會啟用重疊的迴路,並誘發一組常見的行為(例如,齧齒動物的僵住和鎮痛)。與神經科學支援同樣重要的是來自實地工作的支援,實地工作反覆表明,諸如僵住之類的行為可以提高面對捕食者時的生存能力。
Lisa Feldman Barrett (LFB): 我假設,每一種心理事件,無論是恐懼還是其他,都是在動物的大腦中構建的,作為組裝運動行為和支援它們的內臟運動行為的計劃,以及這些行為的預期感覺後果。後者構成了動物對其周圍生態位的體驗(視覺、聽覺、嗅覺等),包括物體的感受價值。這裡的“價值”是一種描述大腦對其身體狀態(即,內感受和骨骼運動預測)以及當動物移動或編碼新事物時該狀態將如何變化的方式。該計劃是一種推論(或一組推論),它是從類似於當前條件的已學習或天生的先驗知識中構建的;它們代表了大腦對預期感覺輸入原因的最佳猜測以及如何應對它們。
與恐懼最常相關的功能是免受威脅的保護。恐懼的相應定義是動物大腦為生存構建防禦行為的一個例項。人類大腦可能會構建在感覺或感知特徵方面與當前條件相似的推論,但這些推論也可能是功能性的,因此是抽象的,因此它們可能由通常被定義為恐懼刺激的事件引發,也可能不引發,並且可能導致通常被定義為恐懼行為的行為,也可能不導致。例如,有時人類可能會在面對威脅時大笑或睡著。在這種觀點中,恐懼不是由引發刺激的感覺特異性或動物產生的特定身體動作來定義的;相反,它以情境化的功能或目標為特徵:一組特定的動作和感覺後果,這些後果是根據先驗知識推斷出來的,目的是在類似情況下服務於特定功能(例如,保護)。
在認知科學中,一組在某些方面彼此相似的物體或事件構成一個類別,因此構建推論也可以描述為構建類別。那麼,措辭我的假設的另一種方式是,大腦正在動態地構建類別,作為對要採取哪些運動行為、它們的感官後果將是什麼以及這些動作和預期感官輸入的原因的猜測。類別的表示是一個概念,因此該假設也可以這樣措辭:大腦正在動態地構建概念,作為關於即將到來的運動行為及其預期感官後果原因的假設。概念或類別是以情境對情境的方式構建的,因此它們被稱為臨時概念或類別。透過這種方式,生物學類別可以被認為是臨時的概念類別。
Joseph LeDoux (JL): 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有意識的情感體驗,與所有其他有意識的體驗一樣,是由皮質迴路認知性地組裝起來的。例如,恐懼是一種有意識的意識,即你正處於危險之中。控制同時發生的行為和生理反應的皮質下回路的啟用可以透過向認知迴路提供輸入來增強體驗,但它們並不能決定體驗的內容。在我的模型中,體驗本身是一個人個人恐懼模式的模式完成的結果,它產生了一些你已經知道的、屬於你一生中積累的“恐懼”概念下的眾多變體之一。即使在某些或所有皮質下觸發的後果缺失時,恐懼也可能發生:當威脅本身產生基於記憶的期望,從而在精神上模擬缺失的元素,從而完成你的恐懼模式時。恐懼通常被認為是普遍存在的。但實際上普遍存在的是危險。人類處於危險之中的體驗是個人和獨特的。雖然其他動物在處於危險之中時可能也有某種體驗,但科學上無法衡量它們體驗到的內容,而且即使我們能做到,它也不太可能等同於人類體驗到的那種認知組裝的個人危險意識。這種認知解釋似乎是必要的,以便在一個框架內解釋一個人可能在其中有意識地體驗到恐懼的各種威脅情境(例如,捕食性、同種、穩態、社會性、生存性)。
Kerry Ressler (KR): 我對恐懼的定義是務實的和臨床的,也許是從 Adolphs 的角度來看的“功能主義”定義。“恐懼”是由特定刺激激發的防禦反應(生理的、行為的和(可能在人類的情況下)對這些反應的有意識體驗和解釋)的組合。在實驗系統中,這些刺激是外部線索,但據推測,在人類中也可能具有內部表徵(可能引發恐懼的線索的思想和記憶本身)。這種引發恐懼的線索會導致積極的防禦反應,當刺激不再存在時,這些反應會逐漸消退。臨床上,恐懼可以被認為是反映對特定線索的反應(例如,對蛇的恐懼),而焦慮是一種持續時間更長的現象,可能不特定於明顯的線索。數十年的臨床前神經科學研究檢查了巴甫洛夫恐懼或威脅條件反射的機制,結合人類神經影像學工作,表明多個大腦區域參與與杏仁核及其下游連線的交流,以支援“硬連線”的皮質下和腦幹區域的調節,這些區域介導心血管、呼吸、自主神經系統、激素、驚嚇、僵住和其他行為“恐懼”或“威脅”反射。

Kay Tye (KT): 恐懼是一種強烈的負面內在狀態。它協調和組織各種協同功能,以激發我們的最佳表現,從而進行躲避、逃跑或對抗。恐懼類似於一個獨裁者,它奴役所有其他大腦過程(從認知到呼吸)。恐懼可以是天生的,也可以是後天習得的。天生的恐懼可以在沒有先前經驗的情況下對環境刺激做出反應,例如人類對蛇和蜘蛛的恐懼,以及齧齒動物對捕食者氣味的恐懼。恐懼關聯——主要在巴甫洛夫恐懼條件反射的背景下研究——是最快速學習(一次嘗試)、最穩健編碼和檢索的,並且容易啟用多個記憶系統。鑑於其在生存中的關鍵重要性及其對大腦其餘部分的獨裁命令,恐懼應該是神經科學中最廣泛研究的主題之一,儘管由於其主觀性,它落後於對感覺和運動過程的研究。觀察他人表現出恐懼的行為表達和反應可能會引起情緒傳染或支援對環境的學習。“恐懼”一詞在行為神經科學領域的使用,透過對最初被稱為“恐懼條件反射”的非常刻板的行為正規化的廣泛使用和研究,而具有了相關但不同的含義。恐懼條件反射可以說是神經科學中最常用的行為正規化,並且在神經迴路解剖方面得到了最全面的挖掘,齧齒動物模型是主要模型,但也已用於人類、靈長類動物甚至無脊椎動物。恐懼條件反射指的是條件刺激(最常是聽覺純音)與足部電擊的巴甫洛夫配對,足部電擊最常在條件刺激終止時呈現。
問題 2:您的恐懼理論如何區分感覺、知覺和行動的神經迴路?
RA: 我不聲稱擁有理論,但在我看來,恐懼、感覺、知覺和行動都是不同的。恐懼與許多其他過程(包括知覺、行動計劃、注意力、記憶等)因果互動。但它是不同的,因為我們可以獨立於許多其他認知變數來操縱恐懼。失去知覺,如失明,不會讓你失去恐懼,只會讓你失去視覺誘導恐懼的能力;失去所有行為,如癱瘓時,也不會讓你失去恐懼;記憶和其他過程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恐懼狀態本身什麼也不做:它需要與其他所有這些過程聯絡起來才能導致行為(知覺、注意力等本身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區分感覺恐懼(有意識的恐懼體驗)和恐懼的功能狀態(解釋威脅刺激對認知和行為產生的所有影響的狀態)。我對這些狀態如何相關持不可知論態度,但我認為出於方法論原因,例如,研究非人類動物恐懼的能力,我們需要在概念上將它們分開。區分感覺恐懼的神經相關性和恐懼的功能狀態也非常困難。以上所有這些都暗示了一種由過程之間的構成和因果關係定義的認知結構。這實際上如何在神經上實現無疑在門和類之間有所不同;章魚的恐懼與人類或老鼠的恐懼在神經細節上會有很大不同。
MF: 它沒有區分。相關的迴路整合了它們;對威脅的知覺導致感覺和行動。恐懼狀態的啟用也會反饋到知覺系統,改變它們對環境刺激的反應方式。對威脅的知覺是恐懼程度和防禦行為形態的關鍵決定因素。請注意,並非所有行動都源於感覺,但所有與恐懼相關的感覺都會導致行動的某些改變。如果不是這樣,它們將失去生物學意義,並且在感覺需要能量的程度上,它們將被進化淘汰。一個完整的迴路將這些元件連線和整合到有效的防禦模式中。
LFB: 在我看來,這不是關於恐懼的最佳問題,因為它基於一個沒有根據的假設,即大腦最好被理解為神經元的集合,這些神經元被分組到解剖學上獨立的系統中(神經迴路),用於知覺、心理事件、感覺和各種型別的行動(例如,僵住、奔跑等),這些系統像接力賽中的接力棒一樣彼此來回傳遞資訊。我的研究方法受到另一種假設的指導,即大腦應該被理解為一個複雜的動力系統,它由元素組成:由神經元和支援神經膠質細胞組成的迴路或子網路。這些元素不是彼此獨立運作的,因為它們的排列和組織會動態變化。甚至構成它們的神經元也會動態變化。大腦作為一個動力系統,不斷地穿梭於一系列事件,稱為其狀態空間,狀態空間被指定為一組特徵的值,這些特徵描述了系統的當前狀態。特徵是物理的(例如,神經的、生理的、化學的)和心理的(知覺的、情感的、認知的等)。在這種觀點中,大腦透過預測和糾正而不是透過刺激和反應來工作。在系統特定狀態的動力學中,知覺是運動準備的結果,而不是相反(如刺激-反應方法所暗示的那樣)。
JL: 在我的方案中,恐懼是害怕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我會將“知覺”和“行動”稱為“威脅檢測”和“防禦反應”。我將恐懼體驗和行為反應視為威脅檢測的獨立後果,並由不同但相互作用的迴路介導。威脅檢測顯然始於感覺處理,對其的研究有助於說明刺激處理、行為和體驗之間的關係。例如,對盲視患者視覺知覺的研究表明,通往有意識知覺體驗的路徑可以與通往行為的路徑分離。這表明,健康大腦中知覺體驗與行為的相關性可能是由於不同系統對感覺資訊的並行處理,並不一定意味著體驗和行為在大腦中是糾纏在一起的。因此,知覺研究人員在從行為反應推斷體驗時往往持謹慎態度。就恐懼而言,盲視再次具有啟發意義。這些患者對威脅做出反應,但不報告對威脅刺激的意識或有意識的恐懼感;此類患者對有意識感覺的自我報告與新皮質活動相關。同樣,在對健康人的閾下刺激研究中,威脅會啟用涉及杏仁核的皮質下防禦迴路,並在沒有刺激意識的情況下引發生理反應;即使被專門詢問,也不會報告感覺。因此,控制僅有時與恐懼體驗相關的行為的迴路不一定是體驗的基礎迴路。當我們用“恐懼”一詞來標記這些迴路和行為時,我們會傳播概念上的混亂。
KR: 我認為,在神經科學層面上,我們可以區分感覺成分(例如,感覺丘腦和皮質:感覺)、整合認知成分(例如,聯合皮質和內側前額葉皮質:知覺)以及反射和行為成分(例如,杏仁核、紋狀體、腦幹:行動)。然而,這些不同的迴路如何對映到恐懼處理的有意識方面與行為方面可能更難以解析。解剖恐懼和威脅的神經連線的進展有助於我們理解它們如何調節自主神經、生理和行為活動模式,這些模式共同構成了“恐懼反射”,這似乎在物種之間高度保守。這些不同成分的某些方面顯然在相似的區域中得到表示——例如,在人類的威脅知覺中觀察到內側前額葉皮質和杏仁核的啟用,但也顯然參與了跨物種的威脅行為的基礎行動——而其他區域,例如,腦幹核,可能主要參與恐懼過程的行動成分。
KT: 初始資訊流透過感覺輸入到達,感覺輸入傳播到邊緣迴路(例如,杏仁核),然後前饋到下游靶點(例如,紋狀體、基底神經節),在那裡情緒狀態與威脅迫近程度相結合,以促進行動選擇。邊緣訊號然後可以反饋到感覺系統,以改變知覺。恐懼本身並不對映到單個運動輸出;它是一箇中間過程,將感覺處理與行動選擇聯絡起來。我目前的概念模型由三個心理過程組成,它們分別決定重要性(或顯著性)、效價和行動。這三個過程由不同的迴路介導。例如,如果一隻吃草的鹿聽到樹枝折斷的聲音,它必須首先評估刺激的重要性。如果它身處空曠的景觀中,沒有捕食者可以躲藏的地方,那麼刺激可能會被認為是不重要的,鹿可能會繼續吃草。如果鹿看到一隻熟悉的同種,那麼它可能會將刺激解釋為積極的效價訊號,從而促使選擇爭鬥性社會行為或接近。如果有茂密的灌木叢,那麼刺激所預示的潛在捕食者威脅可能會引發一種內在的恐懼狀態。給定恐懼狀態,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威脅迫近程度。例如,如果捕食者離得很遠或其位置未知,那麼最適合的做法可能是躲藏或僵住以避免被捕食者發現。如果捕食者處於中間距離,探測很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那麼逃跑可能是最佳策略。如果捕食者正在發動攻擊,那麼與捕食者戰鬥的防禦行為可能是最佳反應。
.jpg?w=900)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問題 3:是否存在不同的防禦迴路(例如,捕食性與社會性、生存迴路、反應性與認知性恐懼),如果是,它們是正交的還是協同的?您的立場的證據是什麼?
RA: 是的,我認為有非常好的證據表明,存在專門用於恐懼亞型的神經迴路。恐懼不是一回事。例如,在一些細節上,已經解剖了一個涉及上丘和導水管周圍灰質<0xC2><0xA0>的迴路,用於介導齧齒動物看到空中捕食者引發的恐懼行為。相反,腹內側下丘腦具有參與恐懼狀態的細胞群,並對同種的聲音或氣味做出反應,但不對空中捕食者做出反應。還有與威脅迫近程度相關的不同迴路(焦慮、恐懼、恐慌)。對杏仁核損傷的人類的研究已經將對遠距離感受刺激(蛇、蜘蛛等)的恐懼與對內感受刺激(窒息)的恐懼分離開來。在不同型別的威脅需要不同的適應性行為的程度上,它們將構成不同的功能狀態——這種功能專業化應該反映在神經迴路中。這些相對“專用”的恐懼亞型神經迴路是皮質下的,而皮質的參與可能具有“混合選擇性”,這樣,相同的皮質神經元可以編碼可能需要採取的多種行動,以適應對恐懼的適應性反應,這取決於情況。
MF: 是的。例如,味覺厭惡-厭惡-毒素規避系統(Garcia 的內部環境防禦)與捕食防禦(外部環境)不同。在一個很好的演示中,Bernstein 的實驗室表明,在基底外側杏仁核內,味道(條件刺激)和毒素(非條件刺激)與情境條件刺激和電擊非條件刺激收斂於不同的神經元組。這說明了將基底外側杏仁核視為與“恐懼”同構的常見錯誤。事實並非如此;它介導了幾個厭惡和食慾動機系統,這些系統涉及杏仁核內不同的細胞和微迴路。關於純粹以杏仁核為中心的觀點的另一個擔憂是,並非所有反捕食者防禦模組都同樣依賴於杏仁核。例如,我提出了一個依賴於導水管周圍灰質多於杏仁核的近距離打擊-恐慌防禦模組。該模型預測了二氧化碳引起的恐慌發生在杏仁核雙側喪失的患者身上,而該患者在其他方面嚴重缺乏恐懼反應。不同厭惡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很像食慾和厭惡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通常是抑制性的,因為這些系統服務於不同的功能,並且一個功能可能需要優先於另一個功能;例如,透過鎮痛迴路抑制疼痛或恢復系統是恐懼和防禦系統的一部分。但也存在趨同。在齧齒動物中,防禦捕食者(物種間)和雄性首領(同種)會啟用非常相似的大腦結構和行為,這表明這些防禦存在大量的趨同進化。我的文章(補充資訊)為恐懼提供豐富(六部分)定義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幫助區分恐懼與其他系統。
LFB: 關於運動控制的神經科學研究表明,運動動作不是由簡單的、專用的迴路觸發的,而是在靈活的神經層級結構內組裝的,其運動模組位於脊髓中。我假設,對於內臟運動動作來說,情況可能也是如此。在這種觀點中,構建簡單防禦迴路分類的嘗試在科學上並不具有生成性。靈活神經層級結構的存在意味著,每種行為——例如僵住、逃跑和戰鬥——都不是一個特定迴路的結果,而是可以透過多種方式來實現。在我看來,大腦作為一個單一的動力系統,其核心任務是調節骨骼運動動作以及支援這些動作的身體內部環境中的內臟運動動作。這個想法表明,即使在相同的情況下,每種行為都存在退化組裝。此外,處理感覺輸入的神經元(例如,在 V1、初級內感受皮質中)和代表感受價值的神經元都在為動作服務,並攜帶關於這些動作的資訊,因此是動作控制的靈活層級結構的一部分。
JL: Nathaniel Daw 和我最近提出了防禦行為及其神經基礎的分類法<0xC2><0xA0>,這可能為考慮當前問題中暗示的一些不同分析層次提供一個組織框架。其中包括反射、固定反應、習慣、行動-結果行為以及受非意識和有意識審議控制的行為。例如,對捕食性和社會性線索的物種典型反應可以被認為是固定反應,當不同的,但在一定程度上重疊的皮質下“生存迴路”被啟用時,這些反應會被“釋放”。相關的還有發出生存挑戰訊號的迴路,這些迴路監測穩態失衡並啟動恢復行為。工具性習慣行為是固定的,但必須學習,並且涉及皮質紋狀體迴路,而行動-結果工具性行為是學習的,但靈活的,並且使用不同的皮質紋狀體迴路。審議性工具性反應是前瞻性的和基於模型的,並且它們啟用前額葉迴路;在這裡,關於危險的非意識審議允許快速地在精神上模擬可能的解決方案,而在較慢的有意識審議中,恐懼體驗可以指導未來的計劃和行動。
KR: 為了簡潔起見,我將重點關注“杏仁核”,它實際上是幾個細胞簇(核)的複合體,並且從最原始的哺乳動物到大多數脊椎動物都是保守的。它接收來自大腦幾乎所有感覺區域的神經投射,以及來自記憶處理區域以及聯合和認知大腦區域的神經投射。它向許多這些區域傳送投射,但最有趣的是,它還與一系列腦幹和其他皮質下區域進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迴路都參與防禦和食慾行為,更不用說捕食性與社會性行為等等。最近令人著迷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杏仁核的同一亞區域內,相鄰細胞也可能具有相反的功能或更細微的功能差異;例如,它們可能更喜歡對近端威脅而不是遠端威脅做出反應。這些發現表明,平行的資訊通路,例如編碼“恐懼開啟”與“恐懼關閉”資訊的不同細胞,流經基底外側和中央杏仁核。此外,關閉恐懼反應的相同細胞可能負責啟用積極情緒,例如食慾甚至成癮行為。因此,這些資訊通道可能更適合被理解為潛在的接近與迴避相關行為和驅動力的基礎。然而,也可能的是,當在神經迴路水平上解析這些行為時,它們與我們概述的防禦迴路的歷史術語不太匹配。
KT: 協同作用。邊緣系統中的一切都是連線在一起的,如果不是透過直接的相互連線,那麼也是透過神經調節系統連線在一起的。介導不同型別恐懼的迴路很可能匯聚到一些共同的通路,然後在行動選擇之前再次分叉。例如,動物可以透過第一手經驗學習恐懼環境刺激,也可以透過觀察他人來學習。我們知道,基底外側杏仁核 (BLA) 是將感覺資訊轉化為透過直接經驗學習的關聯的動機意義的關鍵核<0xC2><0xA0>,而觀察性恐懼學習需要 BLA 和前扣帶回皮層。前扣帶回皮層的作用是解釋演示者的痛苦並將該訊號傳送到 BLA,在那裡發生關聯學習。
問題 4:您的觀點如何(或可以)與其他人的觀點相適應?
RA: 我的功能性重點可能最接近 Mobbs 和 Fanselow 的觀點。我特別喜歡威脅迫近性理論,這當然是一種功能性理論。我將恐懼視為一種不同於恐懼意識體驗的狀態,這種觀點似乎與 LeDoux 在這方面的觀點一致。這有點諷刺,因為我不同意 LeDoux 的結論(他將“恐懼”重新定義為“恐懼的意識體驗”),但我認為他最清楚地闡述了這種區別,這很重要。我實際上會將他的觀點重新解釋為關於我們如何識別一個有機體處於恐懼狀態。我們透過擁有恐懼的意識體驗來識別自己身上的這種狀態;我們透過他們的口頭報告或行為來識別其他人身上的這種狀態;我們透過它們的行為來識別動物身上的這種狀態。如果我們想保持一致,我們應該將“恐懼”的任何含義應用於其他人類和動物,因為證據型別相同。Ressler 和 Tye 的觀點更接近神經生物學,我當然也同意許多關於恐懼的問題是經驗性問題,大多仍需解決。毫無疑問,即使在對概念或理論問題沒有任何共識的情況下,恐懼科學也將取得進展,並且確實將為概念和理論問題提供資訊。我同意即使在對哲學問題沒有共識的情況下,繼續研究神經科學也是有成效的;但我也認為我們需要繼續評估和討論哲學問題,以瞭解我們的前進方向。Feldman Barrett 的觀點既與我的一些觀點高度一致,又完全相反。我贊同她對情緒的情境依賴性的強調,特別是她對我們可以從面部表情“解讀”情緒的觀念的抨擊(事實上,我們剛剛就此合著了一篇論文)。但我不同意她的觀點,即沒有客觀標準來判斷動物或人是否處於情緒狀態或處於特定型別的情緒狀態。
MF: 與 Adolphs 的方法一樣,我強調進化需求的方法也是功能主義的一種體現;事實上,我的第一篇關於捕食者迫近性的論文的標題是“對厭惡動機行為的功能行為主義方法”。我完全贊同 Adolphs 的觀點,即“情緒是有機體的狀態,其定義在於它們的作用”。我注意到 Adolphs 和 LeDoux 都批判行為主義方法,但他們的批評是針對激進行為主義的。我的行為主義是托爾曼認知行為主義的產物,它強調行為的目的性,儘管托爾曼更關注直接或近端功能(我如何在這裡獲得食物)而不是最終功能(我為什麼要尋找食物)。事實上,與恐懼相關的行為是系統發育程式設計的,因為它們在許多世代中具有很高的成功機率,但這些行為在當前的即時情況下可能是不適應的。這也意味著這些程式設計行為的任何個體例項在當前情況下都可能無效。這就是為什麼任何特定的恐懼行為例項在當下都可能顯得,並且實際上是,不理性的。我的方法似乎與 Feldman Barrett 和 LeDoux 的觀點直接矛盾,他們的觀點認為恐懼完全是更高階的意識構建。意識的適應性功能通常被認為是提供靈活性和支援審議性的、近端理性的行為。我認為這與面對威脅的生命所必需的特徵相悖。反應必須是即時的;任何花在審議上的時間都會增加死亡的可能性。因此,這些恐懼反應是系統發育程式設計的反應。當面對捕食者時,沒有時間根據試驗和錯誤來習得行為,也沒有時間進行新的計劃。與托爾曼的對比再次具有啟發意義。托爾曼強調達到固定目的的可變手段;如果你有一張認知地圖,揭示了食物的位置,動物可能會使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獲取食物。這個想法與 Feldman Barrett 對運動系統中一對多對映的描述非常相似。但托爾曼的理論是基於對食物強化物的實證研究,在這種情況下,相當大的靈活性不僅可以容忍,而且是有益的:如果你錯過一頓飯,你不會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可能會帶來更豐富的食物來源或前一頓飯中沒有的營養。防禦的需求完全不同。因此,齧齒動物研究最多的覓食反應——槓桿按壓,在受驚的大鼠中幾乎不可能進行研究。
LFB: 從經驗上看,科學發現構成了關於恐懼的神經生物學基礎的未被發現事物的一小部分。我的科學方法在指導本體論承諾方面與指導當前恐懼本質研究的方法有很大不同。
JL: 每位參與者都為自己的立場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據。我很高興閱讀這些文章,並且我學到了一些關於每位作者想法的新知識。我對恐懼的意識體驗的想法與 Barrett 的想法重疊,因為我們都將恐懼視為一種認知組裝的狀態,它基於情境的心理模型和概念化。對我來說,其他有助於恐懼的因素或成分,例如大腦喚醒和來自身體反應的反饋,會調節但不會決定體驗的質量。另一方面,我對諸如杏仁核等大腦區域在檢測威脅和啟動身體反應中的作用,以及在引導工具性行為的由此產生的動機狀態中的作用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與其他貢獻者的觀點相符。我們爭論的大部分內容是語義上的——在存在威脅的情況下,恐懼是體驗本身還是威脅觸發的各種後果?但說差異是語義上的並不意味著它們不重要。文字是強大的。它們是我們概念的基礎,塑造了我們理論觀點的含義,並影響他人對我們研究的結論。我們應該盡最大努力消除科學用詞中的歧義和混亂。我們的詞彙表為我們提供了做到這一點的方法,我們應該在科學地使用語言時利用我們語言的微妙之處。一個簡單的開始方法是避免使用心理狀態術語來描述不基於心理狀態的行為。在人類中,我們可以區分這些,因此當然應該避免使用心理狀態術語來描述動物的行為,而在人類中,類似的反應不受主觀體驗的心理狀態控制。我認為諸如威脅性刺激、防禦性反應和防禦性生存迴路等詞語比恐懼刺激、恐懼迴路和恐懼反應更能描述動物的刺激-反應關係。
KR: 在大多數方面,我同意其他觀點,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在陳述更廣泛的共同理解的相似方面,但存在細微的差異。我認為我的觀點最關注的是,在人類神經精神病學研究中,厭惡行為和與恐懼相關的疾病的科學,或許還有食慾行為和成癮的科學,對於臨床轉化而言是最成熟的。具體而言,我同意 Adolphs 的觀點,即“像恐懼這樣的情緒的功能主義觀點需要跨學科的方法”。我同意 Fanselow 對恐懼的定義特徵——一種形式主義方法,我認為這種方法非常有用,特別是在區分焦慮、恐懼和恐慌之間不同功能模式的不同體驗狀態方面。我同意 Barrett 的觀點,即恐懼的特徵“包括一些身體變化(自主神經系統變化、化學變化、行為等)和感覺,這些感覺變成了對周圍世界和身體的感知”。我同意 LeDoux 的觀點,即“恐懼是一種意識體驗,在這種體驗中,你開始相信自己即將受到傷害”,並且同意 Tye 關於由“分別決定重要性(或顯著性)、效價和行為的三個心理過程”組成的概念模型的重要性。雖然我也同意許多細微的、哲學的、心理學的、行為的和基於神經科學的定義,但我不想忽視已經取得的進展以及“恐懼”的概念對於轉化神經精神病學的強大作用。
Q5:當前用於研究恐懼的行為分析是否限制了我們提高對恐懼的理解能力?
RA: 當代的分析方法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它們比較了動物研究和人類研究中的蘋果和橘子。動物中有很多種恐懼的行為分析方法,但基本上沒有一種用於人類研究中,人類研究通常使用口頭報告作為真實依據。由於不可能在動物中使用口頭報告,因此原則上解決方案似乎很簡單:我們需要將動物研究中的行為量表調整到人類研究中。只有少數研究嘗試過這樣做。當然,另一個挑戰是生態效度。Mobbs 對將狼蛛越來越靠近你的腳的研究,而你正在掃描器中,是這個方向上罕見但經典的成功案例。這個問題也延伸到使用的刺激物。許多研究向人類受試者展示情緒的面部表情,或讓他們閱讀簡短的小插曲。這些研究可能顯示了一些關於社會感知或人們關於恐懼概念的語義知識,但它們並沒有評估恐懼的實際狀態。我非常擔心大多數研究人類恐懼的實驗方案的不充分性,這些方案使人類恐懼的研究與動物恐懼的研究脫節。人類研究需要更具生態效度的刺激和更好的行為分析方法,特別是那些不依賴於口頭報告並且可以被認為與動物研究中使用的行為分析方法具有某種同源性的方法。
MF: 巴甫洛夫恐懼條件反射是獵物識別捕食者的自然組成部分,並且在實驗室中效果很好。但它的成功也伴隨著危險。這些危險之一是,它導致過度強調威脅連續體中的一個模組(遭遇後恐懼),而我們對其他組成部分(臨近攻擊恐慌和遭遇前焦慮)的瞭解則滯後。也許更大的危險是將程式視為與過程同構的趨勢。從程式上講,恐懼條件反射被定義為將中性刺激與厭惡性刺激配對,但此程式不會總是條件反射出恐懼狀態,因為並非所有厭惡性刺激都支援反捕食者防禦系統的參與。毒素顯然是一種厭惡性刺激,但將中性味道與毒素配對會導致適口性轉移,從而減少消耗,而不是反捕食者防禦。同樣,一些電擊足夠新穎和強大,可以條件反射出恐懼,但另一些則不然;輕微的電擊很可能令人惱火,但不足以條件反射出恐懼。大鼠在非常微弱的電擊下行為更靈活,但隨著電擊強度的增加,這種靈活性逐漸喪失。我將這種行為靈活性的喪失視為恐懼狀態的診斷。因此,在選擇電擊強度或讓受試者選擇電擊強度時必須謹慎。此外,人類恐懼研究中常用的其他結果,例如金錢損失,不太可能觸及支援反捕食者防禦的神經系統。
LFB: 當代正規化,在簡單、專門的恐懼神經迴路的概念指導下,以單一分類法排列,在幾個重要方面限制了對恐懼的研究。首先,恐懼例項通常在實驗室環境中進行研究,這些環境與它們自然出現的倫理學環境大相徑庭。所有潛在的行動都有能量成本,動物的大腦會在特定環境中權衡這些成本與潛在的回報和收入。因此,關於行動的經濟選擇必然會受到許多特定情境的考慮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涉及動物的狀態和環境狀態,其中大多數因素在典型的實驗室實驗中保持不變。這些因素不僅影響執行哪種防禦行為(正如某些防禦行為分類法所建議的那樣),而且還影響任何給定行為的實施方式。忽視這些因素會使防禦行為的神經原因顯得比實際情況更原子化,因此,大多數當代正規化都不夠整體(參見我對問題 2 的回答)。其次,當代正規化混淆了應該分開的事物。例如,區分情感和情緒非常重要。諸如效價和喚醒等情感特徵最好被認為是更高維度內感受的低維摘要,這些內感受來自異速穩態;效價和/或喚醒在情緒發作期間可能很強烈,但並非特定於這些發作。由於異速穩態和內感受在動物的生命中持續進行,因此效價和喚醒可能是描述該生命中每個清醒時刻的心理特徵。為了使這種說法在比較人類和非人類動物時有意義,有必要區分大腦的意識能力(一種體驗)和它的覺察能力(報告或反思體驗的能力);相關地,區分以特定方式感知直接情境的感官特徵與覺察到該感知(例如,覺察到感知到威脅)以及覺察到感到恐懼非常重要。同樣重要的是不要將威脅性刺激與威脅出現的背景混淆,這在恐懼分類法中經常發生;大腦不會感知刺激,它們感知感覺陣列,即情境中的“刺激”。也許最重要的是,不應混淆觀察和推斷。科學家測量諸如骨骼運動動作(例如僵住)和支援這些骨骼運動動作的內臟運動動作(例如心率變化)等事物,他們可能會將其稱為“恐懼”;相應地,他們測量支援這些動作的神經放電變化,他們可能會將其稱為“恐懼迴路”。這種方法混淆了觀察到的事物(例如,僵住,心率變化)與它們推斷的原因(例如,恐懼)。如果兩者不經常混淆,恐懼科學將更有效率,更具生成性。當科學家觀察到動作並推斷出恐懼的例項時,科學家正在進行情緒感知。恐懼始終是一種感知——一種推斷——無論是在科學家觀察動物的動作時,人類觀察另一個人的人的動作時,還是動物在理解其感官環境以作為行動控制的一部分時。自主神經系統或骨骼運動動作的任何變化本身都沒有恐懼的意義。大腦透過推斷(也可以描述為預測訊號或臨時概念)使它們具有恐懼的意義。動物的大腦——人類或其他——在沒有意識到這樣做的情況下進行這些推斷。從這個角度來看,理解推斷的神經生物學基礎是理解恐懼神經生物學的一部分。
JL: 當然,恐懼研究的一個主要內容一直是“恐懼”條件反射正規化。它產生了大量關於大腦如何檢測和響應危險的有用資訊。它也可以用來探測人類參與者的意識體驗。但是在非人類動物的研究中,由於在其他地方詳細討論過的原因,研究人員只能測量行為和生理反應。因為類似的反應,包括杏仁核啟用,可以在人類中使用未被有意識地感知並且不引發恐懼感報告的閾下刺激來引發,所以恐懼的體驗似乎不是驅動反應的原因。因此,杏仁核迴路可能被更好地認為是威脅迴路或防禦迴路,而不是恐懼迴路。因此,限制不在於我們的正規化;相反,正規化揭示了當使用這些正規化時,可以從動物與人類身上學到的東西的侷限性。然而,我們對恐懼的理解受到其他事物的限制。一是真正令人恐懼和創傷性的情況,出於倫理原因,不能用於恐懼的實驗室研究;較溫和的替代品只能給我們一些暗示,因為大腦反應不會隨刺激強度線性縮放。另一個是概念上的自滿和語言的隨意使用。如上所述,流行的恐懼和恐懼條件反射觀點與莫厄和米勒可以追溯到 1940 年代的概念化有關。“恐懼條件反射”一詞暗示該任務揭示了恐懼是如何產生的。如果一個人像我一樣將恐懼視為一種意識體驗,那麼恐懼條件反射(或我稱之為“威脅條件反射”)原則上可以在動物研究中用於幫助理解間接促進恐懼的過程;但它不能揭示人類恐懼體驗的潛在機制,而人類恐懼體驗只能在人類中研究(我不否認動物意識是一種自然現象,但質疑我們是否可以科學地研究它)。我認為,使用諸如“恐懼”之類的心理狀態詞語來描述行為控制系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混亂,並導致對動物研究可以和不能告訴我們什麼產生錯誤的期望。因此,如果有人使用“恐懼”一詞,那麼他或她應該每次使用該術語時都澄清“恐懼”的預期含義(例如,新增諸如“有意識”或“無意識”或“顯性”或“隱性”之類的形容詞)以避免混淆。從一開始就將有意識的“恐懼”與無意識的“威脅處理”分開將避免這種混淆。
KR: 當前研究臨床前模型系統中恐懼的最常見方法是基於巴甫洛夫恐懼條件反射模型——檢查恐懼記憶的習得、表達、消退等不同的記憶相關結構——並使用僵住、迴避和驚嚇的行為指標。同樣,在大多數人類模型中,實驗室試圖進行受控實驗,但通常使用自我報告或生理結果指標(例如,皮膚電反應、心率或聽覺驚嚇)。大多數轉化研究的一個侷限性是,人類和模型系統研究通常不使用相同的正規化和相同的結果指標。此外,使用良好控制的學習正規化使得明確定義與先天或無條件恐懼線索、過程和行為相關的途徑和公認的迴路變得更加困難,尤其是在動物模型系統中。一般來說,實驗正規化越受控和還原論,就越難觀察和量化自然的威脅反應模式及其潛在的生物學。
KT: 我認為,對於巴甫洛夫恐懼條件反射來說,擁有一個非常刻板的行為正規化,有助於提高重現性,並更深入地研究解剖學和機制(用於在齧齒動物中將純音與共同終止的足部電擊配對)。然而,還有許多其他型別的恐懼尚未被充分研究或根本沒有研究過,這使我們對恐懼的理解更深入但廣度較小。目前,絕大多數關於“恐懼”的出版物都指的是一種非常具體的正規化,這種正規化只是這種情緒狀態神經機制的一個很小的子集。
Q6:動物模型能否為我們提供關於人類恐懼模型的資訊(反之亦然)?
RA: 我會說動物研究對於理解恐懼至關重要,因為與人類相比,它們可以進行更好的測量和操作——兩者都不是任何事物的“模型”。動物研究調查動物恐懼;人類研究調查人類恐懼。毫無疑問,不同物種之間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而且某些動物將具有功能性定義的恐懼狀態,而這些狀態在其他動物中完全不存在(生活在沒有空中捕食者環境中的動物將不具有涉及上丘的迴路,該回路處理小鼠中該型別的威脅)。我實際上更喜歡動物研究而不是人類研究的原因是,它們可以簡化我們正在尋找的東西。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人類研究通常將對恐懼的研究與對恐懼概念、恐懼的意識體驗或恐懼的口頭報告的研究混合在一起。老鼠當然沒有口頭報告,不太可能有概念,我們也不知道如何測量它的意識體驗——當面對威脅時,它只是處於功能性定義的恐懼狀態。在動物身上也更容易誘導生態有效的恐懼(它們不知道自己正在進行實驗),而且動物更難隨意調節自己的情緒。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在動物身上研究真實、強烈的情緒遠比在人類身上研究容易,並且應該是神經科學家開始的地方。
MF: 當然,它們可以並且已經提供了資訊。沃爾普開發的暴露型療法是從巴甫洛夫和赫爾的動物研究中汲取靈感的,並且仍然是焦慮症的標誌性治療方法。Mobbs 提供了對捕食者迫近性理論的複雜擴充套件,使其能夠捕捉人類情緒的許多獨特特徵。
LFB: 動物模型可以為我們提供關於人類恐懼例項的資訊,但目前存在一些障礙。首先,大多數動物研究僅在少數模型物種中進行,並且未能考慮不同物種基於大腦和基於生態位的特徵的異同,以及作為神經典型人類大腦發育和功能的模型系統。大多數主要大腦部分的計算作用在整個脊椎動物譜系中仍然是保守的,所有大腦都可以被描述為自動且毫不費力地形成推斷(即臨時概念),以分類預期的感覺輸入並指導行動。但由於一般大腦縮放功能和動物生態位中可用的資訊,物種可能在大腦可以構建的概念型別上有所不同。例如,與其他靈長類動物相比,人類大腦具有擴充套件的聯合皮層,從而能夠提高資訊壓縮和降維;這表明人類大腦可能能夠建立以更抽象為特徵的多模態摘要。這一假設絕不會削弱與生存相關的行為在人類情感中的重要性,也不會使在動物模型中研究與生存相關的行為以理解人類情感生物學的目的而無效。然而,它確實表明,解決人類情感之謎——以及更普遍的人類進化——可能需要一門“情感生態學”科學,試圖理解物種通用和物種特有的過程。此外,實驗動物通常在貧乏的實驗室環境中飼養,與自然倫理學環境中典型的感測器運動挑戰範圍相比,它們遇到這些挑戰的機會更少;這可能會影響發育過程中的大腦佈線,從而引發實驗室動物是否甚至是“神經典型”的問題。
JL: 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但細節取決於所涉及的動物以及人們對恐懼的理解。無脊椎動物可能為我們提供關於哺乳動物(包括人類)威脅學習的細胞和分子機制的資訊。非靈長類哺乳動物可能為我們提供關於檢測威脅和控制各種反應(例如,反應、習慣、工具性行動)的迴路的資訊。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可能為我們提供關於支援審議性認知的皮質迴路的資訊。但在每種情況下,儘可能驗證研究結果與人類的相關性都很重要,方法是在人類中進行近似於動物研究的研究,儘管神經生物學細節較少。人類研究對於研究恐懼和其他情緒的意識體驗也是必要的。這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方法論障礙限制了對非人類動物意識的評估。正如傑弗裡·格雷所說,我們只能使用非人類的行為代理來逐步接近意識。雖然存在缺陷,但口頭報告是人類的強大工具。我們通常可以對我們有意識的資訊做出口頭或非口頭回應,但只能對我們缺乏意識的資訊做出非口頭回應;僅憑非口頭回應,很難區分其他動物的有意識和無意識處理。其次,即使我們假設某些非口頭測試揭示了非人類動物意識的某些方面,但鑑於人類大腦在語言、分層認知、概念化、前瞻性認知和自我反思方面的獨特能力,意識的本質很可能大相徑庭,我認為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恐懼和其他情緒體驗。
KR: 雖然很明顯,很少有(如果有的話)動物模型能夠完全代表人類神經精神疾病的複雜性,但有大量證據表明物種之間——從老鼠到人類——對於基本行為(包括許多防禦性威脅反應及其潛在迴路)是保守的。資料有力地表明,食慾性和厭惡性行為分別是成癮綜合徵和與恐懼相關的疾病(如恐懼症、焦慮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的潛在現象。此外,皮質下杏仁核、紋狀體終紋床核 (BNST)、紋狀體、海馬和腦幹迴路,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皮質調節區域的各個方面,在哺乳動物中在形式和功能上高度保守。數十年的工作已經建立了一個清晰的迴路,該回路在人類成像和生理學研究以及使用現代工具(如光遺傳學、化學遺傳學、鈣和電生理學工具)的齧齒動物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證實。雖然還需要建立更多,但強大的方法,如跨區域和物種的單細胞 RNA 測序、與轉錄組學相結合的大規模遺傳工具以及跨物種的數字表型分析,正在實現真正新穎而強大的轉化方法,這些方法本身並不模擬疾病,而是模擬其組成部分,從分子到迴路,再到構成防禦性“威脅”到“恐懼”連續體的行為語法的各個方面。
KT: 新技術和方法可以增強我們對恐懼的理解,因為它們可以促進我們對大腦回路和一般功能的理解。恐懼條件反射通常是用於驗證新技術的第一個原理驗證行為正規化,因為它非常穩健且可重複。
Q7:新技術和方法如何增強我們對恐懼的理解?
RA: 人們已經非常關注提高對大腦的測量和操作的精確度,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提高刺激和行為測量的有效性。只有少數研究使用了高維度、多變數的行為測量方法。例如,可以測量烏賊用來偽裝自己的數萬個小色素細胞的身體表面變化,這種測量方法據稱可以直接讀取動物的感知狀態。人類的豐富測量方法似乎也是可以實現的:我們需要詳細測量人們在 3D 空間中的運動、他們的全身血流等等。在刺激端,最好的刺激是真實世界,在動物的自然環境或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進行的研究將有助於提高實驗室研究的有效性。虛擬現實可能在這裡有所幫助。當然,行為並非一切(恐懼的功能不僅僅是引起行為);與其他認知過程的相互作用對於量化也很重要。在理想情況下,我們不僅會探測當呈現生態有效的威脅刺激時行為如何隨時間變化,還會探測這如何影響記憶、注意力、感知和決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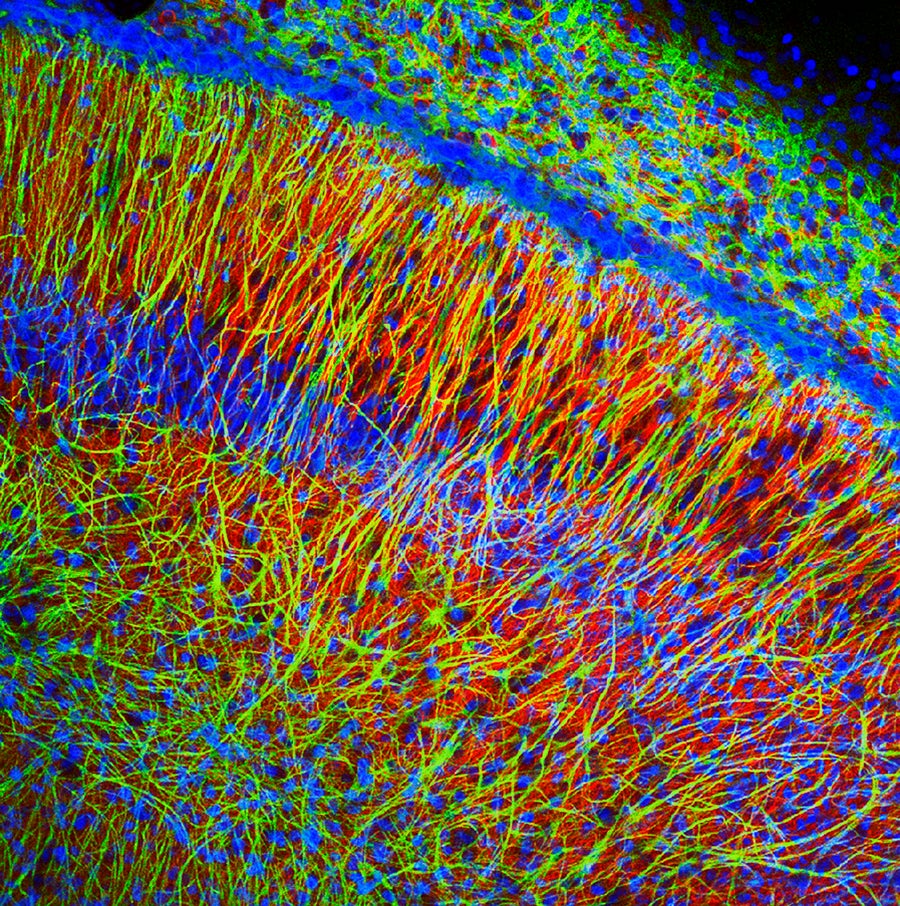
MF: 尤其有用的是我們能夠繪製參與不同情境和行為的大型細胞網路圖譜。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透過即時早期基因成像技術(如 catFISH)實現的。在上面,我描述了伯恩斯坦的研究,該研究使用這種方法證明,味覺厭惡和恐懼條件反射激活了很大程度上獨立的杏仁核網路,這有助於我們區分兩種厭惡動機系統。新型可植入顯微鏡也為增進我們的理解帶來了巨大的希望。但是,我們對現象的概念性理解不能為這些技術成就所犧牲;兩者必須攜手並進。
LFB: 新技術和方法可以透過提供以下能力來增強我們對恐懼的理解:在更廣泛的、高度可變的行為學背景下,使用更高維度的測量程式以及改進的時間和空間特異性來觀察動物。測量和建模自然情境變異的能力至關重要,特別是對於遺傳研究而言;與個體差異相關的、使動物易患疾病的大多數遺傳變異都位於基因組的非編碼區域,這些區域受到情境的強烈影響。
JL: 今天可用的新方法正在徹底改變大腦研究。但有時方法似乎優先於問題。只有當我們充分概念化問題時,新方法才能幫助我們。設計不良的研究帶來的複雜性相對容易糾正——只需做一個更好的實驗即可。概念性問題更難改變。想法變成教條,而教條通常不會受到質疑;新方法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很高興在這個練習中,我們退後一步,評估我們在概念上相對於我們需要達到的位置。
KR: 一系列奇妙的新型分子工具,從光遺傳學到化學遺傳學再到體內動態成像,使得對細胞、分子和途徑的功能解剖成為可能,這些細胞、分子和途徑突出了威脅處理和抑制。理解這些過程將為控制特定型別的情緒反應,特別是恐懼和威脅,提供新穎而可靠的見解。從轉化角度來看,這種細胞水平的行為控制精度帶來了非凡的可能性。透過單細胞 RNA 測序,我們現在可以評估細胞型別和微迴路是否在小鼠和人類之間是保守的。此外,我們可以詢問這些保守的通路是否也共享分子靶點,以便人們可以將資料分析和生物資訊學應用於理解可能特異性抑制保守恐懼迴路或增強消退回路的藥物組合。例如,即使在人類中,我們能否使用腦刺激技術甚至基因療法以可靠的治療方式靶向恐懼迴路?
結論性評論
經過這次討論,我們能否就恐懼的定義達成一致?
RA: 我認為我們應該謹慎地為修訂和發現留出空間,而不是僵化地“定義”恐懼。也許我們可以就以下幾點達成一致:(i)恐懼涉及大腦的特定區域,尤其是明顯的皮層下區域。我們可以透過操縱特定的神經迴路(例如,杏仁核)而不是其他迴路(例如,小腦)來測量和誘導恐懼。這些迴路是否是恐懼特有的,這是一個進一步的經驗問題。我們可以初步列出參與恐懼的特定腦結構的證據強度。(ii)恐懼有亞型、變體或維度。我主張,首先,根據功能標準對其進行區分。我們也可以在這裡列出清單。(iii)恐懼狀態、恐懼的意識體驗、“恐懼”概念的含義以及“恐懼”這個詞的含義都是不同的事物(後兩者只能在人類中研究)。如果你給人們詞語或故事來評分,你正在測試後兩者。制定分類法或術語表將很有用。
MF:幾種方法(阿道夫斯、雷斯勒、泰伊和範瑟洛)似乎都將進化方面的考慮以及恐懼表達之間的共性作為核心。重要的是,這些方法認識到可以從所有恐懼測量中學習到一些東西。勒杜和費爾德曼·巴雷特與眾不同。在我看來,他們的方法受人類傾向於美化口頭報告而忽視所有其他測量的影響。因此,障礙在於同意將口頭報告視為資訊性的,但並非唯一的資訊來源。勒杜對支援恐懼意識報告的迴路的描述承認,杏仁核和反捕食者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有顯著的輸入。我相信費爾德曼·巴雷特的描述也是如此,儘管她沒有討論明確的迴路。產生任何個體恐懼反應的迴路將有兩個組成部分。一個組成部分來自核心防禦迴路,這對於所有恐懼反應都是相似的。但也會有第二個組成部分提供特定資訊以及執行特定反應所需的處理。這對於僵住和口頭報告來說都是如此。每種反應都會有其獨特的子迴路,其中一部分將屬於所有恐懼反應共有的基本回路。每種反應都反映了恐懼和其他情境資訊。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那麼我們可能就接近達成共識了。即使像僵住這樣看似簡單的事情也是一個複雜的構造。啟動僵住的基底外側杏仁核神經元的放電是短暫且瞬時的,需要在其他地方轉換為維持持續運動反應所需的放電模式。我們稱之為僵住的運動模式在姿勢上差異很大;僵住的大鼠可以蹲在地上,也可以後腿站立並靠在牆上。這與費爾德曼·巴雷特對“多對一”反應對映的描述非常相似,其中僵住的“意圖”是透過不同的運動計劃來實現的。僵住不會發生在隨機的地方:動物更喜歡在牆壁附近、角落和黑暗的地方僵住。因此,僵住子迴路處理與訊號危險的感官刺激完全不同的視覺情境資訊。過去的經驗也會影響當前的行動。這些多重資訊流必須以支援每個僵住例項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因此,即使是僵住,用費爾德曼·巴雷特的話來說,也是“高度情境依賴性和可變的”。也許我們並沒有那麼大的分歧。
LFB:我樂觀地認為科學家們可以就恐懼的定義達成一致,但這將要求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一些本體論承諾以及構成我們實證探究基礎的哲學假設。恐懼科學(以及更廣泛的情緒科學)中的一些爭論是哲學性的,而不是科學性的,因此不太可能透過實驗或資料來解決。儘管如此,像這樣的討論還是值得進行的,因為承諾和假設是概念工具,它們會影響(和約束)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產物。
JL: 我們正在討論的根本問題是主觀體驗在情緒科學中的作用。它是情緒的眾多方面之一,還是情緒的全部意義所在?這是情緒理論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我們在這裡討論這個問題,彷彿它是一個新穎的話題,是因為許多當代關於恐懼的大腦機制的研究都涉及恐懼條件反射,而恐懼條件反射在很大程度上與主流情緒理論隔離。我在 1970 年代後期的博士論文包括對裂腦患者情緒意識的研究,並向我介紹了情緒的認知理論。從那時起,我就將情緒視為認知組裝的狀態,並試圖將關於情緒的認知思維整合到“恐懼”條件反射(或我稱之為“威脅條件反射”)領域。但這一直是一場艱苦的戰鬥。例如,在 1980 年代後期,我的一位行為主義傳統同事問我,“你為什麼用情緒來談論恐懼條件反射?” 如今,無論好壞,情緒談論在動物厭惡條件反射領域相當普遍。但是,情緒的概念通常仍然受到 1940 年代米勒-莫勒行為主義“恐懼理論”的嚴重影響,該理論將條件反射的“恐懼”視為迴避行為的潛在因素。雖然行為主義傳統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在托爾曼傳統中,將動物的恐懼視為一個介入變數,一個假設的“中心狀態”(例如,一個假設的非主觀心理或生理狀態),可能將刺激與行為聯絡起來,但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一種主觀的意識體驗;然而,大多數人沒有在這兩種觀點之間表態,這造成了很多混亂。關於人類恐懼的大腦機制的研究也經常以混淆行為和生理反應與主觀體驗的方式使用“恐懼”一詞,進一步加劇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混亂局面。正如我上面指出的,參與本次討論的一些參與者之間的分歧主要是語義上的。但是,正如指出的那樣,語義對於我們的概念和假設至關重要。表達不同的想法是件好事。長期以來,人們談論恐懼的方式暗示著我們都意味著相同的事情。既然不同的概念正在公開討論,正如我上面建議的那樣,研究人員應該更嚴格、更警惕地定義每次使用“恐懼”這個詞時各自的含義,以便其他人能夠理解在給定例項中指的是什麼。我更喜歡的、不那麼繁瑣的替代方案是簡單地將恐懼限制在恐懼本身。正如社會心理學家馬修·利伯曼最近所說,“情緒就是情緒體驗”。更籠統地說,像恐懼這樣的心理狀態術語應該用來指心理狀態,而不是指行為或生理控制迴路。
KR: 我相信我們可以就一個定義達成一致。我認為大多數人已經說明了人類意識覺醒成分子集的一些共同理解,以及人類和模型系統中可觀察到的生理和行為成分。我認為,將效價、顯著性和行為(或感覺、感知和行為)描述分開將有助於解決一些語義問題。此外,我認為,專注於實用主義而不是理論將有助於提高制定可行定義的效率。
在您看來,對恐懼的明確定義有哪些臨床意義?
RA: 臨床意義是巨大的。可能最好的證據是勒杜和派恩的論文,以及範瑟洛隨後的反駁。勒杜和派恩認為,在齧齒動物身上研究的抗焦慮藥物的效果並不能說明恐懼的意識體驗,這就是為什麼抗焦慮藥物在緩解人類恐懼方面效果不佳的原因:它們的目標是錯誤的。例如,一種讓抑鬱症患者真正清醒和活躍並讓他們早上起床的抗抑鬱藥,如果他們仍然感到抑鬱,則無濟於事。這只是一個例子,但它表明,當我們研究動物和人類的恐懼以及當我們測量或操縱其神經成分時,弄清楚我們正在研究什麼非常重要。
MF: 恐懼的科學定義必須幫助我們理解恐懼的臨床表現。讓我們從我看到的兩個大問題開始。首先,為什麼焦慮症如此普遍?在其他地方,我將此描述為在評估威脅存在時,命中與未命中成本和收益的自然且可預測的後果。其次,為什麼焦慮症如此有害?在沒有實際危險的情況下,恐懼、焦慮和恐慌是沒有益處的,那麼為什麼認識到這一事實並不能使焦慮症消失呢?我認為這是啟動了一個系統的結果,該系統的策略是由在系統發育而不是個體發育過程中起作用的偶然性決定的。我還回到我的觀點,即如果意識進化是為了實現靈活和理性的決策,那麼焦慮症的特徵是缺乏靈活性和理性行動,這表明意識的貢獻是有限的。我並不是說沒有貢獻,但我們必須用臨床情況的事實來緩和我們的結論。
LFB: 理解恐懼的神經生物學基礎的一個目標是幫助治療和預防精神和身體疾病中與情緒相關的症狀。只有當我們結合更廣泛的證據實際表明的關於神經系統的進化和發育的情況來考慮恐懼的機制和特徵時,才能實現這一目標。進化發育方法要求考慮更廣泛的證據實際表明的關於人類神經系統的特徵,這些特徵是深度進化保守的,還是在人類與非人類大腦發育過程中出現的特徵。此外,科學家應該理解,強烈暗示恐懼和/或焦慮的疾病,例如 PTSD,不是特定的“恐懼”障礙;這對於如何理解、治療和預防這些疾病具有重要意義。
JL: 面對突如其來的危險,我們通常有意識地體驗到恐懼,並做出行為和生理反應。由於體驗和反應常常同時發生,我們感覺它們在大腦中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都是恐懼模組的後果。這是一種普遍而流行的恐懼觀點,它導致人們尋找藥物和行為療法,以減輕患有恐懼或焦慮症的患者的主觀痛苦。由於行為和主觀反應都被認為是恐懼模組的產物,因此也假設改變動物行為的治療方法將改變人的恐懼和焦慮。很少有人聲稱這項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一些研究中發現了相對於安慰劑對照組的微小但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但對於任何個體而言,成功治療的機會都遠低於期望值。即使成功,副作用也會帶來其他問題。但與我們這裡關注的問題更相關的是,這些治療方法在奏效時,為什麼會奏效。是因為治療直接改變了主觀體驗的內容,還是因為它間接影響了體驗(例如,透過降低大腦喚醒、身體反應的反饋),還是因為它影響了有助於體驗的認知過程(情景記憶和語義記憶;分層審議、工作記憶、自我意識),還是所有這些?對於患者來說,治療方法如何起作用可能並不重要,但為了找到新的和更好的藥物,瞭解潛在的作用機制至關重要。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概念化,不僅要概念化大腦如何控制威脅引起的行為和生理反應,還要概念化威脅如何產生恐懼的意識體驗——這隻能在人類身上探索。經過幾十年的邊緣化,被視為“僅僅是恐懼的另一種衡量標準”,心理學、神經科學和各種心理治療界對意識(包括情緒意識)重新產生了興趣——不僅僅是因為主觀體驗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還因為它在我們的生活中起著核心作用,並且必須是治療的核心部分。
KR: 恐懼處理障礙(以及相關的恐慌和焦慮),從恐慌症、社交焦慮症和恐懼症到 PTSD,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影響著全球數億人。總的來說,它們也是發病率、工作損失、合併精神和內科疾病以及自殺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儘管有這些不幸的統計資料,但我們對這些疾病的瞭解還算不錯,並且有合理的治療方法。這些疾病都具有恐懼和威脅相關症狀的核心情緒。在所有這些疾病中共享的驚恐發作的診斷包括心跳加速、出汗、胸痛、呼吸困難、失控感以及恐懼、恐怖、末日來臨和死亡感——基本上是“失控的恐懼反射”!那些患有焦慮症的人一直都在體驗在威脅情況下“正常”的反射和症狀——就好像他們無法“關閉”恐懼開關一樣。此外,對這些疾病最有效、經驗證有效的治療方法依賴於重複暴露,現在被理解為“恐懼消退”的過程。我們對恐懼和威脅處理機制、其潛在神經迴路和分子生物學的理解的進步,以及恐懼抑制和消退方法的改進,將有助於推進這些毀滅性疾病的治療和預防。
未來研究(和資助)應該努力填補的一個重要空白是什麼?
RA: 整合性的、跨物種的研究。現在,對恐懼(和其他情緒)的研究就像盲人摸象。每個實驗室要麼研究人類,要麼研究單一動物模型,並且每項研究都側重於恐懼的狹隘方面。我們需要弄清楚如何將所有這些整合在一起。我並不是建議一個研究所有物種和人類的大型專案,但我們應該制定一套科學界可以使用的標準化實驗協議——特別是,這些協議及其措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跨越物種。目前,對動物和人類恐懼的研究實際上是脫節的,如果要取得進展,就必須改變這一點。我們需要統一的標準來評估論文和資助,並建立恐懼的累積科學。不用說,現在常見的可重複性和資料共享標準也應該適用。
MF: 目前神經科學的技術發展既重要又令人歎為觀止,但我們不足之處在於概念發展和推進行為的形式理論。如果沒有概念發展,使用這些工具收集的資料可能而且經常被嚴重誤解。雖然本次討論的一些貢獻者對行為主義的影響表示遺憾,但我認為一個更成問題的趨勢是對行為的直覺和通常擬人化的方法,這種方法是目前正在進行的許多技術最先進的神經科學的特徵。這種告誡是行為主義最初發展的主要動機。再次,我注意到上面關於行為主義的負面評論是針對過時的行為主義形式,學習理論家在幾十年前就拋棄了這種形式,因此這些評論可以被認為是稻草人論證。行為至關重要,不僅因為它允許客觀觀察,還因為它是有機體與選擇壓力聯絡的地方。仔細觀察情緒激動的動物表明,行為常常是非理性的,我們關於如何解釋行為的直覺很可能會失敗。我將“捕食迫近理論”稱為一種功能行為主義方法,因為它的思想源於對進化和行為地形的關注。
LFB: 每種行為都是關於動物全球能量預算的經濟決策的結果,並且涉及估計動物在其行為學背景下相關的各種時間視窗內的支出和存款,同時考慮到動物當前的生理狀況。如果要從進化和發育的角度理解恐懼,那麼就必須在這些經濟決策的現實中研究恐懼,因為它們出現在動物的行為學背景中。必須更加關注基本代謝和能量調節,包括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的細胞呼吸。必須考慮預測處理方法,而不是刺激-反應方法。並且必須考慮在所有分析層面上的變異和退化,以及神經重用。
JL: 我的觀點是,阻礙進步的最大障礙是我們的概念以及我們用來描述心理結構的語言。我個人的偏好是,在討論控制行為的相對原始的過程時,應該避免使用諸如恐懼之類的心理狀態術語;心理狀態詞語應該僅在專門指心理狀態時使用,例如恐懼的意識體驗。
KR: 我同意泰伊的觀點,即“鑑於恐懼在生存中的關鍵重要性及其對大腦其餘部分的權威控制,恐懼應該成為神經科學中研究最廣泛的主題之一,儘管由於其主觀性,它落後於感覺和運動過程的研究。” 我認為它是行為和轉化神經科學中最容易實現的“最低垂的果實”之一,並且解釋性科學——從分子到細胞到迴路到行為——將為神經科學和神經精神病學的其他領域提供變革性的範例。我認為當前的差距包括本次討論中提出的許多問題,例如效價、顯著性、感知和行為如何在神經迴路水平上分離。捕食性與社會生存迴路之間以及反應性恐懼與認知恐懼之間是否存在關鍵差異?在細胞迴路和微迴路水平上,構成威脅處理基礎的不同成分和行為有多麼離散?最後,從轉化的角度來看,分子、細胞和迴路在人類中是如何保守的——哪些構成了具有不同機制的相似行為的趨同進化,哪些代表了在齧齒動物和人類中基本相同的真正保守機制?
KT: 該領域將極大地受益於其他正規化,這些正規化是獨特的但又是刻板的,以便促進圍繞它的關鍵研究質量,就像巴甫洛夫恐懼條件反射所經歷的那樣,以便真正能夠進行比較。
總結
我們在理解參與恐懼的神經迴路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是一項跨物種的努力,但——正如這裡討論的那樣——在如何調查和定義恐懼方面存在差異。我們希望這裡提出的辯論,代表了該領域一些傑出研究人員的觀點,將激勵社群統一對恐懼(及其亞型)的明確定義,並展現出勇氣去追求新的行為測定,這些測定可以更好地區分參與感知、感覺和行為的恐懼迴路(或概念)。其影響將是深遠的,因為對哪些神經系統參與恐懼和恐懼學習缺乏連貫性將阻礙科學進步,包括對人類情感障礙(如 PTSD、焦慮症和恐慌症)的研究。也就是說,我們如何定義恐懼決定了我們如何研究這種情緒。
本文經許可轉載,最初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首次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