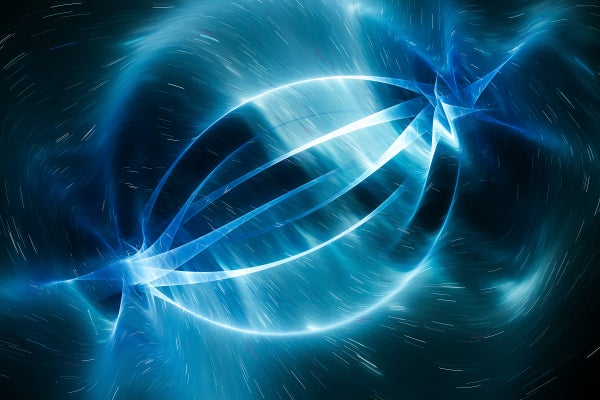量子力學是描述宇宙極小尺度物理學的理論,以其違反常識而聞名。例如,考慮一下該理論的標準解釋如何描述量子領域的變化: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轉變被認為是不可預測且瞬時發生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熟悉的世界中的事件以類似於原子內部事件的方式展開,我們就會期望經常看到麵糊直接變成完全烤好的蛋糕,而無需經歷任何中間步驟。當然,日常經驗告訴我們情況並非如此,但對於不太容易接近的微觀領域來說,這種“量子躍遷”的真正本質一直是物理學中的一個主要未解之謎。
然而,近幾十年來,技術進步使得物理學家能夠在精心安排的實驗室環境中更仔細地探索這個問題。可以說,最根本的突破發生在 1986 年,當時研究人員首次透過實驗驗證了量子躍遷是可以觀察和研究的實際物理事件。從那時起,持續的技術進步為神秘現象打開了更深層次的視野。值得注意的是,一項實驗於 2019 年發表,它顛覆了量子躍遷的傳統觀點,證明量子躍遷一旦開始,就會以可預測且漸進的方式移動,甚至可以在中途停止。
該實驗在耶魯大學進行,使用了一種允許研究人員以最小的干擾監測躍遷的裝置。每次躍遷都發生在超導量子位元(一種旨在模擬原子特性的微小電路)的兩個能量值之間。研究團隊利用對系統處於較低能量時電路中發生的“側向活動”的測量。這有點像透過只聽某些關鍵詞來了解另一個房間的電視上正在播放哪個節目。這種間接探測避開了量子實驗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即如何避免影響正在觀察的系統本身。這些測量被稱為“咔噠聲”(來自舊蓋革計數器檢測放射性時發出的聲音),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特性:躍遷到更高能量總是先於“關鍵詞”的暫停,即側向活動的暫停。這最終使團隊能夠預測躍遷的展開,甚至可以隨意停止它們。
支援科學新聞事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事業 訂閱。 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現在,一項新的理論研究更深入地探討了關於躍遷以及何時發生躍遷的說法。它發現這種看似簡單而基本的現象實際上非常複雜。
抓得到我嗎
新研究發表在《物理評論研究》雜誌上,它模擬了量子躍遷從開始到結束的逐步演化過程——從系統的初始低能量狀態(稱為基態),到第二個能量更高的狀態(稱為激發態),最後再躍遷回基態。該模型表明,可預測的、“可捕捉”的量子躍遷必然存在不可捕捉的對應物,該研究的作者基裡洛·斯尼日科說。斯尼日科是一位博士後研究員,目前在德國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此前曾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工作,這項研究就是在那裡進行的。
具體而言,研究人員所說的“不可捕捉”是指躍遷回基態並非總是平滑且可預測的。相反,該研究的結果表明,此類事件的演化取決於測量裝置與系統的“連線”程度(量子領域的另一個特性,在這種情況下,它與測量的時標與躍遷的時標有關)。連線可能很弱,在這種情況下,量子躍遷也可以透過量子位元側向活動咔噠聲的暫停來預測,就像耶魯大學實驗中使用的方式一樣。
系統透過混合激發態和基態(一種稱為疊加的量子現象)進行躍遷。但是,有時,當連線超過某個閾值時,這種疊加會將自身轉移到混合物的特定值,並傾向於停留在該狀態,直到它在未宣佈的情況下移動到基態。在這種特殊情況下,“這種機率量子躍遷無法預測,也無法在中途逆轉,”魏茨曼研究所的博士後研究員、最新研究的合著者帕爾文·庫馬爾解釋說。換句話說,即使最初計時可預測的躍遷,也會緊隨其後出現本質上不可預測的躍遷。
但是,在檢查最初可捕捉的躍遷時,還有更多的細微差別。斯尼日科說,即使是這些躍遷也具有不可預測的因素。可捕捉的量子躍遷將始終沿著透過激發態和基態疊加的“軌跡”進行,但無法保證躍遷會完成。“在軌跡中的每個點,躍遷都有可能繼續,也有可能被投射回基態,”斯尼日科說。“因此,躍遷可能開始發生,然後突然取消。軌跡是完全確定的——但系統是否會完成軌跡是不可預測的。”
這種行為出現在耶魯大學實驗的結果中。該研究背後的科學家將這種可捕捉的躍遷稱為“不確定性海洋中的可預測性島嶼”。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該研究的作者之一里卡多·古鐵雷斯-豪雷吉指出,“這項工作的亮點在於表明,在沒有咔噠聲的情況下,系統沿著預定的路徑在短暫但非零的時間內到達激發態。然而,當系統透過這條路徑躍遷時,該裝置仍然有機會‘咔噠’一聲,從而中斷其躍遷。”
“量子物理學崩潰了!”
IBM 托馬斯·J·沃森研究中心的 Zlatko Minev 是早期耶魯大學研究的主要作者,他指出,新的理論論文“推匯出了一個非常好的、簡單的模型,並解釋了量子位元背景下量子躍遷現象作為實驗引數的函式。”結合耶魯大學的實驗,這些結果“表明,量子力學中的離散性、隨機性和可預測性遠比通常認為的要多。”具體而言,量子躍遷令人驚訝的細微行為——從基態到激發態的飛躍可以預見的方式——表明量子世界固有的可預測性程度是以前從未觀察到的。如果不是已經被實驗驗證,有些人甚至會認為這是被禁止的。當 Minev 第一次與他的小組中的其他人討論可預測量子躍遷的可能性時,一位同事回應喊道:“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量子物理學就崩潰了!”
“最終,我們的實驗成功了,並且從中可以推斷出量子躍遷是隨機且離散的,”Minev 說。“然而,在更精細的時間尺度上,它們的演化是相干且連續的。這兩種看似對立的觀點共存。”
至於這些過程是否可以應用於更廣泛的物質世界——例如,量子實驗室外的原子——庫馬爾尚未決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研究的條件非常具體。“推廣我們的結果會很有趣,”他說。如果不同測量裝置的結果相似,那麼這種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既是隨機的又是可預測的、既是離散的又是連續的事件——可能反映了量子世界更普遍的屬性。
與此同時,這項研究的預測可能很快得到檢驗。魏茨曼研究所的研究員 Serge Rosenblum 沒有參與這兩項研究,他表示,這些效應可以用當今最先進的超導量子系統觀察到,並且是該研究所新的 量子位元實驗室 的實驗重點。“讓我感到非常驚訝的是,像單個量子位元這樣看似簡單的系統,當我們測量它時,仍然可以隱藏如此多的驚喜,”他補充道。
長期以來,量子躍遷——自然界一切事物最基本的過程——被認為幾乎不可能探測。但技術進步正在改變這一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副教授 Kater Murch 沒有參與這兩項研究,他評論說:“我喜歡耶魯大學的實驗似乎激發了這篇理論論文,該論文揭示了一個研究了幾十年的物理問題的新方面。在我看來,實驗確實有助於推動理論家思考事物的方式,這導致了新的發現。”
然而,這個謎團可能不會消失。正如斯尼日科所說,“我不認為量子躍遷問題會在短期內完全解決;它在量子理論中根深蒂固。但是透過使用不同的測量和躍遷,我們可能會偶然發現一些實際有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