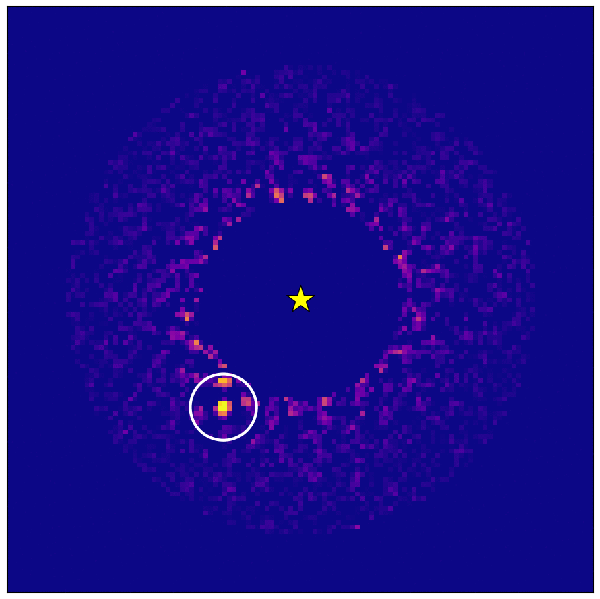三十年前,當天文學家發現首批圍繞其他恆星執行的世界時,他們也開始了所謂的銀河系行星普查,統計銀河系中系外行星的數量和型別。儘管徹底調查我們星系數千億顆恆星是不可行的,但它們的代表性樣本可以提供重要的資訊。透過研究這樣一個樣本的行星數量,研究人員希望瞭解哪些型別的世界最常見或最稀有,以及我們自己的地球和太陽系與它們相比如何。
但是,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可以找到行星,每種方法往往最適合不同型別的世界,這可能導致結果出現偏差。迄今為止,主要的探測技術是透過尋找行星對其恆星的微妙影響來推斷行星的存在,這些技術對非常靠近恆星的巨行星最敏感。這些世界的軌道“年”短至幾天或幾周,而太陽系中不存在這樣的世界。相比之下,直接觀測行星——稱為直接成像——需要將行星與恆星壓倒性的眩光區分開來,這對於位於星系外圍的巨行星來說最容易做到。如果這樣的軌道圍繞我們的太陽,它們會將這些行星中的大多數置於冥王星之外很遠的地方。
幸運的是,新的方法和更廣泛的資料集現在讓科學家們能夠彌合這些極端之間的差距,結合多種行星探測技術的結果,以獲得更好、更清晰的銀河系真實行星數量的檢視。《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項新研究是這種協同方法的首批成功案例之一,不僅獲得了一顆新發現的“中間路線”行星,而且獲得了一種更廣泛的策略,用於尋找和研究更多其他行星。這些待發現行星中最大和最亮的行星也可能是未來直接成像工作的良好候選者,有可能讓天文學家辨別出它們的大氣層和氣候。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美國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的行星獵手、該研究的主要作者泰恩·柯里說:“當我們把[運動和影像]結合在一起時,我們就獲得了行星的所有三個關鍵屬性——它的軌道、質量和大氣層——因此我們學到了更多。”
捕捉一顆恆星
柯里和他的同事們透過比較歐洲航天局蓋亞探測器於 2021 年收集的關於 HIP 99770 b 的恆星運動資料,以及蓋亞的前身、歐空局的依巴谷衛星在 1990 年代早期採集的類似但不太精確的測量資料,發現了他們的新行星,一顆名為 HIP 99770 b 的巨行星。蓋亞和依巴谷都旨在使用一種稱為天體測量的技術精確跟蹤恆星的位置、距離和運動,從而繪製銀河系恆星的地圖(而不是行星)。但是天體測量也可以揭示行星:一顆行星圍繞恆星執行會導致恆星的位置發生週期性的輕微偏移,在天空中來回振盪。透過確定這種偏移的大小和重複性,天文學家可以確定一顆看不見的行星的質量和軌道。
這顆行星的初步發現及其攝影后續觀測之所以成為可能,僅僅是因為跨越數十年的蓋亞-依巴谷資料,這些資料使得探測 HIP 99770 b 的長軌道成為可能。這個組合目錄本身也花費了多年的時間才製作完成。在蓋亞於 2016 年首次釋出資料後,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天文學家、新研究的合著者蒂莫西·勃蘭特釋出了一份包含數萬顆恆星的列表,這些恆星經過了早期依巴谷觀測的交叉檢查和擴充,並在 2021 年蓋亞最新資料釋出後再次更新。結果是,我們獲得了大約 25 年的時間視窗,瞭解這些恆星如何在天空中移動。
一些團隊已經開始挖掘新的資料庫以尋找恆星伴星,“每個團隊都有自己選擇目標的具體資訊,”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研究系外行星大氣層的研究員卡羅琳·莫利說,她沒有參與這項新研究。
就 HIP 99770 b 而言,蓋亞-依巴谷資料顯示,它是一顆氣態巨行星,其軌道距離恆星略遠於天王星距太陽的距離——足夠大、足夠亮且遠離其恆星宿主,因此可以直接成像。在夏威夷莫納克亞山的斯巴魯望遠鏡上使用 SCExAO 直接成像儀進行的後續觀測證實了這些推測,揭示了這顆行星是一個被水蒸氣和一氧化碳分子籠罩的點。氣候模型表明,這顆行星的溫度在 1300 到 1400 開爾文之間(在 1880 到 2060 華氏度之間)。儘管明顯不像地球,但總的來說,HIP 99770 b 的特性使其成為地球相對較近的近親。
“這是[從這個資料庫中獲得的]第一個可以真正聲稱‘這可能是一顆行星質量’的發現,”未參與該研究團隊的貝絲·比勒說。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天文學家比勒接著指出,這個重型天體位於行星和褐矮星之間的灰色地帶,有些人可能會反對將其歸類為行星。無論如何,“這肯定是這種方法探測到的質量最低的天體,”她說。
價值千言萬語
像這樣的結果可以幫助填補銀河系行星普查中長期存在的空白。除了僅限於非常寬軌道上的非常大的行星外,目前直接成像工作最適合非常年輕的世界——年齡在 1000 萬到 1 億年之間——並且仍然因其形成過程中遺留的熱量而發出光芒。比勒說,所有早期調查的累積結果都很重要,但仍然不盡如人意。“我們發現[熱的、年輕的、寬軌道的]巨行星非常罕見,”她說。
雖然預計許多恆星都有某種行星在軌道上執行,但直接成像調查發現,很少有恆星在其邊緣有巨行星。紅外影像揭示了這些世界大氣層的奧秘,模型提供了對其質量的估計。在直接成像捕獲的數十顆系外行星中,天文學家僅設法使用間接行星探測技術的後續測量,更精確地縮小了其中兩顆行星的質量範圍。部分問題在於先前對年輕行星的觀測偏好,這些行星具有相對年輕的宿主恆星,這些恆星比更成熟的恆星活躍得多,因此對基於恆星的伴星質量測量更具破壞性。
勃蘭特說:“一旦你直接成像了一顆行星,在推匯出它的物理特性時,就存在一定程度的猜測。”融合天體測量和直接成像不僅為尋找更多目標打開了大門;它還透過揭示每顆新發現行星的軌道和質量以及其大氣層,消除了其中一些猜測。
儘管蓋亞的目標是 20 億顆恆星,但依巴谷只研究了 10 萬顆,所有這些恆星都相對明亮且靠近地球。柯里估計,在組合目錄中研究的恆星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有伴星,其中大多數是低質量恆星。如果在編目恆星中,每 100 顆有伴星的恆星中只有一顆有可拍照的行星,那麼行星探測新方法的融合應該會顯著增加天文學家很快可以直接觀測到的世界總數。研究人員表示,到其為期十年的調查結束時,蓋亞可能會額外識別出多達 100 顆行星,作為當前儀器直接成像的候選者——比迄今為止識別出的直接成像世界多四倍以上。這將拓寬我們對行星系統的瞭解,使其超越最年輕和最亮的行星,或許會展示更多像我們自己這樣的世界。
柯里說:“新發現的產量高於我們僅僅進行盲搜所能獲得的產量,而且我們獲得的資訊比我們僅僅進行直接成像所能獲得的資訊要豐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