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研究人員像 Suzanne Simard 一樣對流行文化產生如此大的影響。這位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生態學家是理查德·鮑爾斯 2019 年普利策獎獲獎小說《樹木王國》中頗具爭議的樹木科學家帕特里夏·韋斯特福德的原型。Simard 的工作也啟發了詹姆斯·卡梅隆在他 2009 年票房大片《阿凡達》中對神一般的“靈魂之樹”的構想。她的研究還在德國林務員彼得·沃萊本 2016 年的非虛構暢銷書《樹木的隱秘生活》中得到了突出展示。
Simard 的發現俘獲了公眾的想象力,即樹木是社會性生物,它們交換養分、互相幫助,並就蟲害和其他環境威脅進行交流。
之前的生態學家專注於地上發生的事情,但 Simard 使用碳的放射性同位素來追蹤樹木如何透過一個錯綜複雜的 菌根真菌 網路相互分享資源和資訊,這些真菌在樹根上定殖。在最近的工作中,她發現有證據表明,樹木能夠識別自己的親屬,並將它們的大部分 bounty 給予它們,尤其是在樹苗最脆弱的時候。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Simard 的第一本書,《尋找母親樹:發現森林的智慧》本週由克諾夫出版社出版。她在書中論證說,森林不是孤立生物的集合,而是不斷演變的關係網路。她說,多年來,人類透過破壞性做法(如皆伐和滅火)一直在破壞這些網路。現在,它們正在導致氣候變化加速,速度超過了樹木的適應能力,導致物種死亡和害蟲(如小蠹蟲)的侵擾急劇增加,這些害蟲已經摧毀了整個北美西部的森林。
Simard 說,人們可以採取許多行動來幫助森林(世界上最大的陸地碳匯)恢復,並在此過程中減緩全球變暖。在她最非常規的想法中,古老的巨樹(她稱之為“母親樹”)在生態系統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我們需要熱心保護它們。
[以下是訪談的編輯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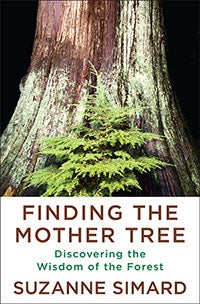
圖片來源:克諾夫出版社
人們可能會驚訝於您在伐木家庭中長大——不完全是一群擁抱樹木的人。您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農村的童年經歷如何為您作為科學家的生活做好準備?
像我小時候那樣在森林裡度過時光,您會知道一切都是交織和重疊的,事物彼此緊挨著生長。對我來說,這始終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聯絡緊密的地方,即使我小時候無法清楚地表達出來。
在今天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伐木工人犧牲了樺樹和闊葉樹,他們認為這些樹木與他們收穫的冷杉爭奪陽光和養分。作為一名年輕的政府樹木科學家,您發現樺樹實際上正在給冷杉幼苗提供養分,使其存活下來。
是的,沒錯。我被派去查明為什麼人工林中的一些冷杉不如天然林中健康的幼年冷杉樹長勢良好。我們發現的一件事是,在天然林中,樺樹對花旗松幼苗的遮蔭越多,樺樹透過地下菌根網路為它們提供的光合糖形式的碳就越多。
樺樹還富含氮,氮反過來支援細菌,這些細菌完成所有養分迴圈的工作,並在土壤中產生抗生素和其他化學物質,以對抗病原體並幫助產生平衡的生態系統。
但是,土壤細菌不是為自己產生抗生素,而不是為樹木產生抗生素嗎?我們怎麼知道它們對樹木有幫助呢?
樺樹向土壤供應碳和氮,這些物質由根和菌根分泌出來,這為土壤中的細菌生長提供能量。在樺樹根的根際生長的一種細菌是熒光假單胞菌。我進行了實驗室研究,表明這種細菌與蜜環菌(一種攻擊冷杉的病原真菌,對樺樹的攻擊程度較輕)一起培養時,會抑制真菌的生長。
您還發現樺樹在夏季透過菌根網路向冷杉樹提供糖分,而冷杉在春季和秋季(樺樹沒有葉子時)透過向樺樹輸送食物來回報。
這不是很酷嗎?一些科學家對此感到困惑:一棵樹為什麼要向另一種物種輸送光合糖?對我來說,這太明顯了。它們都在互相幫助,以建立一個對每個人都有益的健康社群。
您是說森林社群在某些方面比我們自己的社會更平等、更有效率嗎?這裡有什麼教訓嗎?
是的,它們促進多樣性。研究表明,生物多樣性帶來穩定性——它帶來複原力,而且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物種協同合作。這是一個協同系統。一種植物具有很高的光合能力,它可以為所有這些固氮土壤細菌提供燃料。然後還有另一種深根植物,它向下紮根並提取水分,然後與固氮植物分享,因為固氮植物需要大量水分才能開展活動。因此,突然之間,整個生態系統的生產力大幅提高。
因為物種之間互相幫助嗎?
是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我們所有人都需要了解和接受。這是一個我們一直未能理解的概念。
因此,合作與競爭同等重要,甚至比競爭更重要。我們需要修正我們對自然運作方式的看法嗎?
我認為我們需要這樣做。[查爾斯] 達爾文也理解合作的重要性。他知道植物共同生活在群落中,並且對此進行了描述。只是它從未像他基於競爭的自然選擇理論那樣受到關注。
如今,我們審視人類基因組等事物,意識到我們 DNA 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病毒或細菌。我們現在知道,我們自身就是共同進化的物種聯盟。以這種方式思考正變得越來越主流。同樣,森林也是多物種組織。土著文化了解這些聯絡和互動以及它們的複雜程度。人類並非一直持有這種還原論方法。這是西方科學發展的結果,它將我們引向了這一步。
您的意思是西方科學過於關注個體生物,而對更大群落的功能關注不足嗎?
是的,但我也認為科學一直在進步。我們從非常簡單的事情開始:我們觀察單個生物,然後我們觀察單個物種,然後我們開始觀察物種群落,然後是生態系統,然後是更高層次的組織。因此,西方科學已經從簡單走向複雜。隨著我們自身變得更加成熟,它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變化。它變得更加整體化。
您使用“智慧”一詞來描述樹木是有爭議的。但您似乎正在提出一個更激進的論斷——整個生態系統中存在“智慧”。
您使用了“有爭議”這個詞。這源於我使用人類術語來描述一個高度進化的系統,這個系統可以正常工作,並且實際上具有與我們大腦非常相似的結構。它們不是大腦,但它們具有智慧的所有特徵:行為、反應、感知、學習、記憶存檔。並且透過這些網路傳送的是[化學物質],例如穀氨酸,穀氨酸是一種氨基酸,也在我們的大腦中充當神經遞質。我稱該系統為“智慧”,因為這是我在英語中能找到的最能類比我所看到情況的詞語。
有些人質疑您使用“記憶”等詞語。我們有什麼證據表明樹木實際上“記住”了發生在它們身上的事情?
過去事件的記憶儲存在樹木年輪和種子的 DNA 中。樹木年輪的寬度和密度,以及某些同位素的自然丰度,都儲存著往年生長條件的記憶,例如是溼潤年還是乾旱年,或者附近是否有樹木,或者它們是否被吹倒,從而為樹木生長得更快創造了更多空間。在種子中,DNA 透過突變以及表觀遺傳學進化,反映了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條件的遺傳適應。
您在書中寫道:“透過傾聽而不是強加我的意願和索取答案,我學到了更多。” 您能談談這一點嗎?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們受到了非常嚴格的訓練。它可能非常僵化。有非常嚴格的實驗設計。我不能只是去觀察事物——他們不會發表我的作品。我必須使用這些實驗設計——我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我的觀察對我提出的問題總是非常重要。它們始終來自我的成長經歷、我對森林的看法以及我的觀察。
您最新的研究專案被稱為母親樹專案。什麼是“母親樹”?
母親樹是森林中最大、最古老的樹木。它們是將森林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劑。它們擁有來自先前氣候的基因;它們是許多生物、許多生物多樣性的家園。透過其巨大的光合能力,它們為整個土壤生命網路提供食物。它們將碳保留在土壤和地上,並保持水分流動。這些古老的樹木有助於森林從擾動中恢復。我們不能失去它們。
母親樹專案試圖在真實的森林中應用這些概念,以便我們可以開始管理森林以實現復原力、生物多樣性和健康,認識到我們實際上已透過氣候變化和過度採伐將它們推向崩潰的邊緣。我們目前正在 9 個森林中工作,這些森林的範圍從美國-加拿大邊境延伸到聖詹姆斯堡,大約位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中途。
《樹木王國》中受您啟發的人物帕特里夏·韋斯特福德有時會感到絕望。您有時也會感到沮喪嗎?
當然我會。但我沒有時間感到沮喪。當我開始研究這些森林系統時,我意識到它們的組織方式使它們能夠非常迅速地恢復。您可以將它們推到崩潰的邊緣,但它們具有巨大的緩衝能力。我的意思是,大自然是輝煌的,對吧?
但現在的不同之處在於,由於氣候變化,我們將需要稍微幫助大自然。我們將不得不確保母親樹在那裡幫助下一代向前發展。我們將不得不將一些預先適應溫暖氣候的基因型移入更北部或更高海拔的森林,這些森林正在迅速變暖。氣候變化的velocity遠快於樹木自身遷移或適應的velocity。
將種子從一個綜合生態系統轉移到另一個生態系統是否存在風險?
儘管再生本地適應的種子是最好的,但我們改變氣候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森林將需要幫助才能生存和繁殖。我們必須協助已經預先適應溫暖氣候的種子的遷移。我們需要成為積極的變革推動者——生產性推動者而不是剝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