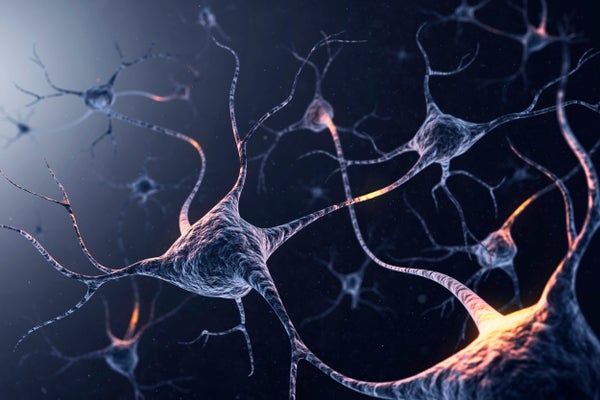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神經科學家週一報告稱,他們透過注射RNA將記憶從一隻動物轉移到另一隻動物身上,這一驚人的結果挑戰了關於記憶在大腦中儲存位置和方式的普遍觀點。
大衛·格蘭茲曼實驗室的這一發現暗示了未來可能出現基於RNA的新療法,以恢復失憶症,如果正確的話,可能會撼動記憶和學習領域。
“這非常令人震驚,”紐約州布魯克林區紐約州立大學下城醫療中心的神經學家和記憶研究員託德·薩克託博士說。“重要的是,我們首次研究出記憶儲存的基本字母表。” 他沒有參與這項研究,該研究發表在eNeuro上,這是神經科學學會的線上期刊。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 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許多科學家預計會更加謹慎地看待這項研究。這項工作是在蝸牛身上進行的,蝸牛已被證明是神經科學的強大模型生物,但其簡單的大腦與人類的大腦運作方式截然不同。這些實驗需要重複,包括在具有更復雜大腦的動物身上進行。而且,這些結果與大量證據相悖,這些證據支援根深蒂固的觀點,即記憶是透過神經元之間連線或突觸強度的變化來儲存的。
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的助理教授托馬斯·瑞安說:“如果他是對的,這將是絕對驚天動地的。”他的實驗室正在尋找記憶的物理痕跡,即印跡。“但我不認為他是對的。”
格蘭茲曼知道他對突觸的非正式降級不會在該領域引起共鳴。“我預計會感到震驚和懷疑,”他說。“我不期望人們會在下一次神經科學學會會議上為我舉行遊行。”
甚至他自己的同事也表示懷疑。“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說服我實驗室的人做這個實驗,”他說。“他們認為這太瘋狂了。”
格蘭茲曼的實驗——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包括對海蝸牛加州海兔進行輕微的電擊。受到電擊的蝸牛學會收回其脆弱的虹吸管和鰓近一分鐘,作為隨後受到輕微觸控時的防禦;未受到電擊的蝸牛隻會短暫收回。
研究人員從受到電擊的蝸牛的神經系統中提取了RNA,並將該物質注射到未受到電擊的蝸牛中。RNA的主要作用是在細胞內充當信使,攜帶來自其近親DNA的蛋白質製造指令。但是,當注射這種RNA時,這些未受刺激的蝸牛在受到輕柔觸控後,將其虹吸管收回了很長時間。接受了未受到電擊的蝸牛的RNA注射的對照蝸牛,其虹吸管收回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格蘭茲曼說:“就好像我們轉移了記憶一樣。”
格蘭茲曼的研究小組更進一步,表明如果將培養皿中的海兔感覺神經元暴露於來自受到電擊的蝸牛的RNA,它們會變得更興奮,就像受到電擊後一樣。暴露於來自從未受到電擊的蝸牛的RNA不會導致細胞變得更興奮。
格蘭茲曼說,結果表明記憶可能儲存在神經元的細胞核內,RNA在那裡合成,並且可以作用於DNA以開啟和關閉基因。他說,他認為記憶儲存涉及這些表觀遺傳變化——基因活動的改變,而不是構成這些基因的DNA序列的變化——這些變化是由RNA介導的。
這種觀點挑戰了廣泛持有的觀點,即記憶是透過增強神經元之間的突觸連線來儲存的。相反,格蘭茲曼認為,記憶形成過程中發生的突觸變化源於RNA攜帶的資訊。
麻省理工學院皮考爾學習與記憶研究所所長、神經科學家李慧表示:“這個想法很激進,絕對挑戰了這個領域。” 蔡最近與人合著了一篇關於記憶形成的主要綜述,她稱格蘭茲曼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且有趣”,並表示許多研究支援表觀遺傳機制在記憶形成中發揮一定作用的觀點,這可能是一個複雜且多方面的過程。但她說,她強烈反對格蘭茲曼的觀點,即突觸連線在記憶儲存中不起關鍵作用。
與格蘭茲曼一樣,聖三一學院的瑞安也與少數神經科學家(有些人稱他們為叛逆者)站在一起,他們質疑記憶是透過突觸強度儲存的想法。2015年,瑞安是《科學》雜誌一篇論文的第一作者,該論文與麻省理工學院諾貝爾獎獲得者利根川進合作,表明即使在突觸加強被阻止後,記憶也可以被檢索。瑞安說,他正在研究這樣一種觀點,即記憶是透過由新的突觸連線結合在一起的神經元集合來儲存的,而不是透過加強現有連線。
瑞安認識格蘭茲曼並信任他的工作。他說他相信新論文中的資料。但他不認為蝸牛或細胞的行為證明RNA正在轉移記憶。他說,他不明白RNA如何在幾分鐘到幾小時的時間尺度內工作,如何引起幾乎瞬間的記憶回憶,或者RNA如何連線大腦的許多部分,例如聽覺和視覺系統,這些部分參與更復雜的記憶。
但格蘭茲曼說,他確信RNA正在發揮超越突觸的作用。2014年,他的實驗室表明,由於一系列實驗程式而在蝸牛中丟失的電擊記憶可以被恢復——但是當記憶恢復時,與記憶一起丟失的突觸模式以隨機方式重新形成,這表明記憶並非儲存在那裡。格蘭茲曼的實驗室和其他實驗室也表明,即使突觸形成或加強沒有改變,阻止表觀遺傳變化也會阻止長期記憶的形成。
他說:“突觸可以來來去去,但記憶仍然可以在那裡,”他說,他認為突觸僅僅是“細胞核中持有的知識的反映”。
格蘭茲曼研究記憶已有三十多年。他與埃裡克·坎德爾(Eric Kandel)一起做了博士後工作——這位神經科學家因對海兔的研究而分享了2000年諾貝爾獎,探索了突觸在記憶中的作用——他說,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相信突觸變化是記憶儲存的關鍵。
但他說,近年來來自其他實驗室和他自己實驗室的一系列發現使他開始質疑突觸教條。他稱自己為“康復中的突觸學家”。
對格蘭茲曼研究的懷疑可能部分是由於這項工作讓人回想起科學界令人不安的一幕,涉及一位非常規心理學家詹姆斯·V·麥康奈爾,他曾在密歇根大學花費多年時間試圖證明大腦外部的某種東西——他稱之為“記憶RNA”的因素——可以轉移記憶。在50年代和60年代,麥康奈爾訓練了扁蟲,然後將訓練過的蠕蟲的身體餵給未經訓練的蠕蟲。未經訓練的蠕蟲隨後似乎表現出它們吞噬的訓練有素的蠕蟲的行為,這表明記憶以某種方式轉移了。他還表明,訓練過的蠕蟲在被斬首後可以記住它們的訓練,即使它們長出了新的頭。
儘管這項工作被其他一些實驗室複製,但麥康奈爾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嘲笑,並且經常被描述為一個警示故事,因為其他實驗室花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試圖(通常是不成功地)複製這項工作。(麥康奈爾於1990年去世,五年前他曾是炸彈客西奧多·卡辛斯基的目標。)
最近,塔夫茨大學的發育生物學家邁克爾·萊文在更受控制的環境下複製了麥康奈爾的無頭蠕蟲實驗,並認為麥康奈爾可能確實是正確的。
格蘭茲曼說,麥康奈爾的一位學生艾爾·雅各布森在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助理教授期間,巧合地證明了透過RNA注射在扁蟲之間轉移記憶。這項工作發表在1966年的《自然》雜誌上,但雅各布森從未獲得終身教職,可能是因為人們對他的發現表示懷疑。然而,該實驗不久後在老鼠身上得到了重複。
格蘭茲曼在印第安納大學攻讀心理學本科時瞭解了麥康奈爾的工作——以及他的諷刺期刊《蠕蟲賽跑者文摘》——但從未認真對待這些結果。現在,雖然他仍然不相信麥康奈爾完全正確地認為能夠轉移記憶,但他確實認為麥康奈爾和雅各布森都發現了一些東西。
對於那些挑戰現狀的人來說,在記憶領域工作可能很艱難。例如,紐約州立大學的薩克託花了超過25年的時間——儘管受到同行科學家的懷疑、拒絕和徹底嘲笑——追逐一個單一分子PKMzeta,他認為該分子對於長期記憶的形成至關重要,並且可能與格蘭茲曼發現的RNA機制有關。
該領域的風險很高,因為記憶對我們的自我意識至關重要,許多科學家認為,理解記憶的運作方式是現在應該弄清楚的事情。“這是20世紀生物學中最後一個偉大的問題,”薩克託說。“某些方面使得神經科學家難以弄清楚。”
部分原因可能是過度關注突觸強度。瑞安指出,大約有12,000篇關於突觸強度的論文發表,但沒有對記憶如何儲存提供充分的解釋,他補充說,他讚賞格蘭茲曼開闢了一條探索的新途徑,儘管它很激進。
瑞安說:“現實情況是,我們對記憶知之甚少。“我對任何新的視野和途徑都感到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