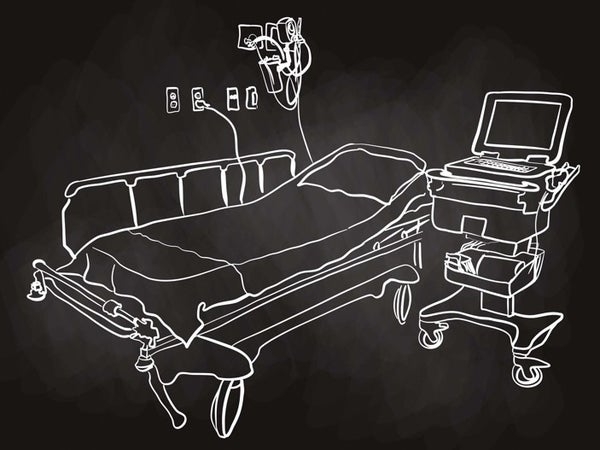2016年,加拿大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將自願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之一。自從新規透過以來,居住在那裡的患有“嚴重且不可補救的醫療狀況”的人可以選擇透過施用致命的藥物混合物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許多醫療組織,包括世界醫學協會,強烈反對這種做法。但是,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更深層的倫理困境:一些尋求醫生協助死亡的患者也表達了他們希望將自己的組織捐贈給科學研究,以幫助研究人員在未來幾代人中治療和治癒他們的疾病。
已經有幾位患有晚期多發性硬化症 (MS) 的人自願在接受自願安樂死(在加拿大正式稱為醫療輔助死亡)後捐贈腦組織樣本用於醫學研究。他們的組織在他們去世後一小時內被收集,對於收集腦組織樣本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短暫時間視窗,研究人員表示:“死亡和屍檢之間的時間間隔過長,組織就會降解,”蒙特利爾大學的神經科學家亞歷山大·普拉特說。這使得幾乎不可能確定與 MS 相關的腦損傷內部基因和蛋白質的活動。普拉特稱之為“超新鮮”的腦組織樣本在死亡後不久收集,研究人員可以訪問這些資訊。他說,這樣做可能會揭示疾病的根本原因,並最終帶來改進的治療方法。
儘管潛在的科學益處是顯而易見的,但該實踐的倫理道德卻比較模糊,並且它們對患者、他們的親人以及全球醫學界都具有影響。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對 MS 等疾病的研究傳統上因疾病動物模型的使用而變得更容易。最近,三維腦“類器官”已成為研究 MS 的一種很有前景的新工具。但是,沒有什麼可以替代透過研究從患有這種疾病的人身上採集的組織樣本而獲得的見解。
“說‘我們在大鼠模型中看到了這種生物學反應或作用機制,我們認為這些可能與人類相關’,這當然很好,”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和脊柱外科醫生布 Brian Kwon 說。“但有機會在人類患者身上測試這些假設則是另一回事。”
但普拉特說,從患有 MS 等疾病的人身上收集腦組織樣本具有挑戰性。他說,大腦癒合不良,這使得研究人員無法從患有這種疾病的活人身上獲取活組織檢查樣本。這意味著腦組織樣本必須在死後採集。有傳聞證據表明,一些 MS 患者渴望捐獻他們的大腦用於研究。例如,當在2017 年為數字出版物《今日多發性硬化症新聞》撰寫的文章中提出這個主題時,幾位 MS 患者在該文章下方留言,表達了捐獻自己大腦的意願。“我沒想到 MS 患者被允許捐獻器官,”一位評論員寫道。“我想捐獻我的 MS 大腦來幫助 MS 研究。”
但普拉特說,如果在宣佈死亡和樣本採集之間存在 significant 延遲,組織就會失去其醫療價值。他說,死亡和屍檢之間僅等待五到六個小時,只有穩定的蛋白質才能在樣本中檢測到。“不穩定的蛋白質會被降解,RNA 將毫無用處。就我們可以在病理學層面研究的內容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限制。”
在加拿大允許輔助死亡的新法律生效後,普拉特和他的同事聯絡了一些選擇接受醫學安樂死的 MS 患者,詢問他們是否也會考慮捐贈腦組織樣本用於研究。加拿大法律的撰寫方式意味著,如果患有嚴重但非絕症(如 MS)的人的健康狀況非常差,以至於死亡被認為是“合理可預見的”,他們可能有資格接受醫學安樂死。此外,在加拿大接受輔助死亡的人中,略低於一半的人在醫院環境中這樣做,這意味著屍檢小組可以待命在附近的屍檢室中,以便在宣佈死亡後不久收集組織。
普拉特說,到目前為止,大約有六個人接受了輔助死亡,並同意捐贈他們的組織用於普拉特領導的研究。親人可以在宣佈死亡後與患者待在一起長達一個小時,進行最後的告別,然後將遺體轉移到屍檢室。取出此人的大腦並對與 MS 相關的病變進行取樣。其中一些樣本留在普拉特的機構;另一些樣本立即運往遠在美國和法國的合作者。普拉特說,研究小組正在使用一種稱為單細胞 RNA 測序的技術來計算樣本中不同形式 RNA 的數量。他們還使用免疫組織化學來表徵不同腦損傷內的組織,並使用流式細胞術來識別特定的細胞型別。
普拉特表示,MS 是一種異質性疾病,因此確定個體腦損傷的確切細胞和分子特徵具有真正的價值。“在 MS 中,大腦有數百或數千個損傷,每個損傷都不同,”他說。他和他的同事正在收集的資料將用於構建一個數據庫,以探索這種變異的極限。它最終可能會為針對個體患者量身定製的 MS 帶來更好的治療選擇。
阿姆斯特丹荷蘭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神經科學家 Inge Huitinga 說:“屍檢延遲越短,腦組織質量越好。” “短暫的屍檢延遲允許對組織進行最先進的分析。”
Huitinga 是荷蘭腦庫的主任,自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來,該腦庫接受了來自患有各種神經和精神疾病的捐贈者以及死時大腦健康的人的屍檢樣本。
荷蘭腦庫中少量大腦來自接受安樂死的捐贈者,安樂死自 2002 年以來在荷蘭是合法的。然而,Huitinga 說,根據她的經驗,這些大腦與以其他方式死亡的人捐贈的大腦在質量上幾乎沒有差異。原因之一是,在荷蘭,超過 80% 符合安樂死條件的人選擇在家中接受該手術。這意味著,即使可以提前確定死亡時間和日期,但在將遺體運送到醫院期間以及屍檢開始之前,仍然存在延遲。她說:“最終,由於荷蘭的醫療輔助死亡,平均屍檢延遲時間並沒有縮短。”
倫理考量
因此,普拉特的研究似乎是獨一無二的。由於加拿大有一半接受自願安樂死的人在醫院進行安樂死,因此該國可能是唯一一個通常可以在宣佈死亡後一小時內收集腦組織樣本的地方。特雷弗·斯塔默斯是英國倫敦聖瑪麗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他研究安樂死和輔助自殺的倫理道德,他不知道有人以普拉特及其同事的方式收集樣本進行研究。但斯塔默斯說,普拉特的工作提出了一些熟悉的倫理問題,因為在少數幾個國家,已經可以捐贈器官(主要是肝臟和腎臟)用於自願安樂死後的移植。
比利時和荷蘭大約十年前就開始進行此類手術,現在加拿大也在進行此類手術。比利時魯汶大學醫院的胸外科醫生 Dirk van Raemdonck 表示,器官捐贈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用於誘導死亡的巴比妥類藥物、嗎啡和麻痺劑的混合物似乎對為捐贈而收穫的器官沒有毒性作用。
同樣,需要在死後儘快開始屍檢,以便可以在器官退化之前收集器官——儘管在這種情況下,與腦組織收集相關的緊迫性沒有那麼高,並且通常認為延遲幾個小時是可以接受的,van Raemdonck 說。但斯塔默斯說,即使這種在安樂死後略微降低的醫療緊迫感也可能會擾亂親屬的哀悼過程。他認為,如果遺體在他們有時間自己確認之前就被移走,甚至可能導致他們後來不確定他們的親人是否真的死了。
普拉特從 MS 患者身上收集腦組織樣本的經驗表明情況並非如此。家屬被告知,他們可以在宣佈死亡後與親人單獨相處約 60 分鐘,以便他們實現情感上的解脫,但他表示,許多人選擇放棄這項權利,以便屍檢可以更快地開始。
然而,斯塔默斯想知道家屬是否真的對這個過程感到安心。他懷疑有些人可能會擔心,如果他們花太多時間與遺體在一起,並危及組織或器官的醫療價值,他們會辜負醫生。
世界醫學協會醫學倫理委員會主席兼丹麥醫學協會主席 Andreas Rudkjøbing 提出了另一個擔憂。始終向那些申請安樂死的人強調,他們可以隨時撤回他們的請求。但是,如果安樂死候選人隨後也同意在他們死後捐贈組織用於醫學研究,他們可能會覺得他們已經失去了拒絕進行安樂死的選擇,同樣是因為他們擔心讓醫生失望。“如果患者承諾參與研究,他或她將更難改變主意,”他說。
現在說這些擔憂是否會在現實世界中發生可能還為時過早。
但是,對從接受輔助死亡的人那裡獲得的樣本進行 MS 研究會引發其他倫理複雜性。原則上,普拉特及其合作者進行的研究可能會為 MS 帶來新的療法,使全世界的人們受益,包括那些自願安樂死仍然是非法的甚至可能被認為是不道德的國家的患者。
“我認為這令人擔憂,”Rudkjøbing 說。“世界醫學協會堅決反對安樂死,我們同樣反對利用安樂死的做法來促進臨床研究。”
牛津大學醫學倫理學家多米尼克·威爾金森持不同觀點。他認為,知識本身不具有倫理價值。一些研究人員可能會對利用從選擇自願安樂死的人那裡獲得的細胞系進行研究感到不舒服。但威爾金森說,研究人員忽視其他人透過研究此類組織獲得的知識,在倫理上更沒有意義。
也許需要牢記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公眾如何看待普拉特等人的研究。如果人們願意在死後捐獻他們的組織和器官(無論是自然死亡、意外死亡還是醫療輔助死亡),將會帶來巨大的好處。但是,只有當人們感到他們可以信任捐贈過程時,他們才可能準備好成為捐贈者。斯塔默斯擔心,如果圍繞捐贈的討論與圍繞有爭議的自願安樂死問題的討論混淆,一些原本會考慮捐贈組織用於研究的人可能會決定不捐贈。
“我非常支援器官和組織捐贈,”斯塔默斯說。“因此,我擔心任何可能危及它並損害對其有效運作至關重要的信任的事情。”
本文經許可轉載,並於 2020 年 1 月 24 日首次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