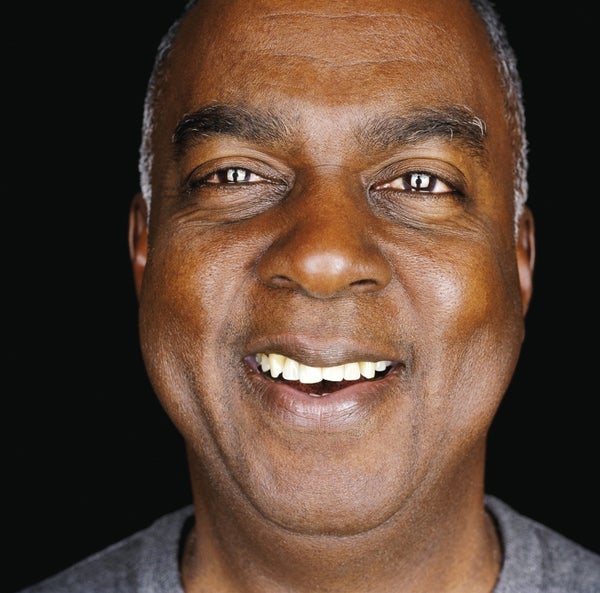一次好的對話中有什麼? 當然可以說出文字——措辭越引人入勝越好。 但對話也包括“眼神、微笑、文字之間的沉默”,正如瑞典作家安妮卡·托爾所寫的那樣。 當這些元素一起嗡嗡作響時,我們會感到與對話夥伴最深入地互動和最緊密地聯絡,彷彿我們與他們同步。
就像優秀的對話者一樣,達特茅斯學院的神經科學家們也採納了這個想法,並將其帶到了新的領域。 作為一系列關於兩個頭腦如何在現實生活中相遇的研究的一部分,他們報告了關於眼神交流和對話期間兩人之間神經活動同步的相互作用的驚人發現。 在 9 月 14 日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一篇論文中,研究人員表明,與對話夥伴保持同步是好的,但是與他們進出同步可能更好。
長期以來,眼神交流一直被認為是像粘合劑一樣,將個體與他們正在交談的人聯絡起來。 它的缺失可能預示著社交功能障礙。 同樣,對神經同步性日益增長的研究也集中在個體之間大腦活動對齊的積極方面。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方式是 訂閱。 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在這項新研究中,心理學家塔利亞·惠特利和研究生索菲·沃爾特延使用瞳孔擴張作為非結構化對話期間同步性的衡量標準,發現眼神交流的時刻標誌著共同關注的峰值——而不是持續凝視的開始。 事實上,同步性在注視對話者的眼睛後急劇下降,並且只有當您和對方移開目光時才開始恢復。 “眼神交流不是引發同步性;它正在破壞同步性,”論文的資深作者惠特利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話需要一定程度的同步性,但惠特利和主要研究作者沃爾特延推測,打破眼神交流最終會推動對話向前發展。 “也許這樣做是為了讓我們打破同步性,回到我們自己的頭腦中,以便我們可以提出新的和個人的貢獻,以保持對話繼續進行,”沃爾特延說。
“這是一項出色的研究,”慕尼黑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學研究所的精神病學家和社會神經科學家萊昂哈德·席爾巴赫說,他研究社互動動,但沒有參與這項研究。 他讚揚了該實驗的設計,以複製自然相遇和關注自由形式的對話。 他說,結果表明,“人際同步性是社互動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可能並非總是合乎需要的。”
該領域的其他人被研究人員對對話的創造性思維方式所吸引,這在論文中被描述為“思想相遇的平臺”。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的社會心理學家朱莉安娜·施羅德說:“這種概念化可能會啟發其他研究人員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對話並更深入地研究它,她也沒有參與這項研究。
這項新工作建立在惠特利和心理學家奧利維亞·康(現任職於哈佛大學)的早期研究基礎上,他們表明瞳孔同步性可以作為共同關注的衡量標準。 我們的瞳孔會隨著光線變化而發生反射性反應而放大和縮小,但也在較小程度上,當我們生理上受到刺激時也會如此。 康和惠特利追蹤了演講者在講述關於他們生活的積極或消極記憶時的眼球運動。 然後,研究人員追蹤了後來在同一時間聽取相同故事的人的眼球運動。 他們發現,當故事中出現情感高峰時,聽眾的瞳孔擴張與演講者的瞳孔擴張同步。 “我們知道這是人們彼此達成共識的標誌,”惠特利說。
對於當前的論文,沃爾特延希望透過研究面對面的對話來擴充套件早期的發現,以便了解眼神交流如何在即時中影響共同關注。 她將達特茅斯的 186 名心理學學生(都是相對陌生人)分成對話對,並要求他們就他們想要的任何事情談論 10 分鐘,同時她追蹤他們的眼球運動。 參與者還觀看了他們對話的影片,並逐分鐘評價了他們記憶中的參與度水平。
“我們預計眼神交流就像趕牛棒一樣,讓兩個人回到同一個波長,”沃爾特延說。 如果是這樣,眼神交流的開始應該導致隨後的瞳孔同步性增加。 相反,研究人員發現結果相反:同步性在開始時達到峰值,然後下降。 但他們也發現,參與者報告說,當他們進行眼神交流時,他們更投入。 “我們想,‘也許這種眼神交流的產生和中斷一定對對話有所幫助,’”沃爾特延說。
先前關於眼神交流的研究通常是被動的,就像惠特利和康早期的工作一樣。 沃爾特延的實驗的現實世界設計提醒人們,大多數人在對話過程中自然會多次看著對方和移開目光。 長時間盯著某人看——或根本不看——可能會顯得尷尬。 當研究人員進一步思考眼神交流可能對我們有什麼作用時,他們轉向了關於創造力的文獻。 在那裡,他們認識到同步性過多的限制。 “如果人們試圖以某種方式創新,你就不希望人們步調一致,”惠特利說。 “你希望人們[說],‘如果我們這樣做會怎麼樣? 如果我們那樣做會怎麼樣?’ 你需要人們提供他們獨立的見解,並以這種方式進行構建。”
眼神凝視可以用來調節同步性的想法引起了其他研究人員的興趣。 席爾巴赫說:“這篇論文中優雅的實驗方法可能有助於定量研究精神疾病,這些疾病可以被描述為‘社互動動障礙’,”他研究了自閉症患者的凝視和其他社互動動要素。
這些發現還有助於解釋 Zoom 和其他視訊會議平臺的挫敗感,在這些平臺上,由於攝像頭和視窗在螢幕上的位置,幾乎不可能進行或打破真正的眼神交流。 (該論文的發表在 Twitter 上引發了關於這一現象的熱烈討論。)
惠特利可以想象後續研究會檢查各種對話情境。 例如,當父母指導孩子時,產生和打破同步性之間的動態舞蹈會如何發揮作用? 據推測,在那種情況下,父母會希望孩子全神貫注,因此完全同步。 另一方面,也許這項研究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在不一直看著對方的長途汽車旅行中,通常更容易進行深入的對話。
“在這種耦合、解耦的事情中,可能存在一個最佳的甜蜜點——人們真正傾聽彼此,但他們也用新的想法來推動對話,”惠特利說。 “這些對話可能是最有趣的。”
這篇文章的一個版本,標題為“失去聯絡”,已改編收錄在 2021 年 12 月號的大眾科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