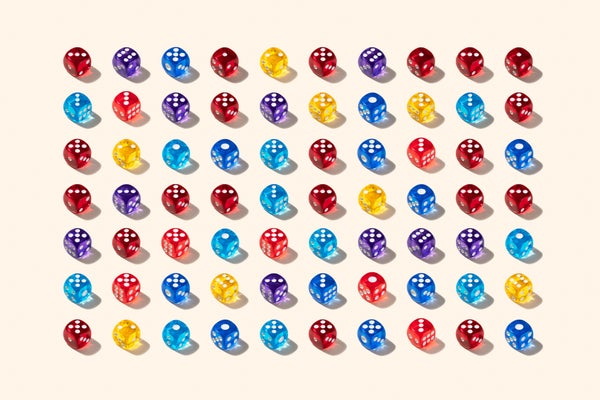COVID-19 的衝擊力很大程度上源於不確定性。如果病毒對我們肉眼可見,我們本可以避開它,並像往常一樣進行其他活動。不僅我們看不到病毒本身,我們也看不到某些可能感染我們的人身上的症狀。因此,我們採取了嚴格的預防措施,遠遠超出了我們顯著暴露的特定地點和時間的比例。我們避免與對我們沒有風險的未感染者互動,我們也不參加本可以使我們的經濟保持運轉甚至繼續繁榮的活動。當有毒昆蟲在附近時,我們會待在原地,僅僅因為我們看不到它。
在阿爾貝·加繆的書《鼠疫》中,一種危及生命的疾病生動地闡釋了我們存在的現實。我們知道我們終有一天會死去,但我們無法為此做好準備,因為我們無法預測它何時會發生。存在的不確定性不僅延伸到我們的私人生活,也延伸到社會領域。 越南戰爭是由對北部灣事件的模糊解釋引發的,並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
人們可能會天真地認為,我們生活中的基本不確定性僅僅反映了資訊的缺乏;透過追蹤缺失的資訊,我們就能夠清除未知的迷霧。然而,量子力學,它是我們物質現實的基礎,暗示著我們能夠期望達到的清晰度是有限的。 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指出,對於某些可觀測物件,總是存在殘留的不確定性。如果我們試圖完善我們對電子位置的瞭解,我們的測量過程將增加其動量的不確定性。位置和動量不確定性的乘積有一個由普朗克常數設定的基本最小值。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訂閱以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工作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這意味著即使我們透過一個完美的實驗檢索到所有可用資訊,我們仍然無法確定地預測電子的未來。傳統上,我們的生活是由大型物體塑造的,例如我們駕駛的汽車,對於這些物體來說,海森堡的不確定性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但是,隨著資訊科技、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的出現,量子世界最終可能會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影響醫療決策。現實的基石是機率性的。我們只能為不同的結果分配可能性。
與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1926年寫給馬克斯·玻恩的信相反,我們現在知道大自然確實擲骰子。我們感染 COVID-19 後總是存在一定的死亡機率。那些在沒有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參加泳池派對的人是在玩俄羅斯輪盤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活下來,但有些人會死去。
當然,醫療方面的既往病史可能會強烈影響 COVID-19 死亡等罕見結果。現實生活中的事件通常源於多種原因的匯合,因此很難解讀。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有可能明確地識別出某種現象的主要原因。這就是受控科學實驗背後的原因,它提供了在尋求更好理解的過程中一次隔離一種影響的機會。
當資料稀缺時,科學界的看法可能會發生很大變化。最近對病毒突變的RNA測序顯示,COVID-19在美國的感染路徑與之前認為的非常不同。
但是,即使收集了大量資料,我們理解其真正含義的能力也會限制我們預測的可靠性。瑪雅文化在許多世紀中收集了大量的天文資料,並將他們的天空影像與人類歷史相關聯,以達到預測戰爭結果的政治目的。我們現在知道,人類行為中隱含的不確定性,就像在越南戰爭中一樣,無法透過監測月球、水星、金星、火星、木星或土星的天空位置來消除。相反,當前科學的目的是以可重複的方式將原因與結果聯絡起來,而沒有一廂情願或偏見。天文學教育我們,行星和恆星的運動與人類的行為無關,而遺傳學則啟發我們,人類的能力與膚色無關。
儘管如此,我們的科學理解中仍然存在巨大的空白。因此,許多人在面對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決定(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是否參加泳池派對)的不確定性時,依賴於一廂情願的想法。如果這是基於過去的經驗,那似乎很自然,但當類似的疫情在1918年肆虐時,年輕的派對參與者還不存在。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我們應該如何應對貫穿我們生活的基本不確定性?負責任的建議很簡單:我們應該考慮所有科學證據,並對未知事物採取有分寸的風險。每次過馬路時,我們都會進行這樣的計算。只有傻瓜才會因為存在的風險而永遠不過馬路。回報通常以風險為前提。如果你想學會游泳,你必須跳入水中;但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你冒著溺水的風險。目前,在科學家為 COVID-19 研製出可靠的疫苗之前,你最好避開任何公共遊泳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