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什麼? 像大多數偉大的問題一樣,這個問題很容易提出,但很難回答。 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嘗試,哲學家們則進行了數千年。 今天,我們的知識如此先進,以至於我們可以精確地操縱生命的基石——DNA、RNA 和蛋白質——來構建生物機器和設計新的基因組。 然而,儘管我們知道這麼多,但目前對於生命的基本定義仍未達成普遍共識。
生命的定義仍然難以捉摸的原因很簡單:我們只知道一種型別的生命——地球上存在的生命——並且用一個樣本量來做科學研究是具有挑戰性的。 這就是所謂的 N = 1 問題(其中“N”表示科學家可以研究的合格候選者的數量)。 無論研究人員多麼聰明地從他們確定的唯一例項中推斷出生命的一般原則,他們都無法確認他們是否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除非 N 增加。 尋找生命的另一個例項——無論它是在地球上、太陽系的其他地方還是更遠的地方被發現——是擴大 N 的一種方法。 對外星生命(以我們未知的方式存在)的尋找才剛剛開始,但它已經耗費了數十億美元和無數小時的勞動,即使不能保證最終會有所發現。
然而,還有另一種解決 N = 1 問題的潛在方法:一些科學家沒有去尋找生命的第二次起源,而是試圖創造一個。 人造生命領域——簡稱 ALife——是有系統地闡明生命基本原則的嘗試,透過研究表現出類似生命行為的無生命自然系統,或透過構建人造系統來與自然界的創造物進行比較。 許多實踐者,即所謂的 ALifers,認為從頭開始創造生命是真正理解生命是什麼的最可靠方法——這種方法也許最好概括為“先構建,後解釋”。
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 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劇透警告:到目前為止,在這個新興領域中,還沒有人令人信服地創造出人造生命——但這並不是因為缺乏嘗試。 這種明顯糟糕的記錄使 ALife 成為各種批評的眾矢之的,從“扮演上帝”的指責到該領域可疑的科學價值的宣告。
東京大學的複雜性科學家池上高志 (Takashi Ikegami) 厭倦了這些抱怨。 他說,他的領域就像任何其他追求知識本身的基礎科學一樣,所以詢問 ALife 的“意義”可能完全沒有抓住重點。
“生命系統的存在與任何事物的功用無關,” 池上說。 “有些人問我,‘人造生命的優點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你祖母的優點是什麼? 你狗的優點是什麼?’”
無盡的進化
儘管許多 ALifers 不願強調他們研究的應用,但創造人造生命的探索也可能帶來實際的回報。 人工智慧可以被認為是 ALife 更迷人的表親,因為這兩個領域的研究人員都沉迷於一個名為開放式進化的概念。 這是一種系統創造本質上無限複雜性的能力,成為一種“新穎性生成器”。 已知唯一表現出這種特性的系統是地球生物圈——一個持續不斷、數十億年的生物多樣性進化爆發,最終可以追溯到簡單的單細胞祖先生物。 如果——或者當——ALife 領域設法在某些虛擬模型中複製生命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造力”時,那麼相同的原理可能會產生真正具有創造力的機器。
目前,在人工智慧領域,“你可以構建這些龐大的深度學習系統,但在某些時候,這些系統無法再學習,” 南丹麥大學的 ALife 研究員兼物理學家斯蒂恩·拉斯穆森 (Steen Rasmussen) 說。 “一個系統要繼續學習需要什麼? 沒人知道。”
與人工智慧的發展相比,ALife 的進展更難被認可。 造成這種差異的一個原因是,ALife 是一個核心概念——生命本身——令人煩惱地未定義的領域。 ALifers 之間缺乏共識也無濟於事——沒有一套共同的原則來指導他們的集體工作,更不用說評估它的標準了。 結果是各種各樣但漫無目的的專案,每個專案都沿著自己獨特的道路隨意前進。 無論好壞,ALife 都反映了它所研究的主題。 它混亂的進展與塑造地球生物圈的漫長進化鬥爭驚人地相似。
組裝 ALife
ALife 的非官方啟動始於 1987 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舉行的首屆生命系統合成與模擬跨學科研討會,該領域在那裡獲得了名稱的合法性。 計算機科學家克里斯托弗·蘭頓 (Christopher Langton) 創造的“人造生命”一詞為科學怪才和流浪者對類生命行為的零散跨學科研究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標籤。 拉斯穆森是 36 年前參加研討會的與會者之一。 他回憶起感覺自己“回到了家”。
一些 ALife 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 1948 年,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 (John von Neumann) 和斯坦尼斯瓦夫·烏拉姆 (Stanislaw Ulam) 著手闡述機器在理論上如何能夠自我複製——ALifers 後來將此特徵作為生命的標誌。 數學家們用筆在紙上構建了細胞自動機的概念,這是一種由在二維網格上跳躍的陰影或無陰影單元組成的動態實體。 在馮·諾伊曼和烏拉姆的公式中,每個單獨的單元根據與其鄰居的簡單關係規則閃爍或關閉。 根據組成單元的初始位置,它們的簇可以展示出令人驚訝的複雜行為,例如無限期的自我複製。 數學家們對細胞自動機的研究幫助他們意識到,複製活細胞必須能夠以某種方式內化和記錄有關其環境的資訊——這一洞察力預示著當時人們越來越認識到 DNA 作為地球生命資訊儲存分子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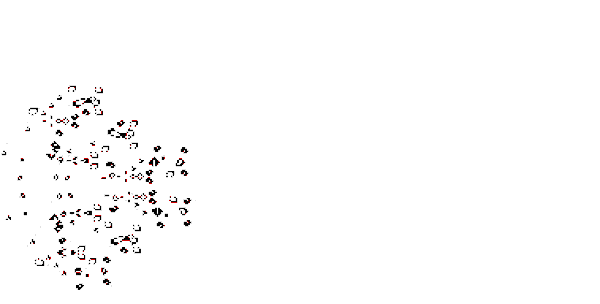
此動畫顯示了“繁殖者”(紅色突出顯示)的演變過程。 繁殖者是康威生命遊戲中細胞自動機的一個類別,它透過生成輔助模式(綠色)的多個副本來生長,每個副本隨後又生成三級模式(藍色)的副本。 這種簡單的系統可以表現出令人驚訝的複雜性,但不符合“生命”的各種其他定義標準。 鳴謝: George 對討論的衍生作品,以及 Hyperdeath/Wikimedia Commons 的 Conways_game_of_life_breeder.png (CC BY-SA 3.0)
當數學家約翰·康威 (John Conway) 在二十多年後設計了生命遊戲時,這些細胞自動機與人造生命追求之間的聯絡變得更加緊密。 首次在 1970 年 10 月版的《大眾科學》上普及,這是一個擴充套件馮·諾伊曼和烏拉姆規則的遊戲概念。 很快,康威遊戲的各種版本開始在早期的數字計算機上大規模執行,從而更容易探索出現的複雜模式和複雜行為。 生命遊戲風靡一時,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玩家成為扶手椅實驗家,在他們螢幕上閃爍的畫素星座中尋找新的數字“生物”。
從卑微的開端開始,最終出現了 ALife 的三個不同分支。 所謂的“軟”Alife,例如生命遊戲,在計算機上模擬生命。 另一個稱為“硬”ALife 的分支涉及自主機器人的創造。 第三個分支“溼”ALife 涉及使用已知的生物化學原理創造合成生物體。
在這些分支中,硬 ALife 在邁向第二次起源的競賽中落後於其他分支。 迄今為止,沒有機器人可以在沒有人類或其他機器的外部幫助下自發組裝自身。
基於軟體的生物體,即軟 ALife 的例子,已經取得了更大的進展。 它們中的一些可以在託管它們的計算機上進化並爭奪空間和時間資源。 其中一個例子是生態學家托馬斯·雷 (Thomas Ray) 開發的虛擬宇宙 Tierra,其特點是實體從一代到一代地複製、變異和相互競爭。 但是,這種虛擬化的“適者生存”仍然未能滿足開放式進化的標準:Tierra 及其同類產品中數字生物體的複雜性和新穎性最終會趨於平穩。
基於化學的溼 ALife 研究最接近真實生物學,並且通常獲得最高的科學尊重。 例如,在 2010 年代的一系列實驗中,遺傳學家 J. 克雷格·文特爾 (J. Craig Venter) 及其團隊成功地將合成基因組移植到中空的支原體細菌中,以創造出定製的自我複製細菌細胞。 2021 年,另一個科學家團隊將成團的青蛙細胞塑造成“異種機器人”,它們可以在培養皿中游動。 這些移動的斑點還可以將分散的青蛙細胞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異種機器人——這是自我複製的另一個證明。
學習經驗
最近,混合方法已經出現,專注於“生命”難題的較小部分。 例如,去年 9 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透過模擬簡單的化學系統如何表現出學習能力,將溼 ALife 和軟 ALife 結合起來。 學習是生命的標誌,因為它使生物體能夠在環境突變中生存下來。 從物種和生態系統的更大範圍來看,進化可以被認為是透過選擇性適應不斷變化的棲息地來學習。 這項工作由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家斯圖爾特·巴特利特 (Stuart Bartlett) 和法國程式設計師大衛·盧阿普爾 (David Louapre) 完成,展示了只有少數虛擬化學反應如何構成簡單模擬化學混合物的長期和短期記憶,以尋求保護免受反覆出現的“毒素”劑量的侵害。 在反覆中毒後,化學系統可以“學習”以確定製造“解毒劑”的時間——既可以先發制人也可以事後使用——以在化學威脅中生存下來。
拉斯穆森說,這項研究是“非常好的工作”,他沒有參與這項研究。 他說,這是因為它將認知某些基礎可能出現在生命出現時的閾值向後推。“我們不知道 [它] 在如此簡陋的條件下有可能出現如此複雜的行為,” 他補充道。
自由機器學習研究顧問尼古拉斯·古滕貝格 (Nicholas Guttenberg) 說,巴特利特和盧阿普爾可能已經證明了迄今為止最簡單的化學學習形式,但他沒有確定非學習系統最初是如何開始學習的,古滕貝格也沒有參與這項研究。 他指出,“學習”能力是巴特利特和盧阿普爾必須預先程式設計到他們的模擬中的東西。 他說,這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學習是否會在沒有首先人為設計的關係的情況下自發出現?”
這些問題並沒有讓巴特利特氣餒,他認為他的虛擬化學混合物是最低限度活著的。 它們消耗自由能、呈指數增長、穩定內部過程並瞭解環境——所有這些都是巴特利特個人對“生命”的工作定義的標準。 它們甚至可以複製——但它們不會代代相傳地偏離,因此它們無法實現任何類似生命的複雜性失控增長。
存在危機
西雅圖系統生物學研究所的生物化學家斯圖爾特·考夫曼 (Stuart Kauffman) 說,即使開放式進化是創造人造生命最後剩下的一個待勾選的方框,該社群的努力也可能註定要失敗。 考夫曼被視為 ALife 的創始人之一,但他現在認為實現開放式進化是該領域無法逾越的障礙,因為 ALife 研究從根本上與科學方法不相容。
考夫曼說,科學透過邏輯演繹來概括收集到的觀察結果,從而形成一個總體理論。 但不可預測性是生命開放式進化的本質,因此科學的分析方法無法預先預測野生物種的進化軌跡,他說。
用進化生物學的術語來說,生命被認為是“外適應”的,這意味著它可以將預先存在的元件用於新的功能。 控制現代魚類浮力的魚鰾被認為是從古代祖先的肺進化而來的。 讓史前鳥類保持溫暖的羽毛逐漸被重新用於飛行和求偶炫耀。“任何東西都有無限多的可能用途,” 考夫曼說。 預測進化將如何將一個特徵轉向其下一個用途的問題不是擲骰子的問題; 而是預測何時會有人出現並擲骰子打破附近的窗戶。

一位藝術家對曙光鳥的構想,這是一種長羽毛的恐龍,其化石表明它無法飛行。 羽毛與許多其他進化創新一樣,可能只是在最初履行其他功能後才被外適應用於飛行。 這種“外適應”趨勢使得預測進化新穎性的出現非常困難。 鳴謝: Emily Willoughby/Stocktrek Images/Getty Images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哲學家卡羅爾·克萊蘭 (Carol Cleland) 說,ALife 的努力可能還有另一個致命的缺陷。 她堅持認為,ALife 的構建以理解方法無法增加 N,因為每種產品都基於過於接近地球生命的假設,將其作為其唯一的參考。 另一種起源的嘗試可能會捕捉到類生命行為的幾個方面,但沒有一種可以毫無疑問地活著或從頭開始構建的新型生命例項。
克萊蘭認為,溼 ALife 的活體創造物是由生物部件組裝而成,並使用熟悉的生物化學原理指導,它們不是原始的生命形式,而僅僅是非自然的生命形式。 因此,它們並沒有告訴科學家關於生命的其他可能性。“這基本上就像拆開一輛汽車,然後透過用塑膠部件替換一些金屬部件將其重新組裝起來,然後說,‘看,我創造了一輛替代汽車!’” 她說。
硬 ALife 和軟 ALife 執行著相反的問題,即與血肉之軀相去甚遠。 它們的構建者通常假設生命的定義超越了生物體的物質形式,而是體現在其功能特性中——誰又能說這首先是概括生命的正確策略? 此外,克萊蘭認為,總是可以提出對生命的粗略抽象,以至於它無意中包括了一些非生命的例子。 她說,從僅僅 N = 1 就斷言自己知道哪些特徵是所有生命的關鍵和普遍特徵的科學家的傲慢自大,並不是悲觀的狙擊,而是一種務實的陳述事實。
“你可以探索已知生命的某些特徵,” 克萊蘭說。 “但你不能保證這些特徵對生命來說是必要的。”
在克萊蘭的概念中,硬 ALife 和軟 ALife 太抽象,而溼 ALife 又太具體。“你需要介於兩者之間的抽象層次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質,” 她說。 大多數 ALifers 都沒有忽視彌合這些差距的中間方式的需求,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知道如何從 N 的單個案例中找到它。
救命稻草
如果有人能夠重拾對 ALife 研究的信心,也許那就是聖達菲研究所的數學生物學家克里斯·肯佩斯 (Chris Kempes)。 他從生物生命的 N = 1 中提取普遍規律的策略是對地球生物多樣性進行詳細的統計分析。 大約 40 億年的開放式進化在生物世界中產生了廣泛的變異,揭示了其成員之間反覆出現的關係,並使科學家能夠推測共同的約束。
但在查明生命的共同基礎時必須謹慎。 天真地看待所有生物生命中都存在的 DNA 並斷定它對所有生命都是必要的,這將是天真的。 肯佩斯呼應了克萊蘭的擔憂,他說,關鍵是“找到正確的抽象”,既不要太具體也不要太籠統。
為了穿針引線,肯佩斯試圖將這些抽象概念與基本的物理原理和量聯絡起來。 他說,具有物理基礎的抽象概念將理所當然地成為生命定律,並且應該在宇宙任何地方的任何 N 中都成立。 這種方法可能會將開放式進化——被詆譭為 ALife 的詛咒——變成它的救星。
肯佩斯和他志同道合的 ALife 同行邏輯上推斷出了一些明顯的生命約束,例如能量,例如,“因為它是生物體想要做的每件事的預算,” 他說。 科學家們早就知道,生物體的代謝率往往會隨著體重的比例增加。 對能量-質量關係的解釋範圍從維持體溫到實現高效的迴圈系統。 “在這個空間中有一個明確定義的最優值,” 肯佩斯說。 “我認為這是一條生命定律。”
這種能量-質量關係是唾手可得的成果,但普遍理論的其他要素可能不易識別。“我確實認為我們將擁有一個完整的生命理論,儘管我不知道它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肯佩斯說。 “我認為該領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理解生命定律的列表有多長。”
處於起步階段
ALife 的模糊性質是任何處於起步階段的科學學科的特徵,其從業者認為。“ALife 是前正規化的,”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天體生物學家兼理論物理學家薩拉·伊瑪麗·沃克 (Sara Imari Walker) 說。 對於某些人來說,這種萌芽狀態只會增加現在參與 ALife 的緊迫性。 該領域的開放性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休耕但肥沃的土壤,可以孕育出可能會蓬勃發展以塑造後代研究的想法。
未定義和不受約束的 ALife 驅動其追隨者重新利用舊思想併產生新穎性。 其隱喻“樹”的三個分支——硬、軟和溼——尚未成長為高聳、發散的高度,這實際上允許任何人在它們之間攀爬。 在這種觀點中,像巴特利特這樣的科學家和像盧阿普爾這樣的 ALife 新手之間合作工作的成果與其說是研究論文,不如說是一次有效的雜交事件,類似於共生物種的進化,它們共同努力以實現共同的生存——也許有一天,甚至能實現統治地位。
當然,這些特徵可能根本不令人驚訝或獨特。 它們可能普遍適用於所有複雜性陡峭的進化行為。 最終,ALife 可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但即使這種否定也暗示著某種奇怪的謙卑而又宏偉的東西:也許,就像宇宙中生命本身一樣,ALife 的興起將被證明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