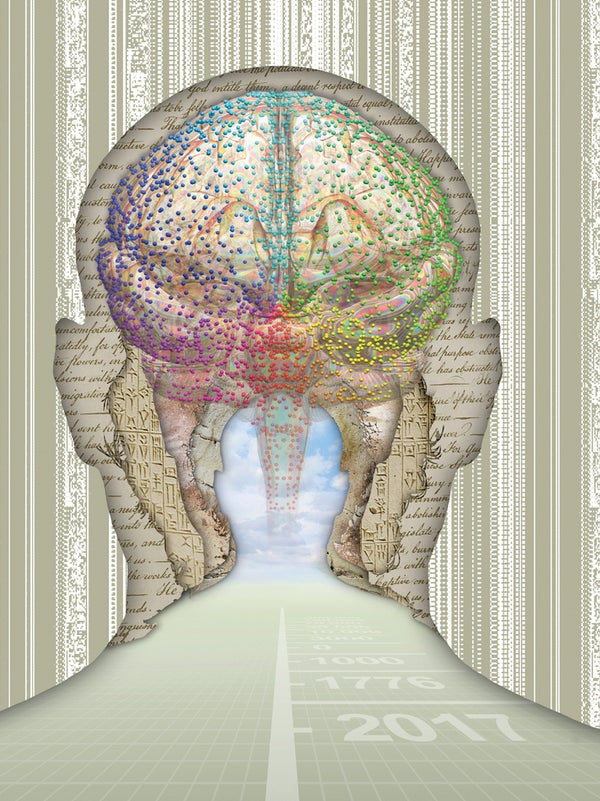海關官員睜大了眼睛。她正在檢視我的兩個行李箱的X光影像。兩個行李箱都裝滿了大大小小的塑膠容器,所有容器都單獨雙層包裝,每個容器都裝著浸泡在透明液體中的柔軟物質。“你帶的是新鮮乳酪嗎?”她問我。那是2012年6月,我正從南非經由聖保羅國際機場返回巴西。在我前面的一對葡萄牙夫婦剛剛被抓到偷偷攜帶違禁的新鮮乳酪,這種乳酪可能含有對當地牛有害的活病原體。
“不,只是大腦,”我回答道。我不怕那些珍貴的器官被沒收。我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正確,所以我耐心地等待著,坐在我仍然未開啟的行李箱旁,而她去請了合適的官員。那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有人會有一個相當有趣的故事可以講。
當困惑的官員試圖回憶起有人攜帶大腦入境時該怎麼做時,我向海關人員出示了厚厚一疊多種語言的許可證——包括宣告我的標本不構成生物威脅且沒有商業價值的檔案。我帶入境的是長頸鹿、各種羚羊、獅子、鬣狗、一頭小鬚鯨和數十種較小的非洲齧齒動物的大腦,這些動物是我的合作者在南非、剛果民主共和國、沙烏地阿拉伯、丹麥和冰島收集的。我把我的檔案遞給代理人,她讓我走了,甚至沒有開啟我的行李箱。我有點遺憾:我希望她能看到我酷炫的收藏。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事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發現和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從事動物大腦進口業務大約10年了,我從許多國家的合作者的實驗室攜帶它們。我的研究興趣是找出每個大腦包含多少神經元,這與大腦大小有何關係,以及它與人類大腦的比較情況。
十四年前,當我在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時,我開發了一種方法,使我能夠計算來自各種大小生物(包括人類和其他生物)的神經元數量,這在以前的脊椎動物大腦中是無法做到的。我的程式?把大腦變成湯。我們獲得的數字推翻了一些關於人類特殊性的舊神話,並揭示出,與其他靈長類動物相比,我們的大腦既具有獨特的強大功能,又出人意料地具有可預測性。事實上,將我們與進化上的近親進行比較表明,是技術而非解剖結構使我們能夠充分發揮我們的神經元能力。
如何製作腦漿
50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試圖給大腦細胞計數。由解剖學家漢斯·埃利亞斯在1960年代初期開創,經典的也是最廣泛使用的無偏計數方法是立體學:首先“固定”腦組織,用甲醛使其變硬,然後將其精細切片。化學染色劑隨後使細胞在顯微鏡下可見,仔細的取樣方案使科學家能夠透過少量計數推斷出大腦結構中細胞的總數。
以這種方式計算細胞的問題在於,它只能在定義明確的、同質的大腦區域中正確完成。這個過程非常費力且耗時。雖然如果使用得當,它非常準確,但它也很容易出現使用者錯誤。將該程式應用於整個大腦,特別是大型大腦,將花費很長時間。
在1970年代,一些研究人員觀察到,由於每個腦細胞的細胞核都具有一定量的DNA含量——並且每個細胞只有一個細胞核——因此應該可以提取大腦中的所有DNA,並用它來計算細胞的總數。這個想法啟發了我:如果我不從細胞核中提取DNA,而是提取細胞核本身呢?

2012年,赫爾庫拉諾-霍澤爾(左)和她裝滿標本的行李箱。她研究了數百個大腦,包括非洲象的大腦(右),以檢查神經元數量在不同動物物種之間如何變化。圖片來源:Suzana Herculano-Houzel
我認為細胞核可以從細胞中釋放出來,就像桃子中的核一樣,一旦釋放出來,就可以將它們混合在已知體積的液體中,直到它們均勻分佈,然後在顯微鏡下計數它們,而無需精細的取樣方案。正如我後來瞭解到的,我不是第一個計算遊離細胞核的人。1963年,比較解剖學家約翰·扎卡里·楊在液體中計數並染色腦組織,以估計章魚的大腦和手臂中的神經元數量。他的統計結果:5億。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數字可能太低了。我的腦漿方法能夠準確工作,而其他方法會遺漏細胞的原因是,我從固定的而非新鮮的組織開始,這使細胞核變硬,並使其能夠抵抗液化過程。當然,它最初並沒有奏效。我最初從生物化學家那裡借用了一種常用的釋放細胞核的方法:在液氮中快速冷凍腦組織,然後在攪拌機中將其破碎。可以預見的是,實驗室裡到處都是被丟擲的冷凍腦組織碎片。我母親建議:“你必須蓋上蓋子,傻瓜。”但仍然沒有用;攪拌機的壁上粘了太多的碎片。我必須確保我能收集到最後一個細胞核。
2003年,我使用洗滌劑溶解已經固定好的大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將組織在玻璃管內的洗滌劑中晃動,我將異質分佈的神經元變成了均勻分佈的遊離細胞核的湯。
然後我可以輕鬆快速地在顯微鏡下計數遊離細胞核,並且——由於每個細胞只有一個細胞核的規則——這與計數細胞一樣有效。對於大鼠大腦,我只需要大約半杯液體就可以懸浮所有細胞核,然後將它們加起來。我可以在一個上午完成這項工作。即使是大象的大腦也可以通過幾加侖的大象腦漿在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完成計數。
自2003年以來,範德堡大學和內華達大學裡諾分校的研究團隊都表明,在兩種方法都可以輕鬆應用的情況下,腦漿的計數結果與傳統的立體學相當。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香港、捷克共和國、巴西和美國的研究人員已經研究了來自鳥類、魚類、哺乳動物和無脊椎動物的腦漿。
人類真的特別嗎?
很快,我的方法開始產生見解。我發現,哺乳動物大腦皮層(大腦外層組織)中的神經元數量差異巨大——在不同物種中,從僅幾百萬到數十億神經元不等。這些細胞負責感覺整合、運動產生、個性、氣質、模式識別、邏輯推理和未來規劃,使行為不僅僅是對刺激的簡單反應。

相關的動物,例如有蹄類動物、靈長類動物或齧齒動物,具有相似的大腦結構,但神經元數量可能不同。圖片來源:Ignacio Palacios Getty Images(有蹄類動物); Anup Shah Getty Images(猩猩);Getty Images(花栗鼠)
此外,在我同事和我迄今為止進行的數十項研究中,我們尚未發現大腦皮層的大小與其中神經元數量之間存在單一的普遍關係。在我們2014年對迄今為止的研究結果的回顧中,我們得出結論,不同的規則適用於靈長類動物和非靈長類動物,與大小相似的齧齒動物或有蹄類動物相比,靈長類動物皮層中可以不顯眼地容納更多數量的較小神經元。
例如,狒狒的大腦皮層比大小相似的羚羊的大腦皮層多10倍的神經元。因此,神經元的數量不能簡單地從大腦皮層的大小來推斷。與此同時,人類的大腦皮層擁有驚人的160億個神經元,這對於我們的大腦大小來說似乎很不尋常——但只有當我們與非靈長類動物進行比較時才是如此。
長期以來,人類大腦一直被視為進化上的異常值:對於任何物種來說,它相對於身體而言都顯得過大。但根據我的資料,人類大腦實際上只是一個按比例放大的靈長類動物大腦。
2014年,我們研究了象的大腦皮層,它的大小是我們的兩倍,但發現它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神經元:56億。即使是最大的鯨魚,根據我們的說法,皮層神經元也不超過30億到50億。大多數哺乳動物的神經元少於10億。
多年來,科學家們還懷疑,人類的前額葉區域不成比例地大,前額葉是大腦皮層的一部分,除了簡單地整合感覺資訊和產生運動之外,還處理複雜的、關聯的功能。然而,在2016年,我們發現了相反的證據。我的同事和我研究了八種靈長類動物皮層中神經元的分佈,發現人類的前額葉皮層僅佔所有皮層神經元的約8%——與其他靈長類動物的比例相同。但是,由於我們的大腦皮層總體上擁有最多的神經元,因此這8%轉化為任何靈長類動物中此類神經元的最大數量。
關於其他大腦(尤其是大象和鯨魚的大腦)中前額葉神經元的數量,目前尚無定論。與我們相比,這些物種擁有大量的灰質,但大腦皮層中的神經元數量相對較少。此外,它們的前額葉皮層似乎只佔大腦的一小部分,而在人類中,它佔據的比例更大,這使得人類大腦很可能擁有最高階的前額葉神經元。
這有什麼關係呢?如果神經元是大腦的基本資訊處理單元,那麼大腦皮層中的神經元越多,它就應該越強大,而與結構的總體大小無關。到目前為止,我們擁有地球上任何單個大腦中最多的大腦皮層神經元。鑑於我們大腦的整體連線性和功能分佈實際上對於哺乳動物大腦來說非常典型,我相信,這是我們非凡認知能力的最簡單解釋。
發人深思
腦細胞是昂貴的,因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們能夠負擔得起如此多的大腦皮層神經元。儘管大腦僅佔我們身體質量的2%,但它每天消耗約佔身體運轉所需總能量的25%。
然而,在這裡,我們的大腦再次只是按比例放大的靈長類動物的大腦。透過將不同大腦消耗的能量估計值除以我們對其中神經元數量的計算,我們發現,無論大小如何,齧齒動物和靈長類動物的大腦每天每十億個神經元消耗約六千卡路里。人類大腦平均擁有860億個神經元,預計每天消耗516千卡路里,非常接近其實際測量的每日消耗量約500千卡路里。

越大並不總是越好。鯨魚和大象的大腦很大,但似乎只有相對較少的大腦皮層神經元可以幫助人類進行高階思維。與此同時,鸚鵡和鳴禽的神經元密度比哺乳動物更高。 Getty Images(鯨魚);Annick Vanderschelden Getty Images(大象);Frans Lanting Getty Images(鸚鵡)
考慮到我們的身體,人類擁有的神經元數量和大腦質量恰好符合預期。在許多舊世界和新世界猴子以及較小的靈長類動物中,大腦占身體質量的2%——就像人類一樣。突出的是大型猿類,它們的大腦占身體質量不到0.5%。特別是大猩猩,它們的體重可能是人類的三倍。由於較大的動物往往擁有較大的大腦,我們可能會期望最大的靈長類動物擁有比我們更大的大腦。然而,恰恰相反,人類大腦的重量大約是大猩猩或猩猩大腦的三倍。
大猩猩擁有龐大而昂貴的身體,可能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它們無法負擔得起能量來支援像我們一樣多的神經元。有了這些發現,我可以將比較神經科學的一個關鍵問題顛倒過來:如果由於能量限制,是大型猿類的大腦對於它們的身體來說太小,而不是人類的大腦對於他們的身體來說太大,會怎麼樣呢?
無論可用於支援大腦和身體的能量有多少,它都必須來自動物的食物。2012年,卡琳娜·豐塞卡-阿澤維多和我發表了一篇論文——基於她還是我的本科生時所做的工作——其中包含一些計算,包括不同靈長類動物的大腦和身體需要多少能量,它們從自然飲食中獲得多少能量,以及它們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找到並攝取這些能量。
我們發現,以它們目前的身體質量,大猩猩和猩猩無法負擔得起比它們已經擁有的大腦中更多的神經元。這些動物每天覓食和進食約八小時,當它們覓食和攝入八小時的食物不足時,例如在旱季,它們會體重減輕。
對於每天還需要睡七到八個小時並處理其他事務(例如保衛領土或維護社會地位)的靈長類動物來說,為了負擔更多神經元而延長進食時間不是一個選擇。沒有太多時間做其他事情了。對於需要覓食和進食這麼長時間的人來說,大學教育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由於能量攝入有限,因此身體質量和神經元數量之間存在權衡。就大型猿類而言,它們的大腦只有身體仍然允許的那麼大。
類似的限制也適用於我們:與其他靈長類動物的飲食相當,我們的祖先每天應該花費將近9.5個小時尋找食物和進食——這對於較大的靈長類動物來說是令人望而卻步的。如果他們和我們人類仍然像其他靈長類動物一樣進食,我們就無法生存下來。
然而,我們現在在這裡。如果我們的祖先沒有吝嗇神經元,沒有極其廉價的大腦,並且不能將他們大部分的清醒時間都花在進食上,那麼擺脫腦細胞能量限制的唯一方法就是徹底改變飲食。我的同事和我認為,我們祖先在大約三百萬年前找到了繞過這種限制的方法。他們透過創造切割、砍、切丁、剁碎、壓碎和搗碎的工具,改進了幸運的進化創新——雙足行走——這擴大了人們可以漫遊尋找食物的範圍。
2016年,古人類學家丹尼爾·E·利伯曼及其在哈佛大學的研究小組的研究表明,在食用前對食物進行改良——按照我的定義,即烹飪——可以提高其能量產量。利伯曼的團隊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包括一個參與者必須啃食生山羊肉的設定,這證明了舊石器時代的技術,例如用於切片和搗碎的石器,如何充分改變食物,使富含能量、耐嚼的肉類易於吞嚥。
簡而言之:我們的祖先,而且只有我們的祖先,才會烹飪。Homo culinarius,我喜歡這樣稱呼他們——也許這比自命不凡且不太可能的sapiens(意味著沒有其他物種會思考或知道)更適合我們現代人。在可以食用前改良食物的技術工具清單中,我們的祖先後來又增加了一項,即大約一百萬年前的火。同樣在哈佛大學的靈長類動物學家理查德·蘭厄姆此前曾提出用火烹飪是人類進化史上的分水嶺。

像大猩猩和猩猩這樣的大型猿類需要花費數小時覓食才能獲得足夠的能量來維持其龐大的體型。在類似的限制下,我們需要9.5個小時來尋找和消耗來自生植物的熱量。烹飪使我們從相同的食物中獲得更高的熱量,並且也使肉類更容易食用,這使我們的身體能夠負擔得起更多的神經元。 Anup Shah Getty Images(大猩猩);Christian Jegou Science Source(早期人類)
我們的研究表明,如果不是飲食的徹底改變極大地增加了我們祖先的熱量攝入,我們就無法為我們的大腦提供能量,因此就不會在這裡。烹飪,首先是不使用火,後來使用火,很可能就是這種改變。
Homo culinarius的遺產
像任何技術一樣——根據定義,技術是幫助解決問題的物體、系統或程式——烹飪為我們的祖先釋放了時間。他們可以將那些現在負擔得起的額外神經元用於其他用途。
一旦空閒時間不再是稀缺商品,我們的祖先就可以開發技術創新並將這些發現與他人分享。新工具催生了進一步的進步。我們的物種在文化和複雜性方面不斷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將我們的大腦進一步推向了更多的神經元,隨之而來,我們擴充套件了我們思維的能力。
然而,能力不是技能。從顱骨大小來看,我們現代的約160億個神經元至少已經伴隨我們存在了20萬年。我們驚人的認知壯舉——建造、寫作、調查我們自己和宇宙——要近得多。
需要一生才能將新生兒的人腦塑造成為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的、有學識的成熟大腦。在現代,我們的集體智慧和成就不再掌握在一個人手中。如果沒有足夠的人集體掌握這些知識,也沒有文化傳播,我們所有辛辛苦苦獲得的成果都可能在一代人內消失,儘管事實上我們仍然有能力做出這些事。因此,我們必須透過文化和正規教育來培養、記錄和傳遞知識和技能,以確保我們的能力能夠產生後代的能力。
我們這個物種的成就是巨大的,我們集體思考的潛力是巨大的。我們無疑已經將自己與所有其他動物區分開來。但我們從未停止成為靈長類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