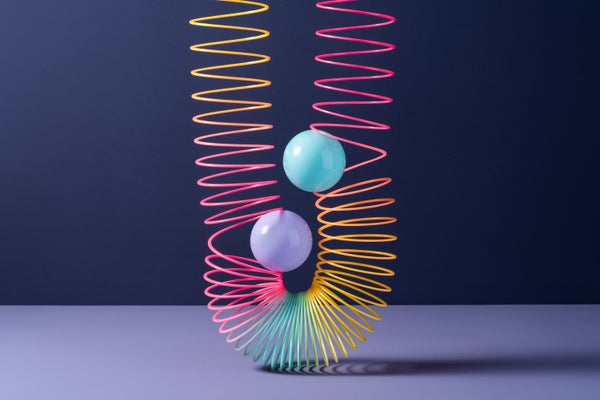萬物之底是什麼?如果我們不斷追問“為什麼?”,最終會到達哪裡?一神論信仰聲稱,我們的問題最終必須歸結為上帝,一位孤獨的、超自然的創造者。物理學家對這一假設不滿意,他們假設一切都源於單一的原始力或粒子,也許是超對稱弦,我們墮落世界中無數的力和粒子都從中流出。
請注意,儘管宗教和物理學存在諸多差異,但它們都抱有超還原論的信念,即現實歸根結底是一個東西。稱之為“一元論教條”。在過去的40年裡,我一直懷有對一元論教條並非完全理性的厭惡,原因我將在下文揭示。因此,我對以下猜想很感興趣:在現實的核心,至少有兩個東西在相互作用。換句話說,存在著一種互動,一種關係。稱之為“關係論教條”。
極富創造力的物理學家約翰·惠勒是這一概念的早期探索者。在1989年發表的論文《資訊、物理、量子:尋找聯絡》中,惠勒試圖解答“古老的問題:存在是如何產生的?”他推測,答案可能來自物理學和資訊理論的融合。前者關注“物”(its),即物理事物,後者關注“位元”(bits),定義為對是非問題的回答。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惠勒提出,“每一個物理量,每一個‘物’,都從位元,即二進位制的是非指示中獲得其最終意義,我們用‘位元生萬物’(it from bit)這句話來概括這一結論。”惠勒注意到測量在量子實驗結果中的關鍵作用,他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參與性宇宙”中,在這個宇宙中,我們把世界帶入存在,反之亦然。
物理學家卡洛·羅韋利延續了惠勒的觀點,在1996年發表的論文《關係量子力學》中,他認為量子力學破壞了“樸素實在論”,即科學發現的現實獨立於我們對它的觀察而存在的觀點。他提出了他稱之為量子力學的“關係”解釋,該解釋認為事物只存在於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中。羅韋利指出,伽利略和康德等人預見了關係視角。
羅韋利繼續闡述關係論教條。在即將發表在《意識研究雜誌》上的一本關於泛心論的論文集中,他寫道:“20世紀的物理學不是關於個體實體自身如何存在。它是關於實體如何向彼此顯現。它是關於關係的。”羅韋利認為,這種觀點不僅適用於電子和光子,而且適用於所有的現實,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相信這不足以解釋石頭、雷暴和思想。”
惠勒和羅韋利在早期的論文中都沒有引用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但他們本可以這樣做。在他獨具一格的1979年著作《哥德爾、埃舍爾、巴赫》中,霍夫施塔特深入探討了心靈和物質最深層的奧秘。與惠勒和羅韋利一樣,研究物理學的霍夫施塔特也認為,粒子只有透過與其他粒子的相互作用才能獲得屬性。但正如他的書名所示,霍夫施塔特在他的解釋世界的努力中遠遠超出了物理學的範疇,借鑑了數學、計算機科學、遺傳學、音樂和藝術。
我會說,霍夫施塔特痴迷於指涉自身、談論自身或以其他方式與自身互動的事物——尤其是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這是一個關於證明侷限性的證明。霍夫施塔特提出,意識、自我、生命、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都源於“奇異迴圈”,即那些把自己帶入存在的事物。藝術家M.C.埃舍爾在他的著名畫作《畫手的兩隻手》中提供了一個奇異迴圈的醒目影像。
另一位雄辯的關係論教條闡釋者是科學作家阿曼達·蓋弗特。在去年12月聽完她的演講後,我為我的播客節目“身心問題”採訪了蓋弗特。蓋弗特似乎致力於超越舊的二元對立,比如心靈和物質之間的二元對立。她對嚴格的唯物主義(它規定物質是根本的)和唯心主義(它堅持心靈先於物質)都不滿意。“量子力學的核心教訓,”蓋弗特告訴我,“是‘主體和客體永遠無法分離’。”
蓋弗特從各種來源汲取靈感,包括惠勒和哲學家馬丁·布伯,經典著作《我與你》的作者。她還對QBism(有時稱為量子貝葉斯主義)很感興趣,這是一種量子力學的解釋,與惠勒和羅韋利的解釋有重疊之處。根據QBism,我們每個人都透過與世界的互動創造了自己的個人世界;客觀的、共識的現實從我們所有主觀世界的互動中產生。
也許,蓋弗特推測,我們既不是生活在第一人稱世界,也不是生活在第三人稱世界,正如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所暗示的那樣。也許我們生活在第二人稱世界,而存在的基本實體不是“我”或“它”,而是“你”。“第二人稱總是處理關係,”蓋弗特解釋說,因為每一個“你”都意味著一個“我”與“你”互動。蓋弗特說,這種觀點“絕對不是唯物主義,但也不是唯心主義”。
我的一部分發現關係論教條,尤其是蓋弗特以“你”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是美好的和令人安慰的,是唯物主義的受歡迎的替代品。關係論教條似乎也符合直覺。正如詞語必須由其他詞語來定義一樣,我們人類也是由其他人來定義的,並在一定程度上被帶入存在的。否則怎麼可能呢?
此外,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我對一元論教條長期以來一直感到厭惡。這種反感可以追溯到1981年的一次迷幻藥體驗,在那次體驗中,我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孤獨的意識,宇宙中唯一的意識。除了我之外,什麼都不存在。起初,這個啟示讓我興奮,但後來它把我嚇壞了。我感到非常痛苦,非常孤獨。這種情緒伴隨著一種奇怪的智力潛臺詞。我想:一個東西和什麼都沒有之間有什麼區別?一個東西只有在與另一個東西的關係中才存在。如果我是唯一存在的東西,我可能還不如不存在。
一次非常好的旅行變成了一次非常糟糕的旅行,負面影響揮之不去;唯我論不再只是一種有趣的幻想,而是一種可怕的可能性。從那時起,我就對一元論教條持懷疑態度,無論它來自神秘主義還是科學。我擔心一元論教條是真的——一個單一的心靈是萬物的基礎——但我不希望它是真的。因此,我被關係論教條所吸引。
然而,我對關係論教條持懷疑態度,就像我對所有特權化心靈、意識、觀察、資訊的形而上學體系一樣。它們帶有自戀、擬人化和一廂情願的色彩。這就是為什麼我嘲笑以心靈為中心的理論為新地心說,這是對中世紀認為宇宙圍繞我們旋轉的信念的倒退。特別是關係論教條,讓我想起了“上帝就是愛”這句感傷的口號。
老實說,我對所有終極理論都持懷疑態度,無論是基於一元論、關係、奇異迴圈還是其他原則。約翰·惠勒在他1989年關於位元生萬物的文章結尾時,用一句令人振奮的驚歎,幾乎是一句祈禱。“當然,總有一天,我們可以相信,我們將掌握這一切的中心思想,它是如此簡單、如此美好、如此引人入勝,以至於我們都會對彼此說,‘哦,怎麼可能是其他的呢!我們怎麼可能都如此盲目如此之久!’”
我曾經和惠勒一樣渴望一種如此強大的啟示,以至於它會驅散存在的怪異性。現在我害怕這種頓悟。如果我們確信我們已經弄清楚了一切,那麼我們的創造性努力——無論是科學的、藝術的、精神的還是政治的——都可能僵化。幸運的是,我對人類的好奇心和不安分抱有信心。我的希望和期望是,世界將永遠讓我們猜測下去。
延伸閱讀:
我在我的兩本最新著作中深入探討了各種棘手的關係問題:《注意:性、死亡和科學》和《身心問題:科學、主觀性和我們真正的身份》。
另請參閱我的播客節目“身心問題”,我在節目中與阿曼達·蓋弗特和其他痴迷於存在之謎的專家進行了對話。
這是一篇觀點和分析文章;作者或多位作者表達的觀點不一定代表《大眾科學》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