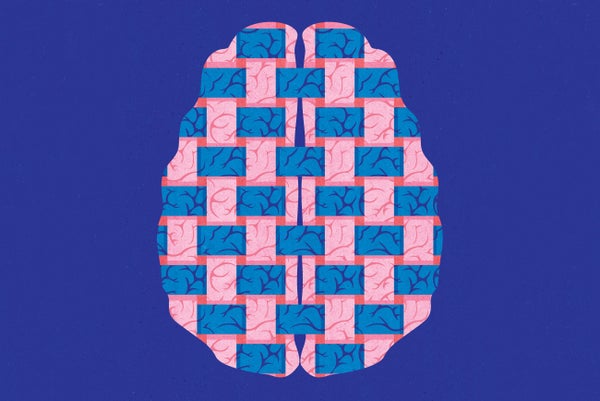2009年,特拉維夫大學的神經科學家達芙娜·喬爾決定開設一門關於性別心理學的課程。作為一名女權主義者,她長期以來對性別問題感興趣,但作為一名科學家,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強迫症行為的神經基礎。為了備課,喬爾花了一年時間回顧了大量關於大腦性別差異的文獻,這些文獻觀點兩極分化嚴重。數百篇論文涵蓋了從大鼠特定解剖結構的大小變化到人類男性攻擊性和女性同理心的可能根源等所有內容。一開始,喬爾也認同一種普遍的假設:正如性別差異幾乎總是產生兩種不同的生殖系統一樣,它們也會產生兩種不同形式的大腦——一種是女性大腦,另一種是男性大腦。
當她繼續閱讀時,喬爾偶然看到一篇論文,該論文與這一觀點相悖。這項研究由特蕾西·肖爾斯和她在羅格斯大學的同事於2001年發表,關注的是大鼠大腦的一個細節:腦細胞上的微小突起,稱為樹突棘,它們調節電訊號的傳輸。研究人員表明,當雌激素水平升高時,雌性大鼠的樹突棘比雄性大鼠更多。肖爾斯還發現,當雄性和雌性大鼠遭受尾部電擊這種急性應激事件時,它們的大腦反應方式相反:雄性大鼠長出更多的棘,而雌性大鼠最終棘的數量減少。
從這一齣乎意料的發現中,喬爾提出了關於大腦性別差異的假設,這在一個已經充滿爭議的領域中引發了新的爭議。她建議,我們不應思考女性和男性之間大腦區域的差異,而應將我們的大腦視為“馬賽克”(借用他人使用過的術語),由各種可變的、有時可變的男性和女性特徵組成。這種變異性本身以及兩性之間行為的重疊——具有攻擊性的女性和富有同情心的男性,甚至表現出這兩種特質的男性和女性——表明大腦不能被歸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或二態的類別。喬爾說,顱骨下這個三磅重的物質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喬爾與她在特拉維夫、德國萊比錫的馬克斯·普朗克人類認知和腦科學研究所,以及蘇黎世大學的同事一起,透過分析1400多個大腦的MRI腦部掃描來檢驗她的想法,並證明它們中的大多數確實包含男性和女性特徵。“我們都屬於一個高度異質的群體,”她說。
支援科學新聞事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訂閱來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事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當喬爾的研究成果於2015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表時,志同道合的科學家們稱讚這是一項突破。“這一結果是對根深蒂固的誤解的重大挑戰,”英國阿斯頓大學認知神經影像學教授吉娜·裡彭寫道。“我希望它將成為21世紀的遊戲規則改變者。”
與此同時,長期研究性別差異的研究人員強烈反對,對喬爾的方法論和結論以及她公開的女權主義提出異議。“這篇論文是以科學為幌子的意識形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神經生物學家拉里·卡希爾說,他認為喬爾的統計方法被“操縱”(儘管不一定是自覺地)以支援她的假設。其他批評則較為溫和。“個體內部存在變異性,她出色地展示了這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大腦中沒有某些區域,平均而言,男性和女性之間會存在差異,”馬里蘭大學醫學院研究大鼠性別差異的神經科學家瑪格麗特·M·麥卡錫說。
就喬爾而言,她同意遺傳、激素和環境確實會在大腦中造成性別差異。她甚至同意,如果有足夠多的關於任何一個大腦特定特徵的資訊,就有可能以很高的準確度猜測出該大腦是屬於女性還是男性。但她指出,你不能做的是相反的事情:僅僅因為你知道一個人的性別,就去觀察任何一個男人或女人,並預測這個人的大腦或個性的地形和分子景觀。
哈佛大學分子生物學家凱瑟琳·杜拉克說,儘管喬爾的研究頗具爭議,但喬爾所說的本質是正確的,她在小鼠身上的研究與喬爾的發現相呼應:“個體之間存在巨大的異質性。”承認這一事實為關於男性或女性意味著什麼的話題開闢了新的思路。對於神經科學家來說,僅僅找出大腦中的性別差異已經不夠了。現在的爭論焦點是這些差異的來源、大小和意義。這可能會對實驗室內外如何看待性別產生重大影響——也可能對藥物治療方案和治療規程是否應針對女性和男性進行專門化產生影響。“我們整個社會都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我們的生殖器將我們分為兩組,不僅在生殖能力或可能性方面,而且在我們的頭腦、行為或心理特徵方面也是如此,”喬爾說。“人們認為差異會累積。如果你在一個特徵上是女性化的,那麼你在其他特徵上也會是女性化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大多數人類都擁有性別馬賽克。”
主張與反駁
在19世紀後期,遠在核磁共振成像技術進入任何科學家視野之前,男性和女性大腦的主要可測量差異是它們的重量(自然是在死後評估的)。由於女性的大腦平均比男性輕五盎司,科學家們宣稱女性一定不如男性聰明。正如記者安吉拉·賽尼在《次等:科學是如何誤解女性的——以及正在改寫故事的新研究》一書中 recounting 的那樣,女權倡導者海倫·漢密爾頓·加德納(一個筆名)挑戰了當時的專家,她認為腦重與體重之比,或大腦尺寸與身體尺寸之比,對於智力而言,一定比單獨的腦重更相關,否則“大象可能會比我們任何人都聰明。”恰如其分的是,加德納將自己的大腦留給了科學研究。人們發現它比男性大腦的平均重量輕五盎司,但與康奈爾大學腦庫的創始人,那位著名男性科學家的大腦重量相同,而加德納的大腦就存放在康奈爾大學。(順便說一句,加德納的觀點有道理。“一旦你校正大腦尺寸,大多數性別差異就會消失,或者變得非常小,”羅莎琳德·富蘭克林醫學與科學大學芝加哥醫學院的神經科學家莉絲·艾略特說。)

圖片來源:科特里娜·祖考斯凱特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大腦中具體的性別差異主要不是神經科學家的領域,而是內分泌學家的領域,他們研究性激素和交配行為。性別決定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它始於X和Y染色體上基因的組合在子宮內發揮作用,啟動女性化或男性化的開關。但是,除了生殖和區分男孩與女孩之外,關於心理和認知性別差異的報告仍然存在。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初,已故的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埃莉諾·麥科比發現的差異比預想的要少:女孩的語言能力比男孩強,而男孩在空間和數學測試中表現更好。可以預見的是,隨之而來的是批評。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心理學家珍妮特·海德進行了薈萃分析,綜合了先前研究的結果,並發現,正如她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所寫的那樣,女性在數學方面與男性表現一樣好,“男性和女性在大多數——但不是所有——心理變數上非常相似。”基於這些結果,海德提出了她所謂的性別相似性假說,該假說認為男性和女性的心理構成與其說是不同,不如說是相似。
一旦技術使窺探活體大腦內部成為可能,就出現了一長串與交配或養育無關的性別差異。卡希爾在2006年《自然-神經科學評論》上撰文描述了“來自動物和人類的大量發現,涉及性別對大腦和行為許多領域的影響,包括情緒、記憶、視覺、聽覺、面孔處理、疼痛感知、導航、神經遞質水平、應激激素對大腦的作用和疾病狀態。”在老鼠身上,麥卡錫測量了從構成細胞核的神經元集合的大小到星形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的數量,這些細胞構成了神經元的支援系統。“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從動物一直到人類,大腦中的性別差異存在生物學基礎,”她說。但麥卡錫也強調,人類性別差異的來源比不與性別(性別的心理和社會屬性)作鬥爭的動物更復雜。“在人類中,從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被培養成特定的性別,這一事實本身就對你的大腦產生生物學影響,”她說。艾略特在她2009年出版的《粉色大腦,藍色大腦》一書中也同意這種觀點,她認為可塑性,即大腦響應經驗而變化的方式,比硬連線的生物學更能驅動行為上的性別差異。
從大腦到行為的飛躍引發了最激烈的爭論。最近一項備受矚目的研究,被指責迎合刻板印象(並被貼上“神經性別歧視”的標籤),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魯本·古爾、拉奎爾·古爾和拉吉尼·維爾瑪於201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該小組使用彌散張量成像技術,這是一種顯示神經元之間連線強度的技術,觀察了近1000名年齡在8歲至22歲之間的受試者的大腦。研究發現,男性在大腦左右半球內的連線更強,而女性在半球之間的連線更穩固。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結果表明,男性大腦的結構旨在促進感知和協調行動之間的連線,而女性大腦的設計旨在促進分析和直覺處理模式之間的溝通。”(反駁:該研究沒有校正大腦尺寸。)
尋找變異性
喬爾走進了這場漩渦之中。許多先前的研究已經確定了單個大腦特徵的差異,然後利用這些差異來聲稱整個群體——女性和男性的平均水平。喬爾和她的同事們做了相反的事情:他們使用整個群體中遇到的群體水平差異的圖景,來詢問可以對個體大腦做出哪些主張。“這是對世界的兩種不同描述,”喬爾說。兩者都顯示了相同的群體水平差異。關鍵問題是:哪種描述更能描述人類大腦——第一種,其中一種型別的大腦是男性的典型,另一種是女性的典型,還是第二種,其中大多數人的大腦是男性和女性特徵的馬賽克?
具體而言,喬爾2015年的研究提出了兩個問題:顯示女性和男性之間差異的特徵有多少重疊?大腦是否“內部一致”?後者是喬爾開發的一種衡量標準,用於確定任何一個大腦中的所有特徵是男性化還是女性化。她的團隊使用四組大型MRI資料,在每個資料集中識別出男性和女性之間差異最大的幾個特徵,例如神經細胞中心體和樹突延伸(灰質)及其連線纖維(白質)的總體積。他們發現了一個特徵連續體。明確的女性化和男性化特徵佔據了極端,中間區域表現出各種屬性的混合。
然後,研究人員逐區域評估資料集中的每個大腦,並對每個特徵進行編碼[見下圖]。他們推斷,如果大腦是內部一致的,那麼顯示性別差異的元素應該可靠地呈現男性或女性的形式。由此推論,應該很少有大腦同時具有女性和男性特徵。但是,23%到53%的大腦(取決於資料集)包含來自頻譜兩端的特徵。內部一致的大腦很少見——在接受檢查的大腦中,這一比例為0%到8%。
喬爾引用了關於單性別課堂可取性的論點,作為變異性為何重要的現實世界例子。“[單性別教育] 假設男孩有一套特徵——例如,他們更活躍,耐心更少——而女孩有另一套特徵。因此,我們應該將他們分開,並區別對待每個群體。我們正在展示的是,雖然這在群體層面是正確的,但在個體層面是不正確的。你不能將學生分成一組,他們非常活躍,喜歡運動,非常擅長數學,不喜歡詩歌,另一組是映象。很少有孩子是這樣的。”
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喬爾證明變異性的工作令人信服。“達芙娜的貢獻是逐個個體地展示了性別內部的變異性,”艾略特說。“從來沒有人發表[這些]資料。”但許多人發現內部一致性的測量存在問題。對喬爾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論文的回應之一來自新墨西哥大學的馬可·德爾·朱迪切和他的同事。他們認為,喬爾和她的同事使用的內部一致性定義過於極端,以至於在生物學上是不合理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使用完全不同的生物學變數集重新運行了喬爾的分析——例如,比較三種外觀非常不同的猴子物種的面部特徵之間的變異性。德爾·朱迪切認為,如果喬爾的方法有效,那麼猴子應該表現出跨物種的清晰(“內部一致”)的面部差異。

圖片來源:珍·克里斯蒂安森;來源:達芙娜·喬爾等人,《超越生殖器:人類大腦馬賽克》,載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第112卷,第50期;2015年12月15日
儘管這三個物種的外觀差異顯著,但任何一隻猴子的顯著面部特徵都很少能產生喬爾定義的內部一致性——因此,卡希爾認為這項研究是“被操縱的”。作為回應,喬爾和她的同事在2018年的一項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技術。在2176個人類大腦中,他們以數學而非生物學的方式測量相似性和差異,他們發現,來自女性的大腦幾乎與來自男性的大腦一樣有可能被歸類為“男性”,並且男性和女性擁有相同大腦型別的可能性幾乎與兩個女性或兩個男性相同。
爭論歸結為哪個更重要:平均值還是研究 population 內的個體。答案通常取決於所提出的問題。但是,研究人員可以並且確實會檢視相同的證據並得出不同的結論。“人類大腦可能是一個馬賽克,但它是一個具有可預測模式的馬賽克,”耶魯大學的阿夫拉姆·霍姆斯和他的同事在2015年回應喬爾時寫道,他們認為這些模式需要進行統計學考慮。生物學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是布朗大學生物學和性別發展名譽教授,也是性別差異研究的批評者,她有另一種觀點。“如果我們只談論平均差異,那將具有誤導性,”她說。“大腦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它的行為不像男性或女性那樣,並且在所有情況下其行為方式都不相同。達芙娜正試圖深入瞭解大腦實際做什麼以及它們如何運作的複雜性。”
這場爭議對科學,特別是旨在治療疾病的臨床研究的意義是重大的。1997年至2000年間,有10種藥物因其副作用危險甚至致命而被撤出美國市場。在這10種藥物中,有8種對女性的健康風險高於男性。2013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將唑吡坦(安眠藥的通用名)的女性處方劑量減少了一半。在登記了患者關於早晨通勤時昏昏欲睡的抱怨後,研究人員發現,一些女性在醒來時體內仍然存在該藥物。在這裡,也出現了反駁。哈佛大學科學史和性別史學家艾略特和莎拉·理查森認為,唑吡坦副作用的大部分差異可能可以用體重差異來解釋。體重並不是全部原因,因為女性較高的體脂水平會導致某些藥物代謝得更慢,但精確識別藥物劑量的真正關鍵變數應該是可能的。
部分是為了回應這些擔憂,從2016年1月開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要求所有臨床前研究(人體試驗前的階段)必須包括雌性動物。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婦女健康研究辦公室主任珍妮·克萊頓在解釋這項新政策時謹慎地說,在研究中納入兩性並不一定意味著要尋找性別差異。許多人認為這項指令是一個重要的步驟。麥卡錫指出,各種早期發病的神經系統疾病或障礙,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和自閉症譜系障礙,在男性中更常見,而那些較晚出現的疾病或障礙,如抑鬱症和焦慮症,在女性中更常見。“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得不將大腦視為男性和女性之間存在生物學差異的生物器官,”她說。“不這樣做將是可悲的。”但喬爾、福斯托-斯特林和其他人擔心鐘擺會擺得太遠。他們主張進行將性別作為變數的研究,男性和女性受試者的數量均等,但在分析結果時要認識到,“男性”和“女性”類別可能反映與性別無關的變數。
更廣泛地說,如果這項工作要改變社會對性別和性別的看法,它可能從術語開始。“是時候拋棄‘二態性’這個詞了,”艾略特說。“二態結構是卵巢與睪丸。灰質與白質比率相差2%不是二態性。這只是與性別相關的差異。”
杜拉克認為,我們需要“更精細的方式來定義這些差異”。她在小鼠身上發現,控制雄性交配行為的神經迴路也存在於雌性中,而母性行為迴路也存在於雄性中。“從我們的工作中得出男性和女性之間沒有差異的結論是錯誤的,”杜拉克說。“但非常有趣的問題是:這些差異是如何出現的,以及它們有多麼細微或重要?”
麥卡錫和喬爾於2017年聯手,為定義性別差異研究中正在測量的內容及其含義,提出了一個更復雜的框架。他們提出了四個可能的維度:特質是持久的還是短暫的;它是否取決於情境;它是隻採取兩種形式之一(因此是真正的二態性),還是落在光譜上;以及它是性別的直接還是間接後果。這種描述性別差異世界的方式遠不如長期以來的火星與金星的比喻那樣引人注目,但它可能更準確。作為一般規律,複雜性更貼切地反映了人們的真實面貌。“我的母親非常 nurtures,但她在空間導航方面比我的父親強得多,”艾略特說。“那是一個馬賽克,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