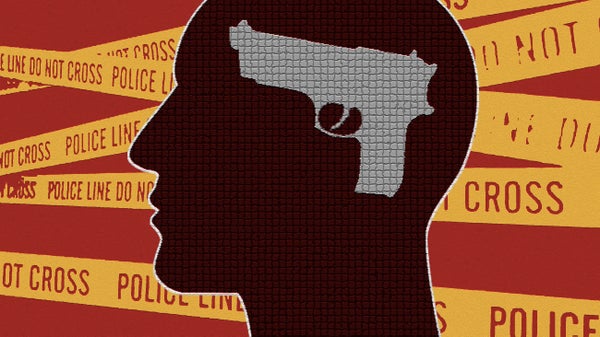2018年10月2日,警察心理學家勞倫斯·米勒出庭為傑森·範戴克辯護,範戴克是一名白人警察,於2014年槍殺了來自芝加哥西區的黑人青少年拉寬·麥克唐納。案件的事實對範戴克不利。作為芝加哥警察局一名有著13年資歷的老兵,他在下警車的幾秒鐘內向麥克唐納開了16槍。雖然麥克唐納手持據報道曾用來破壞巡邏車的刀,但這位17歲的少年是在街中央背對著警察時被槍擊的。這些事件均無可爭議。槍擊事件被另一輛警車的儀表盤攝像頭拍了下來,範戴克被指控犯有一級謀殺罪、16項持槍嚴重傷害罪和一項瀆職罪。
這位67歲、居住在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的米勒並非來爭論外部事件。相反,他要求陪審員關注範戴克對槍擊事件的感知。在擁擠的法庭中,燈光調暗,米勒展示了一份題為《致命武力對抗的神經心理學》的幻燈片。他解釋說,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身體的壓力反應會扭曲認知、感知和記憶。對於警察來說,這可能會導致他所稱的“致命武力心態”現象,在這種心態下,警官會被確保當下生存的神經遞質和激素淹沒,感覺自己唯一的選擇是殺死或被殺。米勒辯稱,範戴克應被判無罪。陪審員在米勒作證期間做了筆記。
當然,在法庭上使用心理學家並不新鮮,辯護律師和檢察官長期以來都依賴專家證詞來幫助解讀驅動人類行為的複雜化學激素和電脈衝湯。但在警察槍擊案辯護中使用心理學則不太常見——部分原因是很少有警察最終被審判。保齡格林州立大學犯罪學家菲利普·斯廷森表示,自2005年以來,美國只有96名警官因執勤期間槍擊事件被逮捕,罪名是謀殺或過失殺人,而且此類案件很少能進入法庭。但當它們確實發生時——一些專家認為,隨著記錄警察與嫌疑人互動的攝像機激增,這種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普遍——關於警察工作獨特且壓力巨大的心理場景的證詞已成為辯方的主要內容。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然而,一些心理學家認為,雖然壓力生物學已得到充分證實,但其與致命武力的聯絡遠不那麼明確。雖然警官在致命對抗期間可能會經歷認知和感知障礙,例如管狀視野和分離感,但研究人員最終對這些障礙在決定使用致命武力中所起的作用知之甚少。在缺乏嚴謹科學的情況下,心理學家們對使用壓力神經生物學為殺人警察辯護持懷疑態度。
紐約城市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教授、警察公平中心(一個研究刑事司法政策中種族差異的智庫)聯合創始人兼主席心理學家菲利普·阿提巴·戈夫說:“辯方使用了一種似乎是開脫責任的論點,儘管沒有實際資料,聲稱‘你不應該負責任,因為這是工作壓力水平’。” “對於科學來說,這是一個糟糕的領域。”
10月5日,芝加哥的陪審員最終裁定範戴克犯有16項持槍嚴重傷害罪和二級謀殺罪。量刑日期尚未確定,雖然範戴克的律師上週仍在為重審奔走(法官駁回了這些動議),但在最初審判後的電話採訪中,米勒表示,他的證詞可能至少部分促使陪審團做出了二級謀殺而非一級謀殺的判決。法律專家表示,這是一個較輕的指控,似乎表明陪審員認為範戴克感到自己處於危險之中,即使他的反應是不合理的。
米勒是否在促成這一結論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我們不得而知,但為此報道採訪的幾位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表示,如果陪審員確實受到了米勒的影響,那也是基於充其量是站不住腳的科學。
米勒本人完全不同意。“關於壓力相關的認知扭曲的科學資料庫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前,”米勒說。“壓力的神經生物學和神經心理學是已確立的科學。”

2018年10月2日,勞倫斯·米勒博士在警官傑森·範戴克槍殺拉寬·麥克唐納案的審判中作證。圖片來源:安東尼奧·佩雷斯-普爾 蓋蒂圖片社
米勒的證詞主要圍繞警察經常面臨的壓力和威脅的嚴峻考驗。
“如果你的汽車滑出道路,糾正它;如果有人在追你,躲開他們,”米勒在審判中作證說——並補充說,急救人員的情況有所不同:“即使他們的大腦告訴他們,‘跑!逃跑,救自己,’他們的工作恰恰相反。他們必須迎著危險跑去,”他作證說,這表明,違背生存的生物本能會加劇危險感,並增加對威脅的感知。
米勒接著詳細描述了各種大腦結構的功能,以及構成所謂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 (HPA) 軸的相互作用和反饋迴路,HPA 軸是神經內分泌系統的一個特徵,調節著一系列生物過程,例如皮質醇和去甲腎上腺素的分泌。米勒解釋說,在緊急情況下,杏仁核會向下丘腦(大腦的某種指揮中心)傳送求救訊號,從而啟動交感神經系統高速運轉。身體的“戰鬥或逃跑”反應隨後被啟用,使其暫時浸泡在有助於確保生存的化學物質中。
米勒的核心論點確實具有一些明顯的優點。丹尼爾·賴斯伯格是裡德學院專門研究感知、認知和法律的心理學教授,他指出,經歷過槍戰的警察自然經常將其描述為壓力極大。“我們的身體有一種相當完善的機制,可以在我們承受壓力時啟動,”賴斯伯格說。
一些研究人員(包括賴斯伯格)表示,問題在於,當米勒和其他少數經常為警察辯護的專家進一步涉足未經證實的,或者至少是非常投機的心理學和神經學科學前沿時。金伯利·麥克盧爾是西伊利諾伊大學的心理學和法律教授,例如,她指出,由於壓力反應具有高度個體性,米勒必須清楚地確定那些可能在範戴克下車前的幾秒鐘內啟用 HPA 軸的因素。雖然研究人員一致認為壓力會扭曲感知,但沒有太多同行評議的研究將這些扭曲與開槍射擊致命武器的決定聯絡起來。
麥克盧爾說,警官接受的關於使用致命武力的培訓傾向於側重於警官處理武器的質量——裝彈、卸彈和發出指令。“較少的研究關注認知因素,”她補充說,“例如壓力下的決策和記憶。”
當然,警察接受過訓練,要抵制逃離現場的衝動,專家表示,適當的培訓和經驗可以使警察能夠在威脅性對抗中抑制壓力的某些影響。研究還發現,關於何時使用武力的明確而嚴格的部門政策可以幫助消除警官酌情權方面的錯誤。在審判期間,檢察官辯稱,範戴克自己在到達現場之前所說的話,正如他在兩年後與米勒進行心理評估時描述的那樣,表明一名警官已準備好進行暴力互動。“如果他在攻擊他們,他們為什麼不射殺他呢?”當透過無線電傳來一名青少年破壞警車的訊息時,他回憶起問他的搭檔。“哦,我的天哪,我們得開槍打死那傢伙。”
雖然研究人員很難知道警察在威脅性對抗中在想什麼,但影響他們決定使用武力的因素正在慢慢被理解。由於研究人員不在真實世界的致命對抗現場,他們會建立高壓力的自然角色扮演場景,讓警官決定是否使用武力,然後在事後分析他們的決策過程。此類研究是新的,它發現,警察使用武力最強大的預測因素不是壓力水平,而是嫌疑人的“不合作”行為,例如肢體攻擊或拒捕。
事實上,發表在《刑事司法與行為》雜誌上的201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許多警官在困難的對抗中並沒有經歷壓力症狀。該研究的作者透過分析91次“彙報會議”評估了使用武力決策,這些會議是在新招募的警官參與了兩種假設情景後進行的:一種涉及家庭暴力,另一種涉及醉酒嫌疑人。雖然研究中的大多數新兵報告了一些形式的壓力相關障礙,但只有約11%的人報告了感知障礙。
然而,在那些確實經歷過障礙的人中,症狀影響了他們執行一些精細運動任務和“成功執行武力技術”的能力。作者表示,對於這些人來說,壓力可能會導致對情況的錯誤評估,從而導致警官或嫌疑人受傷。但專家建議,需要對這些方面進行更多的研究——包括大學科學家與警察部門合作進行的研究——才能瞭解這些扭曲在現實世界中發生的程度,以及它們在警官扣動扳機時所起的作用。“研究的作者指出,“仍然不清楚的是,警官們是如何做出這些武力決定的。”

在範戴克的謀殺案審判期間,播放了一段動畫影片,描繪了芝加哥警官傑森·範戴克和拉寬·麥克唐納。米勒作證說,致命武力案件最終歸結為警官的感知。圖片來源:安東尼奧·佩雷斯-普爾 蓋蒂圖片社
米勒擔任警察部門的心理學顧問已有近 20 年。1988 年,他獲得了紐約城市大學心理學系的博士學位,專業是神經認知。他持有佛羅里達州的心理學執業執照,並於 1998 年在那裡完成了法醫鑑定人培訓。如今,他經營著自己的私人診所,主要為西棕櫚灘警察局和棕櫚灘縣警長辦公室提供諮詢服務,評估警官在參與致命武力對抗和其他令人痛苦的情況後的狀況。
米勒在證人席上說,他曾作為專家證人在四到五起備受矚目的案件中作證——通常是為辯方作證。他在需要出差的案件中擔任專家證人的費用為每天 10,000 美元(他在範戴克的案件中作證了一天)。範戴克的辯護團隊還為 2016 年 4 月 1 日對米勒進行的心理評估支付了 10,000 美元。為此報道接受採訪的多位專家表示,只有少數心理學家被要求為範戴克案件之類的武力使用案件辯護。心理學和法學學者不相信研究的力度足以支撐法庭的需要。
為了確定專家證人的科學證詞是否基於合理的科學推理,法官經常使用所謂的多伯特標準——該標準以 1993 年最高法院的一個案例命名,在該案例中,一個家庭起訴一家制藥公司,原因是他們認為處方藥導致了出生缺陷。為了使科學證詞符合多伯特標準,它通常必須基於科學界廣泛接受的同行評議研究。
麥克盧爾和其他專家認為,在警察槍擊案辯護中使用的研究往往未能達到這一門檻。“我們根本沒有足夠多的與警官在致命武力對抗期間的決策相關的學術研究來滿足該領域科學的多伯特標準,”麥克盧爾說。在審查米勒的證詞後,麥克盧爾注意到,同行評議的引用文獻少得可憐,這讓她感到震驚。“專家在這些案件中提供證詞似乎為時過早。”
米勒為自己的證詞辯護說,多伯特標準最初是為了評估其他法醫科學技術而制定的,例如化學分析,它並不能完全適用於臨床心理學等領域。“應用於心理學,它通常指的是使用心理測量學測試和測量來評估認知、人格、腦損傷等,”他透過電子郵件說。“臨床醫生和律師都認為,將該標準應用於臨床檢查非常困難。”由於米勒在評估範戴克時沒有使用任何心理測量學測試,因此他不認為多伯特標準是其證詞的有用框架。
該證詞引用了警察心理學家威廉·萊溫斯基和亞歷克西斯·阿特沃爾的研究,他們認為,在致命武力對抗中,警官普遍報告感知扭曲——而這些扭曲為開槍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萊溫斯基拒絕接受本文的採訪,他經營著武力科學研究所,該研究所的研究小組除其他外,還研究“在快速展開的事件中,大腦是如何運作的”。與米勒一樣,萊溫斯基之前也被為警察行為辯護的律師傳喚到法庭,他在法庭上解釋了壓力和扭曲如何對警官在致命武力對抗期間的感知產生深遠影響。
《紐約時報》的一篇人物特寫更直率地評價了萊溫斯基在法庭上的作用:“當警察在可疑情況下射殺他人時,萊溫斯基博士經常會為他們的行為辯護,”該報指出,並補充說,他作為專家證人的收費為每小時 1,000 美元。萊溫斯基被他的同事指責在證人席上傳播“垃圾科學”,他引用的研究發表在警察行業雜誌上,有效地繞過了同行評議過程。華盛頓州立大學心理學家麗莎·富尼耶受司法部委託審查萊溫斯基的研究後表示,這項工作是“無效且不可靠的”,她質疑“萊溫斯基先生將相關且可靠的資料應用於回答問題或支援論點的能力”。
米勒承認,“萊溫斯基的大部分工作都處於案例研究和實證研究的邊緣。”案例研究是幫助講述一名警官故事的軼事。米勒說,它們是“實證測試的先兆”,因此應該具有一定的分量。但為此文采訪的其他專家堅持認為,案例研究不能替代系統的同行評議研究,後者有助於我們瞭解數千名警官的想法和行為。米勒解釋說,在作為專家接手任何案件之前,他都會沉浸在同行評議的文獻中,並將自己在該領域數十年的經驗和臨床判斷作為參考。
當然,每個人都應該得到有力的辯護。“但辯護也必須是合理的,”美國心理學雜誌的編輯富尼耶說。這意味著專家證人應無利益衝突,避免斷章取義,並且只引用同行評議的文章。在為司法部審查了萊溫斯基的研究後,富尼耶說,她對在法庭上被用來為使用武力辯護的“科學”感到“害怕”。她認為,背景是關鍵。科學家們對人體壓力反應瞭解很多。但他們對壓力如何影響警察(他們接受過在高度壓力場景下履行職責的訓練)以及壓力對他們是否開槍的決定有什麼影響知之甚少。

示威者慶祝有罪判決——儘管米勒認為他可能幫助說服陪審員選擇了較輕的二級謀殺罪。圖片來源:約書亞·洛特 蓋蒂圖片社
儘管警察部門和心理學家已經合作了幾十年,但美國心理學會直到 2013 年才正式承認警察心理學為一門專業。美國心理學會對警察心理學的廣泛定義是,旨在確保執法人員和其他公共安全人員安全、合乎道德且合法地履行職責。當兩個不同的學科結合在一起時,自然會產生道德問題,一些心理學家擔心專家證人在法庭上呈現其領域科學的方式。
國家司法研究所1994 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對心理學家僅在壓力管理培訓中解決過度使用武力問題表示擔憂。“以這種方式對待它是否會鼓勵人們認為壓力是過度使用武力的藉口?”該報告的作者艾倫·M·斯克裡夫納問道。警察公平中心主席戈夫回答了這個問題:“推進一種科學理論,認為由於警察所從事的工作以及我們訓練他們的方式,壓力現在應該成為執法部門的開脫責任的理由,這在道德上令人震驚。”
藉口和解釋之間的界限有多細微?“壓力或任何其他因素都不是任何不當行為的藉口,”米勒說。“我同意,不應該僅僅因為任何精神狀態或狀況就本能地為一名警官(或任何人)開脫責任。” 米勒在證人席上作證說,這些致命武力案件最終歸結為警官的感知。現在,越來越多的警察佩戴了行車記錄儀和隨身攝像頭,陪審團可以將警官的證詞與其他證據進行權衡。米勒認為,影片錄影對執法部門來說是“喜憂參半”,並且在範戴克的案件中,反覆向陪審團播放的錄影並沒有“準確地描繪出急救人員的感知”。
在法庭上,範戴克的首席辯護律師詢問米勒,是否有關於警察使用武力的心理學的科學文獻。米勒在回應中說:“我今天想明確說明的一件事是,我在警察心理學領域將要作證的幾乎所有內容都源於一個更大的領域,這個領域可以追溯到近一個世紀前,即大腦對緊急情況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反應。”
儘管對壓力的科學研究可能歷史悠久,但其他專家認為,從該科學推斷出來解釋——或開脫——某些行為的做法要複雜得多。麥克盧爾最近評估了科學研究在警官參與槍擊事件政策中的應用,她說,專家證人有責任幫助法官、陪審團和律師瞭解現有的知識。但專家還應該“認識到我們所掌握資訊中的差距,”她說。
“存在許多差距,重要的是要找出這些差距:一是,以便研究人員可以在這些領域進行更多研究,二是,”她繼續說,“以便我們可以更好地告知法院我們以更高的確定性瞭解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