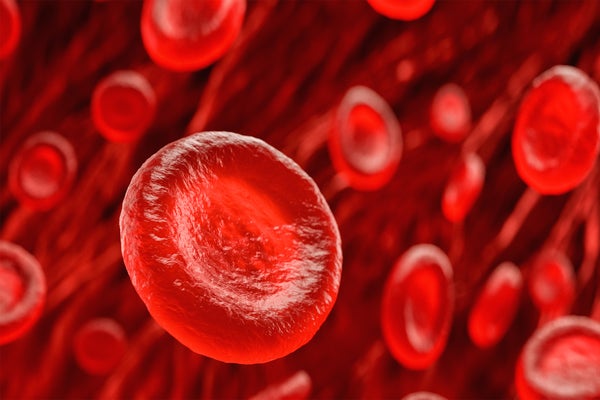去年秋天,美國監管機構在萬眾矚目下批准了兩種用於治療鐮狀細胞病的基因療法,隨後歐盟和英國也紛紛效仿。 許多人希望這些療法能為這種遺傳病提供“功能性治癒”,這種遺傳病會導致紅細胞僵硬、變形,從而導致貧血、劇烈疼痛、血管和器官損傷、中風風險以及預期壽命縮短。 這些鐮狀細胞療法也使我們更接近“CRISPR醫學”時代,在這種時代中,新的基因編輯工具可用於修復一系列使人衰弱的遺傳疾病,包括杜氏肌營養不良症和癌症。
對於全球八百萬人(包括美國十萬人)患有鐮狀細胞病的人來說,這些基因療法可能會改變他們的生活。 然而,批准後,人們的注意力立即轉向了治療的過高成本。 一家公司以 220 萬美元的價格出售其療法,另一家公司則以 310 萬美元的價格出售。 其他基於基因的療法也有類似的價格標籤。
降低這些療法的成本固然重要。 然而,這不太可能讓大多數鐮狀細胞病患者和其他遺傳病患者的生活變得更好。 許多人根本無法或不願意接受這些治療,這些治療需要在數月內多次就醫(通常需要過夜)。 事實上,我們已經知道,由於多種原因,許多人沒有在美國獲得針對鐮狀細胞病的現有治療。 在每年多次發生與血流阻塞相關的疼痛發作的患者中,只有 35% 的人接受了最常見且最便宜的藥物羥基脲,並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單獨接受這種藥物治療。 只有 13.2% 的多次疼痛發作患者接受了一種或多種自 2017 年以來批准的新藥,無論是與羥基脲聯合使用還是單獨使用。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方式是 訂閱。 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人們已經很難獲得鐮狀細胞病的治療,因此降低基因療法的成本不會使治療更容易普及。
理解了這一點,如果我們把成本以外的護理障礙視為創新問題會怎樣? 如果技術為社會服務的最佳方式,特別是為了促進公平,是政府和創新者關注的不僅僅是創造可能拯救生命的療法,那又會怎樣? 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社會和健康挑戰根本不是科學家或生物技術公司的責任。 但如果目標是為了讓人們健康,而不是僅僅將無法普及的產品投放市場,那麼這些挑戰就必須是責任所在。
目前,許多科學家、醫生和患者將這些療法視為在幾代人的歧視和虐待之後,邁向種族平等的重要一步——鐮狀細胞病主要影響非洲、南亞和中東血統的人。
然而,許多鐮狀細胞病患者收入有限,不太可能自掏腰包支付治療費用; 50% 的患者都在醫療補助計劃 (Medicaid) 中。 作為回應,私人保險公司和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 都在制定針對細胞和基因療法的“基於結果”的報銷計劃。 根據這些計劃,如果治療在預先設定的年限內效果不如預期,製藥公司將向付款人報銷費用。
但這只是等式的一部分:許多鐮狀細胞病患者根本沒有參與基因療法全過程所需的護理基礎設施——包括初級保健醫生或專科血液科醫生。 這種護理基礎設施的缺失可能是由於不穩定因素造成的,包括缺乏就業、住房或醫療保健,或者對人們幾十年來遭受種族歧視的科學和醫療機構的警惕。 從事服務行業並按小時工資領取工資的人無法輕易或頻繁地離開工作崗位。 想要生育孩子的人也可能不想參與,因為新療法涉及可能影響生育能力的化療。
除了功能性治癒的想法之外,對於大多數鐮狀細胞病患者來說,他們眼前的首要任務是減輕他們所經歷的劇烈疼痛。 事實上,正如迦納鐮狀細胞專家 Felix Israel Domeno Konotey-Ahulu 在 1975 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樣,幾種西非語言中這種疾病的名稱——chwechweechwe (Ga)、nwiiwii (Fante)、nuidudui (Ewe) 和 ahotutuo (Twi)——都是鐮狀細胞病患者所經歷的持續和重複的齧咬疼痛的擬聲表示。
然而,由於鐮狀細胞病被認為是血液疾病,科學家和工業界已將注意力集中在糾正血細胞功能障礙上。 很少有科學努力集中在為該人群開發新的疼痛治療方法或研究現有療法治療疼痛的療效上。 相反,當患有這種疾病的人去急診科尋求止痛時,他們常常被認為患有物質使用障礙。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觸發響應公眾需求並認真對待人們生活經驗的創新呢? 首先,政府必須改變誰來設定研究議程以及如何設定。 包括高級別諮詢委員會在內的技術專家目前為大多數資助機構設定優先事項。 這導致優先考慮科學和工業優先事項,例如關注新穎性和效率,而不是受疾病影響的個人的需求。
例如,鐮狀細胞病患者和其他了解疾病對社會影響的專家很少發揮作用; 在美國國家心肺血液研究所鐮狀細胞病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中,只有兩名是基層疾病倡導者。 社會中許多服務不足的疾病都是如此。
如果歷史上、心理上和社會上了解鐮狀細胞病的人坐在該委員會中會怎樣? 他們可能會引導更多注意力關注疼痛和解決科學、技術和醫學中的種族主義問題。 他們還可能鼓勵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臨床、社會和基礎研究部門之間的合作,而不是根據科學或醫學專業定義研究專案。
其次,政府可以將資金引導到專注於更直接利益的跨學科研究專案。 他們可以鼓勵生物醫學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患者之間進行真正的合作,以便了解技術可能產生的影響,從而為技術的設計和開發提供資訊。 (國家科學基金會正試圖透過其新的技術負責任設計、開發和部署計劃來率先採用這種方法。)患有鐮狀細胞病的人和社會科學家,如果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也可以加入撥款審查委員會,以確保資助專案的組合符合他們的知識和關切,而不僅僅關注疾病的分子決定因素。
第三,私營部門也必須承擔責任。 建立激勵措施的一種方法是透過指數,例如環境可持續性指數,公開評估公司的社會和公平影響。 這些指數將評估公司產品的實際社會後果,包括是否以及如何將患者納入其創新流程,而不是迫使人們簡單地相信關於技術變革潛力的說法。
為了開發成功解決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的技術,並確保人們從創新中受益,我們需要公共和私營部門在創新過程的早期投資於高影響力的跨學科專案,並且——最重要的是——重視患者的專業知識。 否則,花費數十億美元建立和數百萬美元管理的療法將繼續是那些最需要它們的人無法企及的。
這是一篇觀點和分析文章,作者或作者表達的觀點不一定代表《大眾科學》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