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上,一切看起來都很簡單。一瞬間,嫌疑人揚起了嘴角。他很高興,因為他認為調查人員搞錯了炸彈的放置地點。但是當審訊員提到正確地點時,恐怖分子的臉上閃過一絲怒火。當他宣佈自己無罪時,他聳了聳肩。在專家看來,證據確鑿:嫌疑人的肢體語言與他的話語相矛盾。他在撒謊。
電視連續劇《Lie to Me》中研究微表情的專家是保羅·埃克曼(Paul Ekman)的另一個自我,他今年 86 歲,是世界著名的謊言和情感研究者。他不僅為該節目的創作者提供諮詢,還曾被眾多美國機構聘請,如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埃克曼的信條是,真相寫在我們的臉上。
這種想法由來已久。公元前 900 年左右的一部古印度文獻描述了一個試圖投毒者的行為如下:“他不回答問題,或者他們的回答是含糊其辭的;他胡言亂語,用大腳趾摩擦地面,並且發抖;他的臉色發青;他用手指揉搓髮根。”
支援科學新聞事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事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
在評論 20 世紀初的一個案例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寫道:“有眼能看、有耳能聽的人可能會確信,沒有人能保守秘密。如果他的嘴唇沉默,他會用指尖喋喋不休;背叛從他的每一個毛孔中滲出。” 自那個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安全專家一直在嘗試透過使用測謊儀來區分真相與謊言。其中,所謂的測謊儀記錄了當提出某些問題時,汗液分泌、心率和呼吸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與祖先相同的工具來區分真假:我們的眼睛和耳朵。
從 1971 年到 2004 年,埃克曼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擔任心理學教授,現在是榮譽退休教授。在那之前,他成為第一位大規模研究面部和身體可觀察到的變化如何反映說真話或撒謊的研究人員。在 20 世紀 60 年代,他為基本情感(憤怒、厭惡、快樂、恐懼、悲傷和驚訝)提出了普遍面部表情理論。埃克曼將參與產生這些表情的面部肌肉分類為他所謂的面部動作編碼系統。他和他的合著者華萊士·V·弗裡森在他們 1969 年發表的論文《非語言洩露和欺騙線索》中為埃克曼流行的謊言理論奠定了基礎,該論文處理了患者的非語言訊號。核心思想是:一個人試圖隱藏的情緒有時會被面部表情和手臂、手、腿和腳的動作所背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瞬間的面部表情,持續時間不超過四分之一到半秒,對於沒有經驗的觀察者來說幾乎是不可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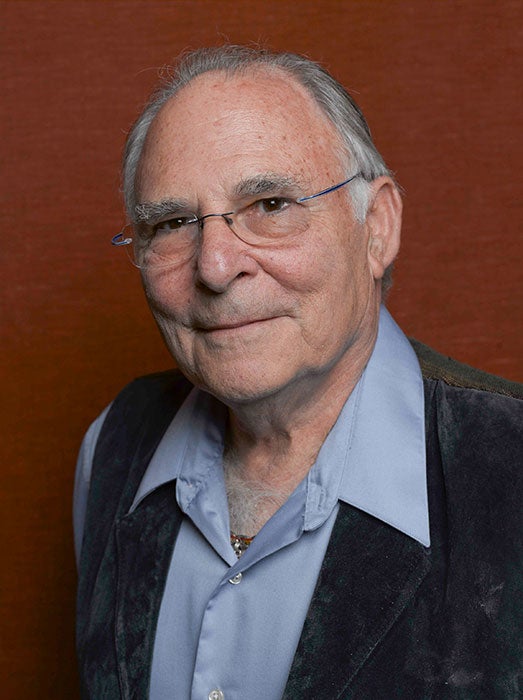
保羅·埃克曼。圖片來源:Steven Dewall Getty Images
然而,根據埃克曼的說法,這種揭示隱藏情緒的微表情並非經常發生。我們更傾向於觀察到被中斷或不完整的情緒。例如,如果我們試圖偽裝恐懼或悲傷,我們額頭上特有的皺紋可能不會顯現出來。眼部肌肉也可能不會參與虛假的微笑。埃克曼不認為這種差異是虛假的證據。他只是認為它們表明可能有些不對勁。這就是為什麼重複和多樣的線索是必要的;一個是不夠的。在他的著作《Telling Lies》中,埃克曼聲稱,在實驗室實驗中,僅憑面部表情就能區分真假,準確率超過 80%,而當面部和身體動作、聲音和語言等因素都納入分析時,準確率達到 90%。
但這些統計資料可能具有誤導性。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的瑪麗亞·哈特維格認為,這種說法“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相比之下,研究文獻表明,成功率通常僅略高於偶然。即使埃克曼要求對測試人員進行廣泛的培訓,他顯然也沒有發表過任何一項研究來證實他的資料。
德國美因茨約翰內斯·古騰堡大學的法律心理學家克里斯蒂娜·蘇霍茨基說:“許多研究人員並沒有特別認真地對待埃克曼關於使用微表情來揭示欺騙的想法。” 這不僅僅是因為缺乏經驗證據。該理論本身就不充分。“僅僅因為某人在審訊過程中感到害怕,並不意味著他們在撒謊,”她說。“你不能從一種情緒中推斷出欺騙行為。”
蘇霍茨基目前是德國在謊言領域最活躍的研究人員。她專注於可能與虛假陳述相關的精神努力的證據。撒謊絕非易事。一個人必須努力隱藏真相,想出一個看似合理的替代故事,設身處地為審訊者著想,並嚴格控制可能暴露真相的情緒——同時還要始終顯得真實。“到目前為止,情緒和認知是分開研究的,”蘇霍茨基說。“我想把兩者結合起來,並闡明一個人撒謊時大腦中會發生什麼。” 她不認為使用微表情來識別欺騙是一種特別有前途的方法。“根本沒有研究支援埃克曼的說法,”蘇霍茨基說。
2008 年,心理學家斯蒂芬·波特和莉安·滕·布林克對這一主題進行了一項為數不多的獨立研究。他們的測試物件被要求在觀看悲傷、引發恐懼和歡樂的圖片時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如果他們試圖模仿不同的情緒,他們的面部表情往往會更加不和諧或不協調。在所有快照中,微表情的出現率為 2%。它們在 22% 的測試物件中出現——但不僅僅是在他們試圖掩飾自己的感受時。
然而,埃克曼和他的批評者都同意一點:人類通常是非常糟糕的謊言探測器。最常被引用的命中率來自一項薈萃分析,該分析基於約 25,000 名測試物件。他們僅在 54% 的情況下猜對了——僅僅略好於碰運氣。僅就錄音帶而言,成功率為 63%,這意味著它明顯高於有聲或無聲錄影帶。顯然,影像分散了觀看者對相關線索的注意力。專業人士——警察、法官或精神科醫生——更頻繁地處理謊言,但這無關緊要:所謂的專家並不比街上普通人做得更好。
但是,當一個人像瞭解自己的孩子一樣瞭解某人時,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一項加拿大實驗研究了父母是否比其他父母或本科生更能識別孩子的謊言。所有三個研究小組都觀看了影片,其中 8 至 16 歲的兒童和青少年講述了他們是否偷看過考試答案的真相或謊言。觀察自己孩子的父母在區分真假方面並不比其他父母或本科生做得更好。所有三個小組的參與者都可能擲硬幣來決定,儘管他們傾向於相信自己的判斷——特別是,評估自己孩子的父母傾向於相信他們。
該研究的合著者之一,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家康·李,無法放下這個話題。在一次 TED 演講中,他展示了一張他兒子撒謊的照片。李使用了一種稱為經皮光學成像的方法,該方法測量皮膚中的血流,以檢視他兒子中性面部表情背後的原因。他將他的發現稱為匹諾曹效應:在撒謊時,面部血液流向臉頰減少,但鼻子增加。
然而,蘇霍茨基回應道:“血液灌注可能是撒謊指標的想法是荒謬的。這種說法很危險,因為它們暗示這種做法可能在公共場所(如機場)有用。” 她說,這種效果可能在受控的實驗室實驗中顯而易見,但沒有任何技術可以解決這樣一個事實,即在說真話的嫌疑人身上也可以觀察到撒謊的特徵。“不存在明確的撒謊跡象——只有可能讓我們得出結論,可能已經撒謊的跡象,”蘇霍茨基補充道。
在心理學家貝拉·德保羅領導的團隊進行的一項薈萃分析中,觀察到 50 種非語言特徵中有 14 種更常與撒謊相關,尤其是瞳孔放大和緊張。但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陳述本身給人的印象。虛假陳述往往猶豫不決、模稜兩可且不確定。然而,德國對 41 項研究進行的一項薈萃分析發現了一些不同的東西。吉森尤斯圖斯·李比希大學的心理學家發現,撒謊尤其與自我控制的證據有關:手、腿和腳的動作減少,頭部點頭也減少。
“這些影響非常細微且不穩定,以至於它們無法幫助我們在實踐中識別謊言,”蘇霍茨基說。語言特徵已被證明更能說明問題。“但這些影響不大,而且這些發現並不足以讓人感到樂觀,”她補充道。
英國朴茨茅斯大學的心理學家阿爾德特·弗裡伊是謊言領域最活躍的研究人員之一,他對欺騙的非語言特徵也不以為然。在一項概述性研究中,他、哈特維格和他們的同事、瑞典哥德堡大學的帕爾·安德斯·格蘭哈格寫道,這些訊號“微弱且不可靠”。研究人員將更多希望寄託在語言線索上——儘管這些線索與撒謊的關聯程度並不比非語言線索更高。然而,正如幾項實驗(包括弗裡伊團隊進行的實驗)所證明的那樣,它們可以透過詢問技巧來誘導和加強。關於非語言特徵的如此廣泛的研究並不存在。
難怪情況如此:語言更容易記錄。可靠地捕捉面部表情和手勢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的觀察員或更復雜的面部和身體佈線。研究人員只是在最近才越來越多地嘗試計算機輔助方法,例如自動面部識別。這項技術有望帶來新的理解,因為它能夠處理海量資料流並識別複雜模式。
弗裡伊、哈特維格和格蘭哈格承認,更微妙的非語言特徵——諸如埃克曼定義的那種面部表情子類別之類的特質——要麼被忽視了,要麼被忽略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例如,真實的陳述更常伴有示範性手勢,而謊言更常與隱喻性手勢配對,例如用拳頭作為力量的象徵。或許研究人員在使用其他方法時會發現更多跡象,或其組合。
當哈特維格和心理學家查爾斯·邦德在一項薈萃分析中結合了數千名 測試物件的各種行為特徵時,他們能夠正確識別出大約三分之二的謊言。大多數研究僅測試選定的特徵。一般來說,實驗室實驗無法重現真實條件。調查員和受試者之間沒有真正的互動。更關鍵的是,欺騙是按需進行的。沒有人能夠確定實驗室研究結果甚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推廣到實際犯罪。
為了讓測試物件感覺自己與結果息息相關,通常會承諾,如果他們具有說服力,就會獲得金錢獎勵。蘇霍茨基為了科學事業嘗試了更具挑戰性的措施:在與德國維爾茨堡尤利烏斯·馬克西米利安大學的同事馬蒂亞斯·加默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參與者被詢問了他們犯下的一起假盜竊案。研究人員告訴一半的受試者,如果計算機認為他們的陳述不可信,他們將受到輕微電擊。在該組中,蘇霍茨基和加默觀察到,在不真實的回答期間,脈搏率較慢,同時手部出汗增加。對潛在後果的恐懼加劇了這些差異。
當然,如果蘇霍茨基的實驗室受試者聽起來不令人信服,實際上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對於滕·布林克和波特進行的一項實地研究中非自願接受調查的受試者來說,後果要嚴重得多。研究人員分析了 78 名向公眾求助以尋找失蹤家庭成員的個人的錄影帶。其中大約一半的人後來被判犯有殺害失蹤人員罪。
正如對 75,000 張靜止影像的比較所示,有罪和無罪的受試者在肢體語言方面沒有差異。然而,作者報告說,有罪者的面部表現出更多隱藏情緒的跡象,例如模擬的快樂和悲傷。滕·布林克和波特寫道,實際上無辜的痛苦的人表現出“全臉的悲傷和痛苦”。
在另一項分析中,有罪者使用了兩倍多的模糊措辭,例如“總有人會在某個地方知道些什麼。我想是這樣的。我認為有人會嚇得逃跑,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真誠的呼籲聽起來更清晰、更直接:“你無法想象莎拉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們是一個堅強的家庭,我們不能很好地分開生活。我們現在、今天就需要她回家,越快越好。”
但是,儘管這些研究聽起來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們仍然沒有解決關於謊言研究的問題。差異很小;指標是模稜兩可的。這些結果僅代表平均值,充其量,它們在個別情況下提供了粗略的潛在指示。一個自信地說出的謊言可能比一個口吃的真相更可信。根據哈特維格和邦德進行的一項薈萃分析,這是因為大多數人根據陳述看起來多麼自信、清晰和明確來判斷。當個人忽略欺騙時,不是因為他們注意到了錯誤的訊號。他們大多在以下情況下失敗:當一個贏得信任的人撒謊,或者當一個看起來不可信的人說真話時。
對於不瞭解別人的想法,我們可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似乎進化應該賦予我們對真相的良好感覺,但我們卻很容易被誤導。也許這就是社會共存的缺點。日常生活中的無害謊言教會了我們輕信。
儘管如此,為什麼這麼多人認為他們可以識別謊言?讓我們換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如果謊言和真相看起來一樣,就像兩個雞蛋一樣,會怎麼樣?如果罪犯逍遙法外,而無辜者替他們付出代價,會怎麼樣?哈特維格覺得這個想法難以忍受。“我們希望相信撒謊者會暴露自己,”她說。
本文最初發表在《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雜誌上,並已獲得許可轉載。
